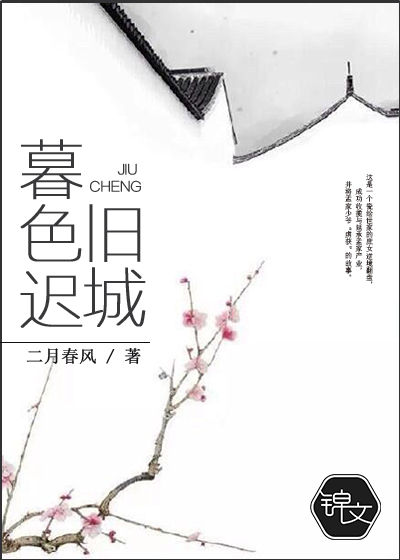林少维却又道:“先生已在四顾轩办了就职的手续,若现在离去,枉费了四顾轩一番心意不说,也是不把你我这朋友一场当回事儿了。” 他其实已说得很委婉,刚就职就要走,违约一事尚且没提。 贺楚书心里明白,他轻声一叹,向孟宏宪拱手:“孟兄,对不住了。” 话已至此,孟宏宪只得回了。 他走后,贺楚书却有些心不在焉。 转至画厅,还没坐稳,一年轻小哥上前来,殷切地道:“贺先生,我是林会长安排到您这儿来学习的,往后您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我。” 贺楚书往桌子上一瞥,道:“这颜料不齐全,你去再拿些过来。” 小哥也往桌子上看了看,疑惑道:“常用的都在这儿了,各个颜色都有,不知先生您还要……” “绯与红是不同的,朱与丹也是不同的,哪里各个颜色都有了,这水色料是透明的,没有覆盖力,需得配合石色料使用,石色颜料才稳定,但是,它又不能调和,颜料的学问大着,你既来学习,怎的什么都不了解?” 小哥听得脸上一阵通红,半懂非懂地去了。 而贺楚书忽地陷入了沉思,想起方才自己谈及颜料,似乎还有一件事未能圆满。 他自恃不是一个追求极致完美的人,没有任何事情非要圆满的决心,但这件,就压在心里总也挥之不去。 去留只在一念之间。 片刻后,他起了身。 待小哥又拿了些颜料过来时,画厅里已空无一人,只有一信压在砚下,封面写:“转呈少维兄亲启。” 孟宅。 孟宏宪破天荒地来到了久违的书苑,怀安与思卿原以为他要启笔教习了,不想,他只丢过来几本书外加几个画册,对二人道:“你们自己看吧,早日学好了,我也好早日让你们去瓷胎上画。” 两人只得低头翻书。 他无所事事,便徘徊到窗口,向外探了探,一股梅花的清香扑面而来。 他的脸色略带悲凉,似对二人说话,又似自言自语:“其实,孟家这些年没有推出新的瓷绘模板,在行内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好在我们自己有窑厂,画面虽没出新,但器型上可做更进,原以为,庭安学那装饰艺术,于瓷器器型塑造上大有用途,可惜他没有学,现在,也不知孟家瓷绘还能撑多久!” 这话里,显然是对怀安二人没抱什么希望,加之贺先生不肯来,他就更没信心了。 思卿很想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可以学好,但是想来无师自通有点难,又不敢冒然夸下海口。 孟宏宪感慨完,回头见二人茫然神色,抖生恼火:“你们俩看着我干嘛,赶紧看书!” 两人连忙又低下头。 正翻着书,思卿面前忽的多了两本,她疑惑地看着旁边。 怀安朝她靠近一些,小声道:“这些我早就看过了,而且看了好多遍,实在没有再看得必要,都给你吧。” 她点点头,刚要将那两本书归纳整齐,恰被孟宏宪发现,立时皱眉:“你这小子打心里还是不想学是不是?” “不是……”怀安连忙站起来。 “既然说定了,不想学也得学!” “我这……” “不要跟我解释,再让我看到你懈怠的模样,小心棍棒伺候!” 思卿连忙将书又推了回去,向怀安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再惹事,怀安只好闭嘴,认了错坐下来,漫不经心地翻着页。 思卿不放心地瞥了几眼怀安,但见他一双眼睛到处瞟,就连窗棂上一根绳子被风吹起,他都能看得津津有味。 唯独书上的字他一眼都不想多看。 眼看孟宏宪要转身了,见他仍然盯着窗,她想提醒一下他,不想对方比她还要警觉,在孟宏宪的目光注视过来之前,他已然挪回眼神,摆出了极其认真的姿态。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做模样给人看的“差事”,他比谁都熟练。 思卿安下心来,慢慢地翻着书。 其实,不单单是怀安,她也看不下去。 孟宏宪给的几本书,什么是笔,什么是砚,什么是生宣,什么是熟宣,这些知识她也是同样谙熟的。 就算孟宏宪不知道她有私下里学过画画,但怀安学了五年,再怎样没长进,总不至于还要从入门开始看吧? 他到底是多看不上怀安? 话说回来,看不上还只能把希望搭在他身上,却也十分无奈。 相对而言,他对庭安就宽容太多了,只要孟庭安不专程去触他的逆鳞,非要研究西洋画,他大概可以真正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事情都不用管。反正,她二人如今再怎样努力,也是为了庭安铺路,这个家,早晚是要传到庭安手里的。 思卿看得清楚,也想得明白,当然亦无所谓,她能走上这一步,就已经与那些深闺中待嫁的女子们不同了。 何况,身边不是还有个人吗,这条路有人陪,总不会孤独。 她只要朝身边一看,就觉得心安。 复又低头翻书,听有人来传话:“贺先生回来了。” 孟宏宪转身,一脸惊讶:“为什么?” 话音未落,贺楚书已走了进来,向他笑道:“有个遗憾,不弥补上,心里总也过不去。” 这一回来,就困了半生,丢了余生。 两个人学画步入正轨,孟宏宪比以前上心了许多,经常过来查看,思卿自不必说,机会得来不易,她万分珍惜,怀安偶尔学烦了还是会偷偷跑出去,但是因为有人相陪,终归没以前那般无聊,大多数时候还是会老老实实地听课。 只是思卿擅长工笔,孟宏宪偏要她学写意,贺楚书便教她将两者结合,画得好了,亦可以展现出孟宏宪要的那种意蕴,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时间就在这样忙碌又美好的日子中慢慢流淌。 孟庭安始终没露面,贺楚书念及与他师生一场,这日择了空,与怀安思卿一并过来看他。 他们去的时候,孟庭安正在书房,一张未完成的画摆在桌子上,听闻有脚步声,他立时站起来遮了遮,然而,门打开的时候,他忽的心一横,又让了身,将那副画全然露了出来。 待看到三人,不知是失望还是松懈,只是轻轻吁了一口气。 思卿第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画,色彩十分鲜明,与她那日在四顾轩未开放的展厅看到的油画用色相像,她当时对那几幅画颇为欣赏,便也印象深刻了。 孟庭安画得是个半身的人像,看五官像是他自己,但线条扭曲,配色亦是惊奇,蓝灰色的背景下,黄色和绿色描绘的脸庞,颜色冲突对比明显,明明线条没有仔细勾勒,却偏因为如此像是有了动态,视觉上带来极大的冲击。 虽好看,但让人觉得压迫恐惧,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贺楚书也盯着画看了好一会儿,叹道:“事情总是要争取的,你何必痛苦?” 思卿有些迷惑,不知贺先生此话何来。 怀安凑到她耳畔,低声道:“西方印象派,没有传统的法则教条,讲究画由心生,三弟画出这样的画,大概心里不大舒服吧。” “印象派,画由心生?”她恍然大悟,怪不得她方才会有压迫之感。 只见孟庭安淡淡一笑,对贺楚书道:“父亲他一向说一不二,我只怕又惹他生气。” “关于惹孟兄生气,你二哥最有经验,你可以去请教清教他。”贺楚书开了句玩笑。 怀安转着脑袋无所谓道:“三弟是乖孩子,爹才不会生他气呢。” 孟庭安又笑:“二哥活得洒脱,我才羡慕呢。” “不洒脱。”怀安摆手,“我怕得很。” 没有安全感的人,最怕没人重视他。 思卿看着他,默默地想,是不是他的顽劣,也是幼稚的想要引起家人的注意? 沉思间,听贺楚书道:“庭安,你的画很好,听我说,既然你喜欢,就不要放弃。” 孟庭安眉宇之间覆上一抹愁绪:“可父亲不喜欢,他为何这么抵触西洋画,我想不通。” “孟兄行事一向求稳,难以接受外来事物可以理解。”贺楚书想了想,望着他道:“你好好画,或许可以在四顾轩展出,若是受到好评,想必孟兄就松口了。” “真的吗?”孟庭安眼前一亮,“我的画可以在四顾轩展出吗?” “以我的观点是可以的,但……”贺楚书直言不讳,“四顾轩仍是国画最受欢迎,他们也不大能接受西洋画,但我尽力帮你争取,倘若……倘若争取不来,我……还是会尽力。” 孟庭安眼底涌现些许失落,但他仍存了感激的心,向贺楚书躬身道:“老师放心,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会好好准备的。” “你能如此想是最好的。”贺楚书点头。 怀安也安慰道:“四顾轩那么多人,不会所有人都排斥西洋画吧,总有人会欣赏的,放心,要是他们不让办画展,你哥我去扁他们。” 孟庭安又被逗笑了,思索了片刻,换了郑重的表情,道:“二哥,我知道你对瓷绘是有天赋的,你与四妹好好学,莫要浪费了天赋。” 怀安不以为然:“那当然,我对什么都有天赋。” 又来了,孟庭安摇摇头,几人接着闲聊一番,天色将晚,三人起身离去。 轻风吹来,带来两三片白色碎片,思卿抬手一迎,那白色落在手背上,转瞬化成了一颗颗水珠。 她抬起头,才发现下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