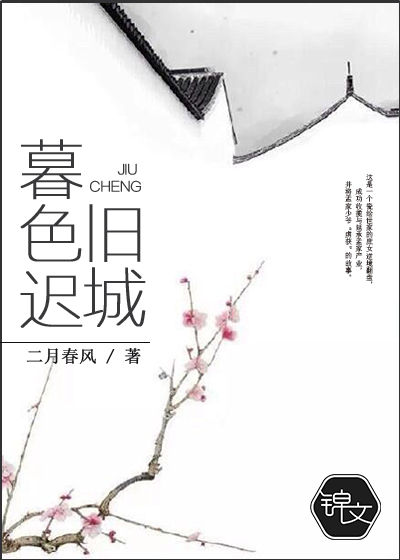秀娥回道:“不一定是这事儿,老爷让两位少爷还有思亦小姐都过去了。” 思卿茫然来到正院,她住得偏,又是最后一个得到通知的,来得也最迟,一进厅里,见孟宏宪于正席端坐,老太太在右侧,潘兰芳与何氏坐在偏席上下两位,怀安庭安以及思亦排排站在厅中央。 思卿低着头,往孟思亦旁边一站,瘦瘦弱弱的。 除了已经嫁出去的孟思汝,孟家人全都到了。 虽然聚齐,且是三代同堂,人数却也不多,孟宏宪是独苗,他的下一代还没都到开枝散叶的年龄。 堂上的老太太看着这些人,第一次有了荒凉之感,以前有孩子在外未归,心里有个盼头,似乎等人回来了就会圆满,如今该回来的回来了,未意料到会回来的也回来了,又发现原来不过如此,不免凄然起来。 孟宏宪发不动火了,淡淡的对四个人道:“今天叫你们过来,郑重地问你们一些事情。” 几人屏吸听着。 “你们是不是都不想学瓷绘,确定了吗?” 四人面面相觑,不知他何意,没人敢言语。 “谁确定不愿意学,站出来……我不怪你们。” 说是不怪,但依旧没人敢动。 唯有最小的孟思亦左右张望了一番,向前迈了脚步。 何氏见状连忙站起来:“你干什么,你还小懂什么?” 孟思亦不满道:“我不小了,我知道自己的喜欢与爱好,我不喜欢瓷绘,那国画和彩釉什么的,我学不来。” 孟思亦今年十四岁,年龄不小,但也绝对不大。 何氏红着脸还要再说,孟宏宪抬手打断了她:“好,你不想学,我知道了。” 语气仍是淡淡的,听不出情绪。 又在另三人身上扫量了一个来回:“还有吗?” 有了前车之鉴,孟庭安亦站了出来:“我想专心研习西洋画,还望您成全。” 孟宏宪眯了眯眼,回道:“你不想学瓷绘我不逼你,但你要研习西洋画,不行。” “父亲……” “此事再议。”孟宏宪没给他争辩的机会,继续道:“你们两个呢?” 不待二人回答,他先对着怀安道:“你肯定是不想学的是吧,只管说,我不责备他们,也不会再责备你,倘若孟家瓷绘到我这一代结束了,那也是命该如此。” 怀安抬头看着他,才几日,孟宏宪赫然多了许多白发,眼里也没了往日的凌厉,看上去疲惫不堪。 他思绪一番,叹了叹气,道:“我学。” “什么?” “好歹我跟贺先生学画的时间最长,那就别让先生和……大家的精力白费了。” 孟宏宪眼睛亮了亮,但没有太大的欣喜。 他略一沉默,目光转向思卿。 思卿在思索该如何回答,从心而论,她是愿意学的,可是,即便孟宏宪这会儿能心平气和地听大家想法,她亦深知孟宏宪不会同意,只怕自己又惹恼了他,加快了将她嫁出去的进程,那可就糟了。 到底是顺着自己的心,还是遂着孟宏宪的意,她一时间权衡不出。 踌躇之间,却听孟宏宪道:“你要不跟着怀安一起学吧,你同意吗?” 她陡然抬头,不敢置信地望着眼前人。 “你同意吗?”孟宏宪又问。 她连连点头,却还是不明白对方为什么突然变了态度。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她雀跃。 “但我有条件,你先得答应。” 就知道机会不会这么容易光顾,她紧张问道:“什么条件?” “既是学,就要把孟家瓷绘传下去,你是女子,以后终归是要跟别人姓的,不得不警醒一些,我的要求是,短期内不许嫁人,你可同意?” 思卿立刻点头,这哪是要求啊,这简直是恩惠啊。 此时何氏插了一句嘴:“那要留她多久啊?”问完觉得不太合适,又道:“姑娘家年龄太大了可更不好嫁了。” “至少要将所学技艺传给孟家下一代,如今庭安……怀安都还没成亲,待下一代长成,数年的工夫是要耗的。” 何氏一怔:“这叫短期?你要传下去的话,不是有怀安吗,何必……” “怀安是怀安,她是她。”孟宏宪冷着脸回应,又看向思卿:“我不强迫你,愿意与否,全凭你自己决定,但若是答应了,就得遵守条件。” 怀安似乎也想说话,但思卿率先扯住了他,毫不犹疑的点着头道:“我愿意。” “你真愿意?”孟宏宪心知自己刁难得有些刻意,见她一点不迟疑,不免惊讶,“你是现在没有遇到良人,才敢如此笃定,倘若他日你碰上了心仪的人,又该如何?” 思卿扯住身边人袖子的手松了松,道:“那就……相守不相亲吧。” 话说到这份儿上,孟宏宪倒有些惭愧了,他思揣片刻,道:“这样吧,若是对方愿入赘孟家,我可放松此条件。” 思卿稍作沉思,心道她原本也不想成婚,入不入赘都没什么影响,但既然孟宏宪已松口,她自不必去将自己的后路堵死,于是点点头,应允了下来。 何氏心中又生不悦,冷哼了两声,拉着思亦先离去了,两人出了院子好一会儿,厅内仍能听到她不住数落思亦的声音,思亦不是个能忍气吞声的,她说一句,思亦就怼一句,两人吵吵嚷嚷,一路从正院吵到了东厢。 孟宏宪任由他二人离去,按了按额头,接着道:“明日我再书帖拜请贺先生回来,你们去吧。” 怀安与思卿来时心情皆凝重,却不想“因祸得福”,离去时皆大大松了口气。 唯孟庭安未能得偿所愿,他默默回了自己的住处,站在书房发呆。 书房是院子的最后一间,采光最好,他对着桌子,一言不发,身边走来一下人,叹着气劝诫他:“三少爷,您何必和老爷这样较真呢,您就松松口说您愿意学不就是了,学不学得成都没关系啊,而且,您那西洋画跟咱们这画有什么区别呀,不都是画画吗,您能学得了那个,还学不了咱们这个吗?” 孟庭安抬起头,望着桌对面的墙,一副画在那里挂了两年,倒是没什么灰尘,应是有人经常来擦拭的。 那是人像画,画里的人就是他自己,而这画的作者,是孟怀安。 这是昔日他出国之前,怀安为他画的,画里的他眉目与本人几近无差,就连略带青涩的笑都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他盯着那画,对身边人道:“不是有没有区别的问题,有些东西我不想碰。” 下人听得糊里糊涂。 与此同时,正厅里,潘兰芳对孟宏宪的决定亦是糊里糊涂。 她屏退了下人,问道:“为什么让思卿也学啊,你还真打算让她一辈子不嫁人了,就算她自己愿意,那孟家难道要养她一辈子么,还答应让她招个入赘的,咱们不但养她,将来还要养她一家几口是吗?” 前脚何氏赌气离开,也是抱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妻妾二人在某些方面的认知上是十分相同的,无外乎能相处融洽。 “她要是能学成,不是不可以。”孟宏宪道。 “好好好,就算养着也行,可是……”她顿了顿,左右一看,小声道:“咱们都知道怀安是什么身份,让他们两个天天在一块儿呆着,这不太合适吧?” 孟宏宪不耐烦地看着她:“你们女人家想得太多还偏偏不动脑子,我们是知道怀安的身份,两孩子自己又不知道,在他们眼里就是兄妹,兄妹一起在书苑学习,有问题吗?” “也对哦。”潘兰芳一拍腿,她倒是忘记这茬了。 另一边的老太太表情不大自在,抿了抿嘴,什么也没说。 “而且,就因为怀安的身份,我才让思卿跟着学。”孟宏宪又道。 “为什么?” “怀安始终是外人,虽然他的身份我们永远不会去揭开,但是只怕万一,万一他知道了,这孟家技艺岂不是传给外人了,思卿好歹是正儿八经的孟家人,让她跟着学总有个保障。” 老太太听此话,叹了口气道:“我原是劝你,若这些个孩子都不成气候,那就到外面收徒弟,可你宁愿关窑也不愿收徒……” 孟宏宪凝重回道:“瓷绘虽无特别之处,浔城做瓷绘的也有好几家,但孟家做了几代,自积攒了不可外说的经验,若是传给了外人,叫我如何跟祖上交代?” “你这样想也有道理。”老太太不再争辩。 潘兰芳却担忧着:“一个是外人,一个是女儿……还是自小没养在身边的女儿,这两个人都不保险,要我说啊,还是再劝劝庭安,那孩子性子软,只要多说一说他就松口了,真的……” “不用了。”孟宏宪摆手,眼里带着疲倦,“怀安用五年的时间让我明白,不想学的人,就算把他按在桌子上也没用。” “不过……话说回来,他为什么又愿意了呢?”这一点他还没想通。 “肯定是怕孟家真的不管他,还不要趁机好好表现一番。”潘兰芳漫不经心的接话。 另两人一想,这个理由说得过去。 然又听潘兰芳道:“这孩子顽劣惯了,他不会老实几天的,你们且看吧。” 要是他再不珍惜这次机会,那就有理由去劝庭安来了! 孟宏宪只当没听见,翌日即去四顾轩请贺楚书回来,原以为没什么悬念,却不想被他拒绝了。 贺楚书的回复是,他真的没什么东西要教怀安了。 孟宏宪道:“现在还多了一个思卿,先生受累再教教她?” 贺楚书还在犹豫,艺博会会长林少维迎上来,听了缘由,忍不住道:“以贺先生之名,舍四顾轩之职去教习一介女流,未免大材小用了吧?” 以前四顾轩有意请孟宏宪来办瓷艺研习社,孟宏宪拒绝得十分干脆,林少维对他有些不满,当面说话便没有很客气。 一介女流四个字让孟宏宪也很不满,虽然他在孟家经常指责女儿无用,但听旁人看轻自家孩子,那就不是一回事了,他冷着脸,不跟他辩,只把目光投向贺楚书:“相信贺先生自有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