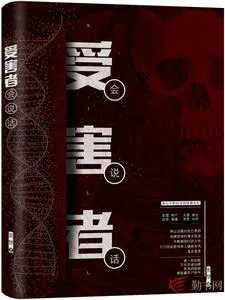一张较为破旧的桌子放置在房间的角落里,房间是她的,原本她要往自己房间堆放什么东西那也是她的自由,可是不知道她从哪里带回来的破旧桌子,破破烂烂,木质材料大部分已经腐化,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最糟糕的是,在腐烂的木材中,时不时会钻出一两条虫子,眨眼间又消失不见,更为糟糕的是,到了半夜时刻,那些虫子会躲藏在木材里,贪婪无比地撕咬着看似美味的木材,遇到僵硬一点的木头它们会咬得更为吃力,那声音简直是如雷贯耳似的,不断地回响在脑海中。我在隔壁房间也能听到那虫咬的声音,更别说crazy女士近距离面对着该桌子。令我困惑不已的是,她似乎对那破烂的桌子特别有感情,捡回来以后,用清水洗了好几遍,很耐心地一点一点地擦拭着。嘴里还不忘哼着歌,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好几次我都想问她,究竟发生什么事,可是她每次都笑而不语。她的行为越来越反常,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我早已习以为常,可是能不能不要弄这一出? 在我第六次问她,为什么要捡一张这样的书桌回来的时候,她才轻描淡写地回答我:“这张桌子用来翻译工作,很有感觉。” 是的,事实上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我压根就不相信她的鬼话,我嗤之以鼻的反驳她:“翻译工作而已,又不是写作,难不成还需要灵感的来源?” 她厚着脸皮回答我:“是的,事实上就是这样,请你要相信我,尽管我知道这张书桌的年龄很糟糕。” 我看着她房间里的欧式书橱、破烂不堪的书桌、公主般高贵的睡床,自然被气得七窍生烟,从她住进来开始,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建基在与我作对的基础上,但她对我并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可她就是这样做,总是令我难堪。对我最大的不满的做法就是,将我原本好好的书桌替换成这么一堆破东西,我不是要歧视它,但前者和后者的差别确实很大,我无法接受这种事实。 “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我看着她在整理书橱上的书籍,脸蛋在笑,但内心毫无波澜。 “别傻了,不知道有多开心。”我发现她把言情小说的顺序和谋杀类型的作品互相调换了位置,言情小说的放在最顶层的位置,谋杀类型的作品则放到了最容易触碰的地方,这很显然,她的阅读习惯产生了改变。 “你把我原有的书桌给替换掉,换了一个被虫咬烂,遍体鳞伤的书桌,前者被你拿去摧毁掉了。” “有些东西有就行了,不用两个同时存在的,必须有一个是要作出牺牲,你懂吗?” “我明白一山不能藏二虎这个道理,可是我觉得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两个老虎,而是……”我延长了尾音,故意让她自己说出来。 “我是故意这样刺激你的。”她居然一下子就承认了,脸不红心不跳,神情自然,呼吸顺畅,畅通无阻,她没有说谎。 “难道说,我最近得罪你了,而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问她。 她一字一句地说:“你在怂恿我回去读书,你企图令我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家。” 天呐,她居然用“家”这个字来形容这里,我心里不是没有感动,但我还是要说清楚:“第一,我没有要驱逐你的意思;第二,我劝你回家读书纯粹是为了你的将来打算的。” 她突然很生气,很不满意地呼喊着:“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你好”为借口逼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是不是只有这样你们才有成就感?你们这些成年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对小孩循循善诱?” 这孩子太偏激了,我必须要矫正她的思想。她呼喊之后,眼睛开始不断地抽搐,眼泪紧接而来,身体下意识地往后移动,我往前一步,她就往后一步,我问她怎么了,她很惆怅地伸出手阻止我前进,捂着嘴巴,跑出了房间,离开了这个“家”。我想追出去,但感到全身乏力,脚步无法正常移动,我的心告诉自己,此时此刻,追出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奈之下,我只能返回自己的房间。重新打开笔记本电脑,阿怪的邮件在昨晚的凌晨已经发送过来,但我心烦意乱,所以没有详细地阅读,现在同样是没有心情阅读任何的文字,但我莫名其妙地关心案件的调查进度,硬着头皮过滤邮件中的每一个细致上的文字。 to:许医生 真不敢相信,千禧酒店的电脑部主管竟然是一名女人,(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该部门的主管是男的)她非常的忙碌,对于警察的接见,一般人都会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但是她不一样,她一边听着电话,一边在我旁边走着,嘴巴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从她谈话的内容中,大部分是关于工作上的交接,她语速很快,几乎没有一丝的停顿,脑袋稍微转得慢一点,都跟不上她的思维。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才消停了一会,扭过头问我:“给你三分钟时间,因为很快就有电话要进来了。” “要切段走廊外面的监控片段,是否只有电脑部的技术人员才做得到?”我傻乎乎地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过,负责监控走廊的总控台没有被做过手脚,现在整个电脑部只有我一个人在负责,所以要么你就怀疑是我做的手脚,要么就承认监控没有拍到的片段纯粹是设备的问题。”她说话很坚决,也很固执,让我无法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难道说,走廊外面还有拍不到的角度?”我自言自语地反问着。 这一会她又开始打电话了,她随口说了一句:“其实你有没有想过,监控没有拍到杀人犯经过外面的走廊不代表他是处心积虑破坏了监控的设备,也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经过那条走廊离开呢?” 她的这一番话使我恍然大悟,使我不再思考监控设备的问题,我换了一个问题:“2901房间,还有其他离开的渠道?”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2901是靠近电梯口的,那里是为特殊客人所准备的,因此那个走廊是没有摄像头的,方便某些富商和情人们的私会,这种事情我们也见怪不怪,但在酒店的平面分析文书报告上,是很清楚地说明了,每一个角度都有监控,这只是掩盖观众的一种说法而已,有一小部分的位置还是没有监控的。” 我故意缓和气氛:“你泄露酒店机密,你不担心被解雇?” 她无所谓地说:“电脑部现在很缺人手,把我也解雇了,科技上的细节,他们还能找谁?” “你刚才用了“也”这个字眼,之前大裁员过?”我问她。 “别提了,前段时间董事局经开会研究决定,实行裁减电脑部的人手,一下子裁员裁了三个,就剩我一个主管级别的。” 我打量着她,怪里怪气地说:“不会吧,千禧酒店是五星级服务,生意兴隆,客人源源不断地前来入住,经济没有萎缩也要裁员?” 她满不在乎地说:“谁知道呢?高层的思维都是捉不到,摸不透的。” “裁员事件是什么时候的事?” “有一段时间了,具体细节我都不记得了。”她打电话过去,似乎没有人接听,她又发起短信了。 “你们高层开行政会议应该有文书记录的,可以拷贝一份给我作为参考资料吗?”我试探性地问着。 她停止了打字,转过头看着我问:“你是警察,我交给你等于与警方合作对不对?” 我严肃又肯定地回答她:“这绝对是良好市民应该尽的责任。” “把你的电子邮箱给我,有时间我会发给你。”她接起电话,离开了我的视线范围。 我默默地在白纸上写上电子邮箱,静悄悄地往她口袋里放,她用眼角的余光瞄了我一眼,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我以为她在向我示好,但是很快我发现自己又自作多情了,站在我身后的是大堂经理,他又轻而易举地发现我的位置,并且找到了我。他给了我一个温馨提示:“阿怪探员,这里是行政部的区域,就算是警察,未经过允许一律不可以内进的,请你离开。” 我不得不再次赞叹他:经理,你真的很厉害!我每次进入酒店,无论躲在哪个角落里,都能被你轻而易举地找到。 他为此辩解:非也,非也,我只是凑巧经过这里发现了你而已。 我连忙对他说:生活艰难,工作不容易,彼此体谅体谅……我趁机逃走,一溜烟似的。其实史警官对这宗案件不闻不问的,我那一组队员又要忙其他的案件,只有我一个人独立支撑整个调查报告,说实话还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委托了阿娇为我做了一份关于梁宇的个人社交圈子以及家庭成员的报告。然而比较遗憾的是,梁宇的家人全部在加拿大生活,他遇害的事暂时没有知会他的家人,他没有欠债,没有不良习惯,不吸烟,但是会喝酒,底子很干净,没有不良嗜好,连嫖娼被抓捕的记录都没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好男人。不过……至于他为什么会想着侵犯张慧慧这件事,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色胆包天的人,否则他怎么会一点犯罪记录都没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没有已婚记录,生活中连女朋友都没有,喜欢的人,暗恋的人,均没有发现。他只是有几个利益冲突的情人,说到底也是出于利益的想法,或许那些感情是不真实的,在虚伪的装扮下,稍微一击破,就会溃不成军。不过,阿娇去了梁宇的私人公寓里,他找到梁宇生前的遗物,结果找到几封由无名氏写给他的“情书”。那几封情书是在垃圾堆的角落里找到的,换句话说他并不在乎那些情书,甚至把它们当作垃圾来看待,还准备把它们一一清除掉。看来有爱慕者一直暗恋着梁宇先生,如今这几封信件很安静地躺在一个精致的礼盒内,我的手触碰在盒子的周围,厚实的纸皮,不怎么精美的包装,使我对这几封信件起了莫大的兴趣…… 不过,关于信件的内容,容许我卖个关子,下一封邮件的内容再向你透露,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我把电子邮件的窗口重新关闭,深呼吸着,把电脑重新合上,客厅传来一阵声响,我知道她回来了,随后传来门被关上的声音,我立刻走了出去,尝试将手放在门把上,轻轻地扭动着,门没有锁,我扭开它,轻轻推开它,在微弱的光线的照明下,我看到了她愈发精致的脸庞,整个人蜷缩在角落里,头发散乱,毫无规律地散在额头上,她以往扎起的小马尾已经荡然无存。 幽静的小屋里,暗淡的光线,源源不断,从未停止的摄影灯光在现场闪烁着,阿力在现场被民警盘问着,他简单地交待了几句,为何来这里找死者以及发现尸体的前前后后;房东则表示一脸无辜,他对这里发生的命案表现得更为迷惘。黄雁如此时此刻的心情很糟糕,她的手里还拿着从出租屋带出来的雨伞,本市的法医开始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她一言不发地打量着尸体,脑海里则陷入了沉思。良久过后,法医终于检验完毕,他在摘下手套的同时,同样是万分茫然地摇了摇头,她问他检验结果如何,他则表示,死者的死亡时间距离现在是非常的接近,换句话说,在他们发现尸体的同时,凶手兴许是刚刚离开不久,更为离奇的是,现场根本找不到可疑的指纹,很难想象凶手是戴着手套行凶或者杀了人之后再进行清理现场的,不过……按照尸体的僵硬速度来看,凶手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清理现场的任何一寸角落。我们可以幻想一下,例如死者在九点零一分钟被凶手杀害,发现尸体的人在零三、零四分钟赶到现场,但是这个时候凶手已经成功逃离凶案现场,甚至尸体的血液还从头颅内涌现出来,第一个问题,凶手是如何逃离现场的呢? 民警已经调了走廊外面的监控进行调查,发现在房东他们赶到现场之前有一名男子神神秘秘地探访死者的家中,但是该名男子戴着帽子,帽檐还压得很低,他又低着头走路、敲门,根本看不清他的样子,或许说,他根本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他的样子,之后这个男人一直没有出来过,直到房东赶到现场,发现了尸体,那个神秘男人都从房子里没有离开过,也就是说,他要么还在房子里,要么已经离开,但监控设备又没有拍到他,此时监控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故障问题,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是疑点重重了。那么凶手是如何离开的呢?这一点恐怕已经是无法解释的一个现象。 阿力哭着一张脸说:“如果让银银知道她父亲已经遇害,她一定会很伤心的,毕竟她的亲人本来就不多了。” 他坐在楼道的阶梯上,黯然失魂地惆怅不已,黄雁如轻声叹息着,同样表示不知道如何向苏美美交待这一件事,其受到的打击已经太多,如果再多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她耳边,她或许会奔溃。 “你来找他干嘛?”她终于想起这个问题。 “我想和银银结婚,欲征求他的同意,毕竟他是她的父亲,我不希望他们两父女一辈子翻脸。没想到,人没有劝好,就这样死了。” 她安慰他:“回去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事情将会更多。” 事实上,她对明天也开始失去信心,但是她很清楚一件事,某些事情总会有一个答案,尽管这个答案不会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