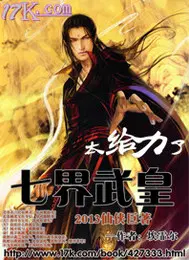缓了口气,我的背也不那么疼了。我挣扎着站起来,蹭到湖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边把那诡异的景色看个究竟,一边在回想着刚才我昏迷之中的那段似梦非梦的经历。 刚才的梦境究竟是真是假?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神秘的濒死体验?我是否真的到达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和我短暂相聚的外公,他真的存在吗?那道门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门里门外的世界会反差这么大? 一连串的问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可是我连一个都没有办法解答。一时之间,我的头又开始痛了起来。被那秃驴弄出的伤口其实已经是好得七七八八了,不过我估摸着里面的淤血还没有消尽,所以这几天每当我认真想问题的时候,脑袋就会隐隐作痛。 我转头问身边的花少:“刚才怎么回事,我到底昏了多久?” 花少嘿嘿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可真的是把老子给吓坏了,想都不想就往下跳。若不是我们已经快要到底了,你小子搞不好就回不来了。” 尼玛的!那是我想往下跳的吗?我忽然记起来了,整件事的罪魁祸首他娘的不正是这个臭小子嘛! 我这气又不打一处来,狠狠地踹了他一脚,算是报了在上面的仇。现在我发现背上的疼痛感已经不那么强烈了,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大碍! 我指着他,破口大骂:“你个死孩子,没事干你******拿枪轰那链子干屁呀,脑子被猪吃了!一船人都差点被你害死你知不知道?你他娘的以为老子是属猫的,有那么多条命,经得起你这么折腾。” 我很少对花少动怒,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冲动起来完全不顾后果。相交这么多年,我早就习惯了他这个德性,但是这次连累白梅都差一点送了命,我还真的是生气了:你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也得考虑考虑别人呀。 花少看我真的发怒,也不敢再胡说些什么,摸着被我踢中的半边屁股,闷声不响地坐在一边。接着他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带封口的塑料袋,里面居然装着几包烟。他打开封口,拆了一包烟,拿出两根,一齐点着了,在递给了我一根后,就坐在地上闷着头猛抽。 我知道刚才骂得狠了,这小子脸上挂不住了。估计除了那华老爷子,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人敢这么熊他。嘿嘿,这白梅在场我看也是一个因素,这小子最怕的就是在女人面前丢面子了。 其实他也不是那么没心没肺,心中肯定也在后悔把那链子打断的事。不过我正在气头上,也懒得理他。两个人就这样一左一右地坐着抽烟,谁也不再说话。 这时候白梅走了过来,对我说道:“你也太过分了,你知道是谁把你从湖里捞上来的?” 原来白梅这小妮子从落水的那一刻就醒了,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当然不知道,她可是一清二楚。这姑娘就拉着我的手,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跟我复述了一遍。 花少看到我们从那船上掉落下去,当时就急了,也要跟着跳下来。巧巧和阿雄在后面拼命地拽住他,他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消失在黑暗中,都快要抓狂了。直到我们掉落进水面,又激起了水面之下的一股子阴火,他们才了解到当时船已经是离水面不远了。(这些事情是后来巧巧对我说的,为了故事的连贯性,我在这里先记述下来。巧巧另外还说了一句让我十分感动的话,她说她这辈子还没有遇见过像我们俩这样可以为对方豁出性命的朋友。) 知道距离不远了,花少和阿雄二话没说,紧跟着就跳了下来。 花少捞住了我,阿雄则去救助白梅。其实白梅的水性很好,她小的时候是体校游泳队的。再加上她下边有我这么一团大肉垫,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浑身上下一点事也没有。所以她清醒之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帮助,在水里,这小妞滑得像条鱼一样。 倒是我,直接跟那水面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巨大的冲击力一下子就把我给整晕过去了,就像个石头一样往下沉去,花少一个人根本就没办法拖得住我。结果他们三个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我给拖上岸。用花少当时的话说,妈的拖条死驴都比拖这小子轻松。 待到上了岸,花少看我不动弹,急得上蹿下跳,又是打算做CPR,又是说要把我倒吊起来倒水。 好在这阿雄还懂点急救常识,让花少不要胡乱搬动我。他摸摸我的颈动脉,又探了探我的鼻息,摆摆手告诉花少,说我只是晕过去了,没有溺水,不需要急救。 说完他又仔细地检查了我的全身,在确定了没有骨折和内伤什么的之后,把情况告诉了花少和白梅。这两人听得我没什么事,悬在半空中的心才算是落了地。 把刚才的情况说完,白梅紧拉着我的手,对我说道:“如果不是他拼了命地救你,只怕现在……”话没说完,她明眸一转,又要落下泪来。 我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花少这小子虽说是个不折不扣的祸精,但是在义气上还真是没的说。我还真不知道,若是换作是他落水,我到底有没有勇气也跟着跳下去呢? 于是我走到花少面前,狠狠地在他头上摸了一把,又拍了拍他的肩膀,对着他点了点头。花少也抬起头来,冲我咧了咧嘴,又扬了扬眉毛。我知道这小子其实也没往心里去,我跟他这么多年朋友下来,基本上很多东西已经不用直白地说出来。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两人已然是能够心意相通了。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其他的人呢?从我醒来到现在,这里就只有我们三个,其他几个人跑哪去了? 花少给了我一个解释,其实在我昏迷的时候,一行人所搭乘的那艘“鬼船”已然是抵达了湖面。而那些姑获鸟被我们落水时激起的那股子阴火一冲,却也惊慌失措,四散逃窜,不多久就消失殆尽。所以除了我这个倒霉孩子以外,其他人都是有惊无险,平安抵达。 到了这里,一行人的意见却产生了分歧:那师徒两急着要赶路,薛忠自告奋勇地要背我,而花少则怕我再有个三长两短,坚持必须等到我醒了才能走。 争执了半天,最后终于是达成了妥协,那师徒两先行探路,花少他们则留下来看护我。巧巧给了花少一个眼色,也加入了探路的行列。花少又担心这师徒两玩什么花样,不放心巧巧的安危,让阿雄也跟着去了,结果七个人里去了四个,只留下了我们仨。 这他娘的叫什么事情嘛!这行军打仗哪有整支主力部队都跑出去探路的?你说他们这决定做得,如果这时候哪里突然间再蹦出个粽子来,就凭我们这三个人的这点战斗力,还不够给它挠痒痒的! 听了花少的讲述,我问花少:“那船呢,在哪儿?”这湖里鬼火丛丛,湖面上的视野非常好,我却没有看到来时乘坐的那艘船。 “不就在那……”花少拿手一指,却指了个空,广阔的湖面上哪里还有那“鬼船”的影子,而且连那八根链子也是一样消失不见了。 “咦?我奇了个怪的,刚才明明还在那里。”花少似乎不怎么相信自己的眼睛,朝那个方向走了几步,想要看个清楚,却还是一无所获。 我当然信任花少,他说刚刚船在那里,那船一定就是在那里。肯定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又有什么机关,使得那艘船消失不见了。 突然之间,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从我的心底冒了出来:这曹操可不是一般人,何等的睿智,其城府更是深不可测。我总觉得这老小子一定是在玩什么花样,他搞艘船来接我们,肯定不会是“欢迎各位莅临指导”这么简单,我反倒觉得这其中有一股子很浓的“请君入瓮”的味道在里面。 我把手里的烟头丢下,问花少:“老爷子他们走了多久?” 花少看了看表:“已经走了有大半个小时了,说好的,一个小时后他们就回来的,我看快了。” 既然已经约定了汇合的时间,看起来暂时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干坐在这里等着他们回来。 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头的不安感却是始终挥之不去,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与巧巧和阿雄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屡次三番出手相助,我心中已然将这两位当做了朋友,不免一直牵挂着他们的安危。 以巧巧和阿雄的身手来看,那师徒两要想玩什么花样的话,他们应该是应付得来。我最怕的就是这地下再有什么厉害的机关,这两个年轻人跟我一样,都没有什么下地的经验,若是一不小心着了那古人的道,那么事情恐怕就会变得比较麻烦了。 我站了起来,活动活动了手脚,以排遣心中的压抑。这时候,身体上的不适感已经完全消失了。看来花少这小子说的不错,老子的这条命还真的是大条得很,这么高掉下来都有没什么事。 四处走了走,我又仔细打量了一番周遭的环境: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湖,湖面上满是鬼火粼粼,将湖边的景色照得透亮。一眼望去,眼睛里满满当当的都是湖水。这湖真的很大,若不是知道这里没有海,我真的会误以为此时我正站在厦门的海边呢。 可是这些光芒也就是局限在沿着湖边的一小块地方。在我的身后,黑暗渐渐地膨胀起来,吞噬着每一寸空间。 我拿起手电,向着那黑暗之中照射。入眼的情况跟我们在那平台之上差不多,无尽的黑暗始终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道这后面有多大的空间。手电的光柱扫了几下,只看到远离湖边的地面上,犬牙交错地布满了嶙峋的怪石,密密麻麻地填满了我所能看到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