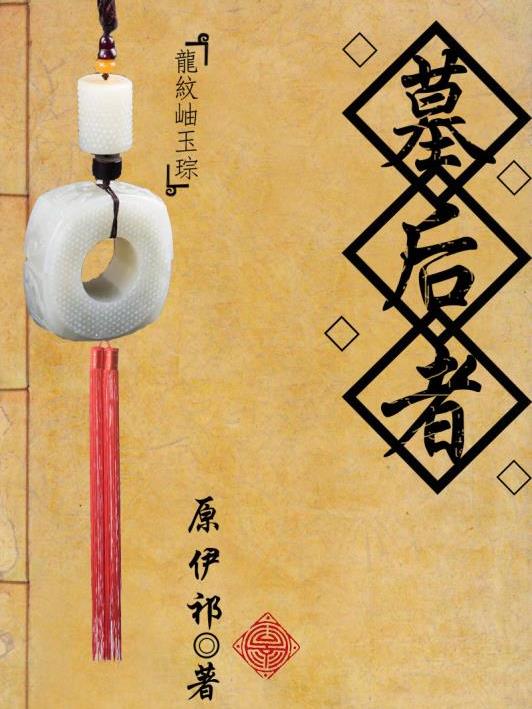图案印在纸上的时候,因为印泥是红色的,似乎这个样子显得反而更加生动,我和郑木香面面相觑,继续看向这个图腾。 图案是两朵花,在滴着血,两花并蒂,猩红美丽。 郑木香看到后说:“你有什么想法?这是什么花?” 我扶着下巴,架着肩膀,蹙眉道:“根据我的了解,这应该是樱花。” 郑木香说:“樱花怎么会要流血?” 我摇头,道:“听说过杜鹃啼血,樱花流血不知道。” 郑木香表情就变了,说:“你是欺负我读书少吗?你以为我不知道杜鹃啼血是说杜鹃鸟,不是说杜鹃花?” 我搔头言道:“我瞎说的,不过这个图案肯定是有什么说法的,一定和这个胳膊的主人有关。” 我当时完全一头雾水,又要防止暴露给郑木香太多信息。 樱花这种东西我除下在我的大学武汉大学听说比较有名,那就是南京林业大学的樱花了,然而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我不得已又联系到了什么。 从整个事件来看,断臂不会来自于一个普通人,我更倾向于相信是个什么组织的人,可能是日本组织。 这个想法的原因依旧出于巴人墓,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抗倭女将会在壁画上画一些日本神话里的鬼怪,那些万千妖魔拥趸的鬼怪居然在白絮音面前手到擒来,千丝万缕之间,我下意识中总是主观地把这些林林总总的线索联系在一起。 这让我对白絮音这个女人更加感兴趣了。 郑木香问我:“你是不是又惹上了什么事儿?你怎么会有个死人胳膊?” 我现在再去看这个胳膊的时候,心里打了个冷战,仔细想想,这个胳膊原来可是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体上的! 我答:“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莫名其妙邮寄给了我,先不管了,反正我们现在专注于自身安全最重要,就把它先搁置吧。” 郑木香也没什么好说的,就只能依我的办。 我收起了这张图案,用手机照了相,然后把装满尸青腰的盒子在一处僻静的地方给焚烧了,并且偷偷用我给白萱的屋子配的锁钥匙打开了隔壁门,把这个胳膊藏在了地下室,如此一来我便放心了很多。 至于这个图案怎么去查,我可能还需要花点力气,但我不能告诉别人。 滴血的并蒂樱花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图腾吗?还是某个事物的密码?白萱寄给我这条胳膊的理由原因到底想要给我表达什么?我完全无法知道。 想着想着,我就跑偏了,还饶有兴趣地给这个图案起了个炫酷的名字——血樱双华! 我回去后,又是对郑木香千叮咛万嘱咐别乱说这件事,郑木香就很无奈地对我说她在武汉人生地不熟的,跟谁说去?我就特别指了指丁叔,到时候肯定是要照脸的,就当这事没发生。 她答应了,这是她的职业习惯,从不多嘴多问。 我们最近只能吃外卖,不敢怎么出门,每天我都要给方欣怡和陈一清做思想工作,他们我实在是不放心,期间我一直在网上去查找血樱双华的内容,根本找不到,甚至于都查到了日本黑帮山口组了,也没有一点信息。 我最怕的就是一个线索没搞明白,又来一个线索,这样的堆积会如乱麻一样搞得我发狂!如果白萱在我面前,我可能会跟她大吵一架,是她给了我一堆神秘的东西。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周末,我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发着呆,郑木香也无聊到不洗脸不洗头了,反正只能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 我每天寝室和租房两点一线的走,竟然觉得我已经不是我自己。 在以前,我每天其实也是这么过得,过着很普通很平淡的日子,上课,吃饭,家教,睡觉,偶尔喝酒撸串唱歌运动,如今我依旧是这样过着,却真的觉得这不是我了。 我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难道经历了那些真的就不一样了吗? 放空的时候,铃声突然响起,我的手机好久没人拨打,我接起来看了看手机号码,是未知号码,很纳闷,居然不是熟人,于是接起来问道:“喂?” 电话那头立马就是熟悉的声音:“童飞,认得我吗还?” 我立马笑:“这才几天,岂能忘却?丁叔好!本想着我到时候给您打电话呢,没想到让您劳驾了。” 他说:“哎,你就甭跟我客套了,你什么习性我都见识到了,敢跟崔爷这么说话的没几个人可。” 我尴尬一笑,说:“别别别,我还是很礼貌的,尤其是我尊重的人。” “这话中听!”丁叔似乎很开心。 我继续问:“怎么样?您和赵夫子的胳膊伤还好吧?” 丁叔兀自暗骂了一声:“她奶奶的,这娘们使些手段确实恶毒,怎么也想不到她的枪是指纹识别的,炸膛伤了胳膊,不过只是皮外伤,这都大半个月了,我俩早都好了!” 我说:“那就行,对了,您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儿?” 他说:“崔爷这边知会了我,让咱们见一面,两边联系熟络熟络,以后方便照应。” 我看了看郑木香,我说:“行!把郑木香也叫上?” 丁叔说:“也叫上!” 然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老大,外面有客户找您……” 丁叔就回我:“我有点事儿,到时候会有一辆白色现代车接你,车牌号鄂axxxxx,你留意着!” 于是我们俩商量在大学正门等他的人来接我们,他就挂了。 之后我就把这件事告知了郑木香,没想到这姑娘平时不怎么动,她一打开行李箱我一下子就惊到了,除下她的衣服单调些,化妆品似乎成了所有女性的必备装备,一箱子没见过的化妆品呈现在我的面前,其余的基本没有…… 然后她把我撵了出去洗了个澡,女的宅在家里一个模样,出门又是一个模样,我这小屋子卫生间特别狭小,估摸着还不合她口味。 我等了她很久,从这里可以看出,女人真的都一个样。 不过从另一方面想,我还是有些欣慰的,至少可以看出来,她对生活还是有一些活力与期待,似乎慢慢从除籍这件事走出来,老崔搞得这个见面确实有些作用。 等了一个小时她都没好,我也有点不耐烦了,然而正在此刻,丁叔的电话又打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