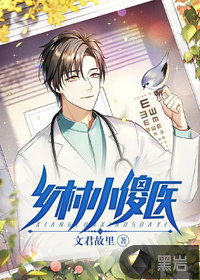这是在三秀意料之中的。虽然她有都达鲁花赤老爷的义女的身份,但她毕竟是个戏子。都达鲁花赤老爷的亲生子女何其多也,又怎会为着她一个戏子去得罪王府呢。“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出城,去沧州,或者回南边去。”三秀道。 瓶娘勉强笑了一笑,似是背后还有隐情,但她并没有说别的。而三秀也没注意这一切。 “是啊,毕竟还要活下去。”三秀也苦笑起来。 三秀大步出了屋子,走向父亲的房间。林庆福不在那儿。走到前厅,看见林庆福正一面揉着腿,一面向弟子吩咐事情,像是要收拾行装的模样。看见三秀来了,林庆福也就不再和徒弟们说话,转而向三秀点点头。徒弟见三秀来了,也不再说话了。 三秀看见,父亲的白发又多了几根。 “父亲。”三秀一开口便落下泪来。“我昨晚不该顶撞你。” 父亲爱怜地拍了拍她的肩: “我正要找你。有客人想要见你。就是朱公子。本来他于你是个极好的归宿,可惜你对他无意。虽说无意,也还是见一面吧。就在会客厅里。他是个正派人,你可以放心去。” 三秀擦擦泪水,道: “我们可是要回老家了么?还是回沧州去?” 父亲笑道: “先出城,走到哪里便是哪里。大有他们已经在装车了。你也莫难过,只当这大都城是我们的一个梦罢!” 三秀点点头,往前厅走去。一路上她看见这院中的老树,破破烂烂的土墙,还有墙边整齐摆着的刀枪棍棒,五色旗子,顿时觉得无限的悲伤。她忽然觉得,介福班就像是一棵蔷薇苗,移到了这小院做的盆里,好不容易开了花,又要拔掉了。 也许开过,就不用后悔了吧。 是告别的时候了!她正叹息着。不知不觉,已经就走到了门口。那里正站着一个翩翩玉立的锦袍公子,不消说,就是朱公子了。 两人相对行礼。 朱公子微笑说:“在下来这里,是与姑娘道别的。” 停顿了片刻,他又压低声音,说: “敝教出了点事情,要回波斯去。” 三秀有点惊讶,没想到朱公子也要走了。 朱公子又道:“听说你们班子也要离开京城了。可惜我们走的海路,不是一条道上。否则真想带你们一程。” “哪里的话。我们是外人,贵教行动秘密。也不好带上我们的。” 三秀说完,忽然注意到,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黑黑瘦瘦,脸上有刀疤的男子。 那男子她上次也曾经见城外的农舍家见过。当时,她就觉得他脸上的刀疤有些怕人。没想到这一次又见面了。 为什么朱公子身边会跟着这么一个人呢? 三秀这么想着,那男子却似乎是看出了她的心意,大大方方地向她施了蒙古人的一礼。这让她很惊讶。朱公子笑道: “吉达是蒙古人,我们的教友遍布天下——他会留在京城,这些天如果有什么要吩咐的,尽管找他好了。吉达,把风筝给她一只吧。” 那个脸上有刀疤的男子果然从怀中取出一个方胜儿,慢慢展开,如蝴蝶展翅似的,一层层翻开,最后展成了一只大风筝,黑红交错的颜色,眼睛和羽毛都栩栩如生,是一只燕子——看上去和城郊三四月时到处放飞的普通燕子风筝也没有什么分别。而就在刚才,它还是一个小小的方胜儿。刚才它究竟是怎样叠起来的?三秀看得呆住了。 朱公子又笑道: “你不是第一个如此惊诧的人——这风筝就是吉达做的。在这京城,不管城内城外,把这风筝放在空中,他便会火速赶到。他的眼睛就像草原上的鹰隼一样敏锐。” 三秀道了谢。还请朱公子坐下吃茶。然而朱公子却说不宜久留,道声珍重,便坐上车去了。只是那脸上有刀疤的男子,虽然上了车,却仍然频频向三秀回看。一次又一次,直到他们一行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三秀不知为什么,觉得他似乎不是在看着自己,而是在透过自己,远远看着另外一个人,一个似乎寄托了曾经的某些回忆,又似乎完全陌生;似乎在那里,但又无法触碰的人。……而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三秀始终不知道。她回头看看自己的身后,那里什么都没有。 风筝被她挂在了屋墙上。瓶娘抬头望了望,道:“这风筝,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时间流水似的过去,朱公子已离开三天了。介福班的行装早已经收拾完毕,大大小小十几只箱笼锁在屋中,都是他们谋生的物什。 然而谁都没说什么时候才能动身。三秀却注意到,父亲似乎怀着什么心事。每天早上,他都让何大有早早的出门。一出去就是一整天。这天黄昏,众人吃过饭,父亲又在门口等何大有回来。三秀站在她身边,父亲却好像当她不存在似的。 终于,何大有回来了。林庆福看见他两手空空,就叹了一声,说:“我看也不必再等了……” 三秀终于忍不住问起来:“大师兄是去做什么啊。” 何大有道:“去城门那里开出城的文书。” 林庆福想阻止他,但已经来不及了。 “怎么出城也要文书了?”三秀问。 何大有看到师父脸上不悦的神色,就乖乖闭了嘴。林庆福道:“没你什么事,你回去吧。” 三秀满心狐疑走回屋去,心中觉得这事情有点奇怪。忽然她想起,两天前从瓶娘那里听说父亲去见都达鲁花赤老爷的事,那时瓶娘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似乎隐瞒了什么。她正想该怎样问瓶娘,就看见了腹部微微隆起的祝双成在往桌上摆着碗筷,把刚才给丈夫热好的饭菜摆上来。 双成腹中的胎儿已经三个月了,正是要小心谨慎的时候。三秀连忙走过去,帮她张罗。双成感谢地笑了笑。三秀心想或许她知道些什么,想了一想,就道: “你现在的身子,舟车劳顿,不太方便罢?” “还好,现在又不能出城,不是正抓魔教么。” 没想到朱公子他们刚一走,城里就开始搜寻魔教的人了。 “唉,也不知这事要闹多久。” 双成抬头看了三秀一眼,似乎在想什么,然后淡淡一笑,道: “让他们闹吧。” 果然双成是知道什么的。 三秀决定套一套她的话。 “双成,”三秀做出一副沮丧的模样,“都达鲁花赤老爷那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听三秀这么说,双成松了一口气,接着就是叹息。 “我们还怕你知道,原来你已经知道了。世间竟有他这样趁人之危的禽兽……比不花还不如!三秀,你别自责,——我们不会让他占你一点便宜!” 都达鲁花赤要趁人之危? 这是三秀没有想到的,她惊呆了。 她想起了那天父亲听说她去陪酒时的暴怒,想起了父亲挥在自己脸上的一巴掌。那时她觉得委屈,现在,她总算有点明白了父亲当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