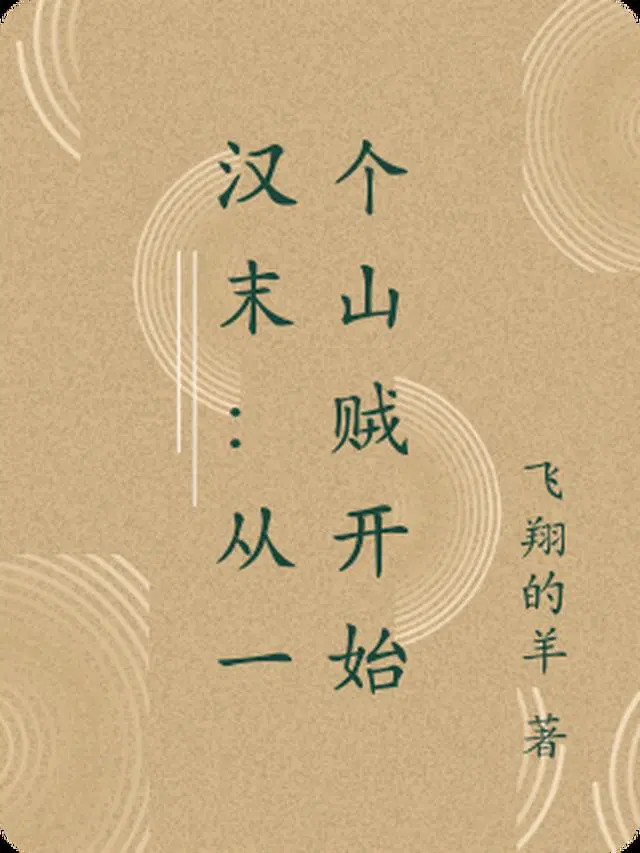三秀的话还没说完,瓶娘便已会意,脸上顿时一片愁云,低声道:“姐姐休要再提,瓶娘是立过毒誓的。” “毒誓?” “‘若在众人面前出了那瓶,终身不得行走。’” 瓶娘的声音越来越小。三秀听她这么说,水杏眼的瞳孔里又笼了一层阴翳。然而那阴翳也只是一瞬间,转眼便又是笑:“你呀,也莫愁了。程笑卿昨天打扬州回来了,我去央他写几支新曲儿。” “程笑卿。” 瓶娘低头重复了一边这个陌生的名字。三秀打趣道,“妹妹可要小心。要说有谁担得起‘风流倜傥、负心薄幸’这八个字,非他莫属了。” 三秀说得明白,瓶娘却好似听天书一般,神色钝然,询问地望向三秀。三秀又笑:“谁家姑娘要是让他给沾上,就得把方才那支《塞鸿秋》每日唱个十七八遍呢。” 瓶娘也不懂那支《塞鸿秋》的意思,只是见三秀一脸狡黠的笑容,便心知这不是什么好话,低下了头,忽忽不乐。 三秀便又觉得她可怜可爱了。 ☆、第 5 章 等到黄昏铺满小院四角的天空之时,瓶娘正一面绣着花,一面唱着那首“月呀月”的《塞鸿秋》。三秀则把胡琴搁在膝上,琴弓丢在一边,纤纤玉指随意拨着。斜阳从窗户口拉进来,爬上三秀的琵琶弦,爬过瓶娘的细密针脚。这日子似乎就是永远。 突然间,一阵犬吠自深巷而来,扰乱了平和的傍晚。犬吠的间歇里,依稀可闻男子带着醉意的声音: “……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三秀听见,停了手里的拨弄,转头看向瓶娘。果然,瓶娘的脸色已经煞白。三秀知道她必然是想到了不快的过往:曾经那个倚仗瓶娘混吃喝的男人,就是在灌了黄汤之后,对瓶娘为难的。 而就在这时,远处那男子突然低声呵斥起来: “……呔!你这畜生!……白养了你这么些年,‘三岁贯汝,莫我肯顾’,竟咬起吕洞宾来!你看那满路衣冠禽兽,白日横行,你却俯首帖耳,百般恭顺!……‘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瓶娘脸上的惊惧之色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困惑不解。这人骂得倒奇怪,“之乎者也”文绉绉的,竟然不像发酒疯的模样。她心中正奇怪那人说着什么,却见三秀“嗤”地笑出了声,好像早已经见怪不怪,将这当做惯有的趣事一般。她正要问,三秀早已转过来,道:“他来了。” 三秀话音刚落,远处巷子里又传来一个女子的温柔声音。 “程大夫您又醉了。何必和狗怄气呢。哎,仔细脚下!” “醉?……”那男子的声音渐渐平静,“‘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若举世皆醉我独醒,那醉的是我,还是你们?……醉?我可不觉得我醉……三秀呢?”那男子突然好似想起了什么似的,高声喊起来,“三秀!” 一阵砰砰乱响。接着是嘎吱开窗户的声音。 “唉,乱喊什么!”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泼辣好像玫瑰花扎人一手刺儿,“小妹你也真是,竟然还和他搭话。他黄汤灌多昏了头了,保不齐连亲老娘都不认识了,你也昏了头不成?——你三秀妹妹在后头院子里——别影响我们生意!”窗子吱嘎又阖上了。 屋里瓶娘听见了,慌忙看向三秀,三秀向她做了个“嘘”的手势。瓶娘便点点头,轻道了声“我出去了”,转而躲到了别屋。三秀刚欲说什么,瓶娘却已经走了。 “我刚才听见有人唱《塞鸿秋》。” 屋门口传来年轻男子的声音。三秀斜乜一眼门口,只见一名二十岁上下的男子正立在门口,一身月白衫子,腰间垂下一杆箫。 三秀没急着答他,撂了胡琴,一手护着灯盏,把灯燃了,待到窗上她巨大的身影不晃了才撒开手,冷冷道:“程大夫是尊真佛,巴巴的请了这些日,今天怎么忽而来了?” 男子淡淡笑了,满面春风。大概刚刚那一会儿别人给他饮了醒酒汤,神智比方才清明了不少,只是神色里的颓唐不羁依然如故: “自是寻春为汝归。好妹妹不放我进来坐下?” 三秀听见他轻薄的话,啐了一口:“谁是你好妹妹!还想进来坐,仔细脏了我这地方。” “好妹妹真是宜嗔宜喜春风面。妹妹的《塞鸿秋》唱得那样好,‘盼他时似盼辰钩月’,我这辰钩月也该回来了。” 三秀“嗤”地笑了出来,“又自作多情。那是瓶娘唱的。你整日眠花宿柳的,还不曾见过她罢?她可是我的人,才不是盼你。” 男子哈哈一笑,豁然里带两分自嘲,“是我马屁拍到马脚上了。和你这一番话,我算明白了。什么洛阳花、章台柳,她们的喜都是假的,嗔更是假的,不过是和恩客们虚与委蛇罢了。只有逗逗你这小娘子才有几分真趣。” 男子的语声转为惆怅。 三秀并不理睬他的感慨,只是回身大大方方地掇了一把交椅,道了声坐,又道:“别的话不多说了。你可愿为新来的小妹写点什么新曲儿?” 瓶娘并没走远。她正躲在屋后,一双眼睛瞧着三秀房屋的窗子出神。 夜幕已经降临,三秀的窗便是她面前的光明的来源。黑夜里,窗口的桃花纸把屋里柔和的灯光透了出来,也投上了两个人影,边缘清晰如剪刀剪过一般。 两个人影——年轻的女性和男性。女性是她所熟悉的三秀无疑。而那男子,大概就是方才在巷口喧哗的那位了。 因为方才已经见识了此人的古怪酒疯,瓶娘对此人的好奇渐渐升起。她仔细看着那男子的举手投足。他利落地向三秀一抱拳,随后潇洒地走到了三秀的对面坐下。茶水盛好了,他把茶盏端起来,随后以文人雅士才有的姿态,风雅地啜饮着。 他们二人继续着怎样的对话呢?瓶娘好奇地想着——屋里谈话的声音,是传不到她所在的地方的。 桃花纸透出的灯色明明如月,又如水。窗口栽种的兰草叶片背后透了光,便似水里的藻荇。一阵夜风吹过,兰叶轻摇,两个人影便好似在藻荇中游动了。 好美。瓶娘从心底赞叹着。 “这么看来,”三秀站起身子,“程大夫,你是不肯的了?” 那男子轻轻哂笑一声,“她?众人不过拿她当个玩物,玩腻了也就忘了。你还觉得她不够像个鸟雀儿,还要让她会唱,变成一只瓶子里的黄莺么?” “瓶娘她,不是玩物。” “也只有你这样想,也要想想别人是怎么说的——‘近来有个新鲜玩艺在“醉太平”……’” “不过是你这样想罢了,”三秀正色,“我不仅要让瓶娘学唱,还要让她从那瓶里出来,名正言顺地登台献技。她有成名角的天赋。曲子教她一遍她就会,至于板眼,从一开始就从没错过。你也承认了,她的《塞鸿秋》唱得很好。而这是我下午时候才教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