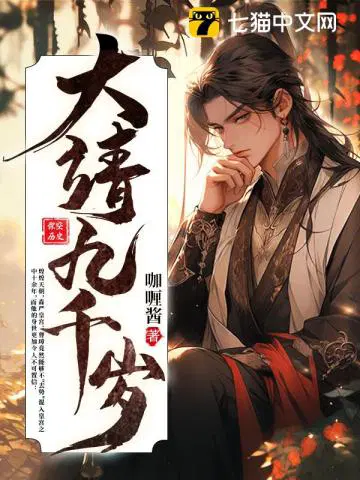后殿内。 曹璋不敢离开太久,又蹑手蹑脚地返回来,靠在旁边的柱子上闭眼养神地眯着墩儿。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了说话声,声音越来越大。 曹璋最先被声音惊醒,侧耳细听声音的来源,立时就瞪大了眼睛,这是皇太子张竚的声音。 他心中更加惊讶了。 是非之时的是非之人,竟敢如此猖獗地闯到坤宁宫来了。 不过这样更好,越是这般作死,他的太子之位就越是不保,就算太康要稳,那也被逼上辕门不结。 门外的声音逐渐地靠近了。 “你他娘的算什么东西?淫贱材儿下作种子,就知道在父皇后面拍马屁溜勾子舔屁股,也敢当爷的驾,你他娘的不想活了?” “太子爷!”这是刘全硕恳求的声音,“您省些事儿吧,万岁爷一宿没有休息刚刚睡下,奴才职责在身,怎敢放您进去?” 外面传来“啪”的一记清脆的耳光。 张竚喝骂道:“王八蛋!就凭你也敢在爷面前耍威风?给爷闪开,要不然,爷现在就要了你的脑袋!” 刘全硕苦苦哀求:“太子爷,您体恤体恤万岁……” 曹璋差异张竚的张狂跋扈的无法无天。按理来说皇太子张竚并不是笨人,为人平素也算和善,机辩才智,就算诗书学问那也是学富五车的,怎么会变成怎样? 难道是糊涂油蒙了心? “叫他进来!” 这当儿功夫,太康已经被外面的动静吵醒来,他掀开被子翻身跳了炕,气得浑身哆嗦的穿上鞋两步冲到殿门口,猛地掀开帘子,赤红着眼盯着外面的张竚,刁狠地一笑:“啊哈!是你呀!朕以为是谁敢这么大的胆子闯宫,半夜三更的来什么事儿?是不是太子手谕不管用,来取朕的玉玺?” “曹璋!”太康厉喝,“去,把朕的玉玺取来,让太子爷去调兵,朕等着他来杀咱们。” “父皇赎罪,儿臣万般不敢……” “你进来!”太康返身进去,坐在炕上,恶狠狠地盯着门口呆若木鸡的张竚,“进来!” 张竚怯怯地走进来,脸色苍白得像张白纸。 太康转脸看向杨立:“去乾清宫,把几位阁老叫来!” 杨立慌忙去了。 “父皇!”张竚跪拜在炕沿下面,“儿臣自知有罪,今夜前来,转为请罪,请父皇降罪。” “你居然有罪?!”太康阴森地笑起来,声音都变得尖锐,“朕哪里敢治你太子爷的罪?朕今晚吓得连觉都不敢睡,在反应慢点儿,明天你就能代替朕登基上位了。你还真是小看了朕,就凭区区几千城防兵也想造朕的反?你还差得远呢!” 曹璋第一次见太康如此口如刀剑般的骂人,非常吃惊,听着竟不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张竚跪拜:“儿臣知道今夜之事构陷已深,也辩无可辩,儿臣特来请罪,请父皇圣鉴烛照,罪在儿臣一身,世子还小……” “哈!”听到世子二字,太康冷笑起来,“你还想着世子?你还真是个好儿子好父亲,做得出如此辱没祖宗的之事,朕都难告天下臣民,你还有脸在这里说这些?你想拉垫背的朕还不许呢!” 张竚被骂得说不出话来。 太康气得狂躁不安地坐不住,站起身指着张竚对曹璋喝道:“快点把这个逆种拉出去,朕看到他恶心,拉出去!” 曹璋深知现在的太康已经到达暴走的边缘,慌忙跑过去搀扶着张竚起来,满眼恳求之意。 张竚不敢停留,被扶起身,哈着腰出去了。 刚将张竚送到门口,就瞧见贾深、姜品、岳山棋和董路迤逦往进走。 张竚看到贾深,慌忙跑过去,带着几分哭声恳求道:“贾阁老!贾阁老…我没有写过什么手谕,皇上愤怒之极不听我言,求阁老救我!” 众人劈面相遇,贾深等人诧异造反的太子怎么会出现在坤宁宫? 面对太子的苦苦哀求,贾深不答应不行,答应也不行,思索着说:“太子稍安勿躁,且回东宫稍作休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太子只要问心无愧便可。” 太子满脸凄楚,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贾深不敢过多的交谈,松开他紧紧拉住的手,快步朝着后殿走去。岳山棋则是冷哼一声,仰头擦肩而过。 董路走到张竚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他一个安慰的眼神。 张竚软软地站在那里,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 整个人像是抽去了魂魄的行尸走肉,眼神空洞,垂着双臂提不起力量。 “太子爷!”曹璋在旁边提醒,“晚上冷,您先回去等吧,好歹等皇上的旨意。” 张竚没有说话,拔起脚,摇晃着走出门去。 早有门口守候着东宫的太监慌忙扶住张竚,坐上轿子,朝着东宫而去。 曹璋站在门口,望着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模糊影子,叹了口气,转身返回后殿内。 刚进到殿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贾深等人的惊呼声。 曹璋慌忙冲进去,就看到太康倒在炕上昏迷不醒,贾深等人惊得面如土色,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命人传太医。 好在温实初就守在坤宁宫。 他早就静静地守候着,听着外面的动静,当听到里面传来急切的呼唤声时,他就有了预感,一把抓起行医箱,冲了出去,差点装上刚进门的曹璋,他立马守住身子,点头示意。 曹璋侧开身子让他先进去,然后自己跟着进去,站在侧面不动声色的看着昏迷的太康。 陈渊这个时候也走了进来,他先是看了昏迷的太康,在看了看曹璋,悄悄地站在另一侧。 今晚上不是陈渊当值。 他现在进来,恐怕是想赶上今晚的大变。 贾深等人围在炕沿边,神色紧张万分地盯着温实初下针,温实初这辈子行医扎针无数,也没有被这么多的大臣盯着,浑身竟然冒出汗来。 所有人都屏声静气。 整个大殿又恢复了之前的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