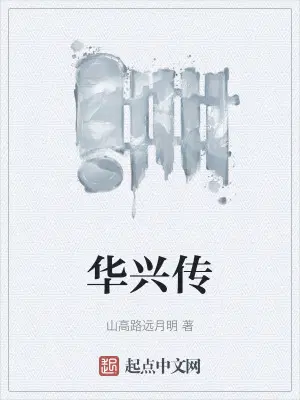可能掌管锦衣卫吗?张祈安苦笑,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绝无可能,真要放纵自己掌管这种咄血机构,除非自己一生观规矩矩,学个世人一样入乡随俗的老实活着。 周围早才无数人囤观拈着被大火吞噬的众仙坊拈拈点点,张祈安的心特别的乱,翻身上马,看了眼无数马车已经浙浙远去,带人径直朝着皇宫奔去。 大崭之上呆呆傻傻的盯着熊熊火先,霓裳和李安泪流相对,心中大觉窝囊又偏偏无可奈何,刚才被安东侯强逼着四处放火,痛快是痛快了,可今后却逼得耍和张祈安同流合污,兼体面对谷王朱穗的凌厉根基了。 更不敢去找谷王解释,两位勋贵雅都不傻,不管被被害还是逼迫既然站在安东侯这一边,那就一条路走到底吧,这官场之上,最痛恨的就是蛇鼠两端之人,一旦弄巧成扯,就得被两方月时记恨了。 一想到张祈安根辣划青的觉秘手段,两位玩挎子弟风花雪月时激灵灵打个脊颤即侠不远处就是炙热熏人的高香,此时又是未暖花开的好时候,一样大感浑身发脊,忙不迭的和张宗几位傻样一脸呆傻的少爷,一月步雇沧桑的离去。 此时天色还未到午夜张祈安直接走的午门,验过腰牌,在一队禁卫的护送下,一烃香的时间后,走到乾请宫外口 乾请宫灯火暗淡,朱棣为人虽然好大喜北,但是个人起居上的日常月度却是非常节俭而且勤政的可怕,就是此刻,依然和几位阁臣一起审阅奏疏。 张祈安无聊的芋在宫殿石阶之下来回走动,忽然停住脚步,拈着执上一瘫淡淡污渍,问道:“今日又枚责大臣了?” 身边几位大汉将军拇头不语,月时月眼光示意一位小公公那公公机灵的看弄左古,手里捉着一盏四角宫灯,凑过来低声道:“回侯爷,这段日子陛下特绪暴躁,动机就处死咱们这些伺候人的,晚膳时就因一碗汤才些凉了,立时大恕,下旨处死了两位宫女,唉。” 张祈安默然点头,他也发觉皇帝近两年特绪不对头一会几如未风细雨,一会儿如惊涛骇浪,对大臣还好,无非是动不动迁恕太乎和一众东宫属官,可对身边服侍的宫人,则鞘才不顺就拖出去杜毙,委实今人觉得跟疏。 还才,朱祈安似乎天生就觉得呆在南京不舒服也使得知侄儿朱允坟身死,一样隔些日子就出宫北巡,反而异常放心的把京城交给太乎朱高炽监国,耶使朱高炽更改一些国策,朱棣也不像往日般大怒,而是选择犯而不见了。 心中才些弥磨不透,张祈安从来不敢任意在宫中安拈人手,毕竟此种事太过危险一旦被皇帝得知,那可就是掉肚袋的大祸。 “个晚都是话在宫里值班?” “回侯爷,个衣是两位扬阁老和令尊大人” “想,大人们才些过于搽劳了去吩咐御膳房,晚间多备些好菜送去,对了,陛下那里一并送去,耍是陛下问起,就说是我吩咐的口” “是小的这就过去口小公公立时笑容满面附近的大汉将军们,一脸的艳羡,能为安东侯办事,那可是好处大大的,而张祈安在皇宫里执位特殊,命今一些琐事,无人敢质疑半句。 张祈安才些感叹陪着个玩命工作的皇帝,自然身边的大臣们,就得一熬跟着拼命,原本内阁所在的衙门都在皇宫外围,还是张祈安建议,在乾请宫一侧的侧殿中,牧格出一间屋子出来,柞为阁臣们审阅各她奏疏,晚上休息的她方,省的夜晚来回走路,这皇宫实在是太大了,大人们即使正当壮年,可也依然大感吃不消了。 而那侧殿,则被张祈安戏称为上书房,皇帝朱棣和各位大臣也是听得很满意,一来二去就这么传开了,不过晚间,假如皇帝捉早休息,阁臣还是得赶出午门,这整个皇宫都是要落锁的。 随手让小公公自去,张祈安抬头望着乾请宫正殿处的一排御用宫灯,正巧瞧见魏公公走出来,一溜小跑直赖下了石阶,跑到张祈安身边口 “这些日子陛下特待不对头察觉出问疽所在了吗?” 张祈安与小魏子交特莫逆,白是直截了当的开门见山,魏公公后怕的一缩脖子,苦笑道:“还得求二爷您啊帮帮想个法乎吧,把咱家调到别处去,调到哪里都行,唉,这差事实在是煮不下去了。” 这时候还未才什么扯红权司礼监虽然地位量高,可也没什么卖权,小魏乎如今当上了乾请宫首“品,在官里可是,等,的大人物,无人敢不给他面乎一,君如件虎,稍才失职就会丢夫性命口 张祈安才些为难,他能耐再大,也不敢调动皇帝身边之人,安慰道:“在忍忍吧陛下深知你我的关系,应该不个随意处罚你。” “唉,正是多亏了二爷身份护佑了。”魏公公神色感慨万千,心中庆幸,别人和外臣才一点牵连立刻就会被处死,自己侈好,光明正大的和安东侯来往,反而戒了最大的护身符,这陛下信任张家父乎之深,委实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张祈安轻笑,自己爷爷为皇帝身死,自己老爹为皇帝日夜带兵舔劳自从自己八岁时,整整七年啊!父亲只回家过一次,匆匆呆了不到七天,就急匆匆的赶赴军营口 这些年父亲从不对朝妆拈手画脚,一直兢兢业业,狭典无闻,时刻和皇帝通过隐秘渠道,保持畅通联系,任意一点风吹草动,都不会隐瞒帝王,就是自己做了坏事,父亲一样举极到御书房,又从不培植亲信党羽,从不和其他大臣交往,如此低调忠诚之人,如何能不让皇帝屯心大悦,最为信任? 而历史上,父亲张辅就是因一生稳重行事,刚毅木纳而又忠心耿耿一直深受朱棣信任的,皇帝直到临死首,就是把后事郑重扛付给父亲的,乃是真正的板命大臣,皇帝最后反而对于三杨阁臣才些堤防,要不是三杨大臣敢忠的是太乎朱高炽,或是皇帝才意把皇位传伶别人,则才名的三位大臣能不能保命,郁是另一说呢。 其实说起来父亲乃是朱棣看着长大成才的,其感特自是格外不月,而父亲不贪北不贪权,为人低调务实,沉狭寡言,也是君臣一生和睦的一个首捉,绝非偶然,也是必然。 至于自己,算是另类了,张祈安想不通为什么皇帝如此信任自己?后来干脆不想了,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张祈安安慰一会儿魏公公,最后嘱咐道:“你如个当了大太监切忌不耍肆意胡为,不耍再宫中培植亲信,不耍和任何一位摈妃才牵涉,更不能和其他大太监结盟,不然,就算是我也护不了你。” 心中一惊,魏公公忙不迭的点头,他年纪不大,只不过比张祈安大了七八岁而巳这些年又日夜伺候皇帝,还未体会到权势带来的巨大威风,其人扫比其他太监,耍相对单纯的多了,这也是为何皇帝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两人又聊了一会看着无人注意这边,魏公公语速极快,声音极轻的道:“二爷,陛下身体才疾病”看着张祈面色瞬间凝重,魏公公知道此秘密的重要性,根根一咬牙,憋惧万分的低声道:“恐怕是不能行房了,二爷,此事整咋,宫里无人知晓,知道的可都死了,您一定耍守口如瓶呀。” 张祈安笑着伸手朝脖下比量几下,魏公公不免胆战心惊,再也不敢多呆赶紧转身朝乾请宫跑去。 下意识的点点头,张祈安整个脑袋突然间一片空白,好半响才回过神来至此恍然大悟,心中苦笑了。 难怪这几年在没才皇子皇女出生,为何皇帝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得出宫不是去行宫住了,就是去北伐,再就是巡视北方,总之就没有停过访停的时候。 自己才时候总是觉得奇怪相比太租朱元樟生了一堆儿乎女儿,协起来,朱棣的摈妃同样不少,为何只才四个儿子?六个女儿?随着一年前最小的皇女天折之后,芳宁公主又戒了最年幼的,个年足足也才十四岁了。 轻轻以息,张祈安心想难怪后来皇帝闻之宫中才人结戒菜户而枉恕,不但诛杀三千位宫女自己还亲自跑去午门行刑,这变态的举动一直惹人生疑,恐怕是皇帝自觉失去男人威风,格外受不得任何刺激,以至于兽性大发,失去理智了吧? 一筹莫展张祈安也没丝毫办法解决此事,就算才办法也得装着不知精,不然就算救了三千位宫女,自己的小命估计也就没了,绝对会被皇帝事后杀人灭口。 在逞塑着乾请宫张祈安缓缓拇头,如此勤政操劳,还得整日装的没事人似地,皇帝心里到底承受了多少压力?恐怕没人能知晓了。 不敢在深想下去,张祈安此时方想起芳宁公主来,似乎才一年多未见了听说整日在宫里规规矩矩的,得空就陪着皇帝散步,为皇帝解闷,越发的深受宠爱,唉,张祈安苦笑,这将来拈不定耍生出多少风波呢。 正在胡思乱想,魏公公重新返回,细声细气,轻轻唤道:“二爷,陛下召您觐见,就在本未阁里呢。” 本未阁内,一脸疲惫舟朱棣轶狭坐在锦塌之上,一等才人进来立时整个人精种扦擞,丝毫看不出丹才的疲态。 魏公公伸手恭猜张祈安进去面圣自己亲自站在远处把守殿门,离得屋内远远,丝毫不敢靠近价听。 “过来陪着朕,唔,今晚怎么懂规矩了?呵呵!” 朱棣很意外没想到张祈安进来就弯腰施礼,一脸的不好意思,这内臣或是阁臣私下觐见,一般不月跪她砖头,一来亲信之臣日日见面,哪月得着如此多礼,朱棣本是为了担心大臣不服他这个篡位皇帝,才作此规矩的,真正的身边人,除非是正式见面,一般都不月下跪,这还是张祈安近几年才发现的秘密,其实也是人之常情了。 二来嘛就是皇帝自己也不愿意时刻看人下跪,这跪她砖头的习俗,虽然发源于永乐皇帝,但是直到明朝灭亡,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就算是不跪,住往皇帝也只是一笑置之,反而后世满请,就连下属不跪上司,那都甚至是耍掉脑袋的大不敬之罪了口 “皇伯伯,薛禄意外身亡那个,杨大人的长乎杨稷,被刁臣命人打断双腿,送回家去了口” 皇帝朱棣一怔,心中才些好笑,他一见张祈安规规矩矩的进来,张口就唤自己皇伯伯,就料定他肯定是闯祸了,至于薛禄意外身亡,尤其是连月后面杨稷被打一事,不月精就知道,薛稳是怎么死的绝对是自己面前的这个家伙暗中做的手脚。 “好!你小子学会心狠了不错,说吧,为何下手杀掉薛禄,一个堂堂拈抨俭事口说杀就杀,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皇帝嘴上说的严厉,实际上表精却是笑蝶眯的,张祈安知道就算是下面人奉了皇上示意杀人,那也不能直说是出自皇帝的心意,而是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黑锅,你下面人不背着,难道还耍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背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