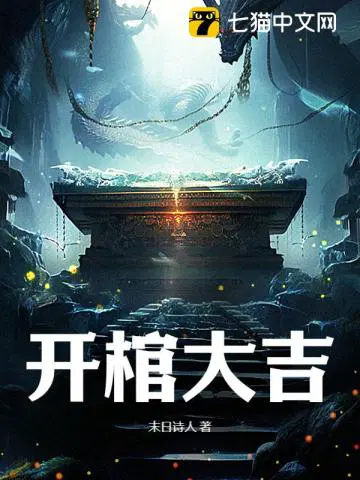我们是夜里十点多出发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下山,已经是将近一点了,然后又一路步行到县城,抵达时,天都亮了。 现在想来,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火力是真的壮。 深更半夜,寒冬腊月的,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在那黑灯瞎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山中,还真有可能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但我们那时候甚至都没觉得冷,只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抵达县城后,我们几人找了一个早餐店,点了三十个包子几碗豆腐脑,狼吞虎咽的吃完后,便火急火燎的直奔火车站,买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票。 当天上午,我们就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绿皮火车,因为昨天一夜没睡,再加上走了一宿的夜路,上车后,几人便做着发财梦相继睡着了。 这一觉睡的可谓是昏天暗地,醒来时,火车已经抵达了哈东站。 我们几人迷迷糊糊的下了车,但下车后,我们几个涉世未深的生瓜蛋子,便被这个操蛋的社会给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课。 我们的钱丢了! 几个人的衣服兜全都被掏了,我奶给我的那把零钱和我在县城买的吉庆香烟全都不翼而飞,兜里只剩下一盒没剩下几根火柴的火柴盒。 “咱们这是遇到扒手了,三金子你快看看你的钱还在不在。” 我们这几个人带的钱加在一起都没三金子带的多,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可全指着三金子呢。 听到大雷子的话后,三金子急忙拉开身上背着的挎包,他先是一愣,随即将挎包举过了头顶。 这时我们才发现,挎包都他妈透亮了,挎包下面,被人用刀片平平整整的割出来一个大口子,除了我们几人的身份证还在挎包的夹层里,其余东西全都没了。 二柱子凑了过去,隔着挎包透亮的窟窿和三金子大眼瞪小眼好一阵,最后竟‘妈呀’一下就哭了出来。 “麻痹的还想着去南方发财呢,这东北还没走出去呢,钱就没了,我这命咋这么苦呢!” “别特么叫唤了,你们看!”大雷子忽然眯着眼睛,用下巴点了点不远处的一个男子。 那人穿着一身军大衣,戴着棉帽子,双手缩在袖子里,他也是刚下车,此刻,正鬼鬼祟祟的跟在一个女人的身后往外走呢。 而他的手,已经凑近了那女人的背包,手指间夹着一个小刀片,正一边走,一边轻轻的割。 “狗日的,走,弄他!”大雷子‘呸’的一声吐了口吐沫,然后就冲那个男人走了过去。 我们三人对视了一眼,然后也快速跟了上去。 “哥们,你手挺长啊?”大雷子走到那人身后,一把拍在了那人的肩膀上。 那人被突然出现的大雷子吓了一跳,转头一看,见是陌生脸孔便骂道:“你他妈谁啊,我手长不长,关你啥事?” 说完后,还一扭身,然后一拳怼在了大雷子的胸口。 大雷子人高马大,被怼一下连晃都没晃一下,反而喊道:“草泥马,给我干他!” 说完后,大雷子冲上去抓着那人胳膊就是一个扫堂腿,直接就将其放倒了。 我们几个在十里八村的,没少惹事,打架那都是常有的事儿,此刻见大雷子动手了,我们几人也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对着那人就是一阵圈踢。 “差不多行了,把钱要回来,咱们赶紧走!”三金子在后面劝。 但三金子话才刚说完,我忽然就发现不对劲了,人群中,竟然有不少人在逆着人流往我们这边冲,而且人数极多,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把我们几个给围住了。 “麻痹的,敢打老子,给我揍死这几个小逼崽子!”被打的那人捂着鼻子,含糊不清的大叫了一声。 他这一叫之下,周围的人呼啦啦的就冲了上来。 他们人数太多了,就算我们几个打架再猛,但也抵不住这么多人的围攻。 虽然时隔这么多年,但我依然记得当时那如雨点般落下的拳头和几乎踹出了残影的脚... 足足被围殴了几分钟之久,那群人才骂骂咧咧的散去,只留下我们哥几个,蜷缩着身子躺在地上。 都说人生就像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 而现在,我们哥几个,就是悲剧中的悲剧。 因为被打的太惨了,二柱子的鞋都丢了一只,我的军大衣都被撕扯成坎肩了,两条袖子被扯了个粉碎,里面的棉花洒落了一地。 “你们三没事吧?”大雷子率先爬了起来,‘呸’的吐出了一口带血丝的吐沫,然后恶狠狠的说道:“操他妈的,这个仇必须得报回来,走,找他们去!” 说完,大雷子就过来扶我们几个。 “唉,你们几个小伙子惹谁不好,怎么就偏偏惹那帮人!”一个保安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摇着头说道:“外地来的吧?那帮人在这里蛮横惯了,你们挨顿揍算轻的了,听哥的,赶紧走吧,不然到了晚上,你们还得挨揍!” “他们咋那么牛逼呢?”大雷子瞪着眼珠子,一脸的不服,但三金子却拉了拉大雷子,说道:“走吧,咱们认栽了!” 说完后,便拉着大雷子,一瘸一拐的往公厕的方向走去。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保安模样的人,和刚才那群人是他妈一伙的。 这群人的套路就是先偷,偷不到就抢,你护着就揍,揍完之后这个穿着假冒制服的人便走出来连唬带蒙的善后。 那时候的人都不咋懂法,被这么一通说,大多数人也就自认倒霉了。 到了公厕后,三金子解开裤腰带脱了裤子,随后竟然从三角裤衩前面的兜里,掏出了十张五十面值的钞票。 而大雷子也脱了鞋,分别从两双鞋的鞋垫下,拿出了六张五十的。 “你俩还有钱?”我惊了,二柱子也是眼珠子瞪的溜圆,刚才还哭丧个脸的他,此刻又笑了。 “我艹,我还以为没法去找四毛子了呢,这不又好起来了嘛!” “走吧,先给二柱子买双鞋,老幺你...”大雷子看了我一眼,随即说:“你就把军大衣当坎肩穿吧!” “不用买鞋,伟人说过,钱得花在刀刃上,走,咱直接买票去!” 当天下午,我们再一次坐上了绿皮火车,有了上次的教训后,这一次,钱都被三金子藏在了三角裤衩的兜里。 而二柱子也确实是个汉子,真就光着一只脚,跟我们一起再次踏上了征程。 我们几个被打的够呛,坐在车上浑身疼,也没了睡意,就那么呆呆的看着车窗外飞退的雪景愣神。 至于二柱子,却是被冻的直哆嗦,透过那双已经包了浆,还露着脚趾和脚后跟的袜子,可以看到他的脚都被冻青了。 最后我实在不忍心,就敞开了军大衣,将他的脚丫子抱在了怀里。 也不知道二柱子多久没洗脚了,那味儿不仅呛鼻子,还他妈辣眼睛,这一路上就别提了。 因为我们几个身上就八百块钱了,且还不确定多久才能抵达云南找到四毛子,所以接下来的这一路,我们几个全都勒紧了裤腰带,除了给二柱子买了一双黄胶鞋外,其余地方都是能省则省。 饿了就啃提前买好的冻馒头,渴了,在有雪的地方就吃雪,没雪的地方就忍着,看见人家后,就厚着脸皮去讨水喝。 而我们剩下的钱,几乎都花在了车票上。 通火车的地方就坐火车,不通火车的地方就坐大巴,不通大巴的地方,我们就噌过路的货车和拖拉机,如果连拖拉机都没有,那就只能开动11路了。 就这样一路边走边打听,终于是在半个月后,抵达了信封后面写着的地址。 云南省怒江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这一路走来,我们哥几个风餐露宿的,造的已经没人样了,此刻进入县城,立马就引来了无数异样的眼光。 至于我们哥几个,站在县城的街头,看着满城都是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少们,已经彻底傻了眼。 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唐僧来到了女儿国,彻底打开新世界了。 而紧接着,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悲催的事。 那就是这地方的人跟本就不说普通话,说的全都是我们听不懂的方言。 而且方言还分好几种。 我们唯一能听懂的,就是一家音像店播放的王菲和那英合唱的那首相约一九九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