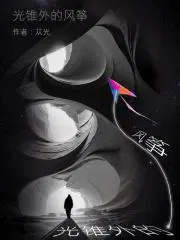真龙睁开眼睛后,两眼却还是无神,好像没有聚焦。 “你好~怎么称呼?”王轩兰在他眼前晃了晃手,问询道。 修铭也靠近了过来,此方天地的诸多视线,此刻都在这真龙人形上。 “稍等一会,我看他还在重建着意识,也在用余光重新扫视着这片天地。”修铭提醒道。 修铭也不确定是如何的流程,死者复生无论在何种地界,都是一个禁忌的议题。 王轩兰点点头,别过身去不想与修铭说话。 修铭无语,这大小姐有时真的不像是一位将主。 一阵无话。 真龙人形的瞳孔中出现了神韵,一瞬间他的瞳孔深度好似被无限拉长,像是浑水为之一清。 “我本名为真,此番相争我已有所知,残余新念也种下心头。水生莲之事,还需谢诸位手下留情。 龙族旧恨扰动新向开辟,是故我之罪。 铭与骄,我会帮助你们,以偿还业债。” 真龙人形有着不同的超凡视界,或许与这人形过去所见有关,或许与莲子所见有关,或只是他一眼就看穿了还未深没的历史潜景。 与之对话,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甚至目光都会给人一种窥破人心的洞穿感。 修铭则有些在意真前辈对两人的称呼,他们没有自我介绍过。 更未曾对此地之人去姓留名自提过。 姓是名的前缀、定语、分类、归属...... 但是更本质的自我,一定是在名上。 真龙,真在前,龙子,龙在前。 铭与骄,则代表着他们可以浮现的最靠近本质的字。 王轩兰旧身,更应该是八向之地少知的隐秘。 他却只用了一眼。 修铭这一路见多了至上之人。 但无论现在隐藏在云雾后的天族将主,虚弱的金忌,半吊子的石至,他们都似乎要差上眼前真龙一些。 或许只有在风星惊鸿一瞥的武威,或许只有追溯时光全盛的王轩骄,或许还有那个未知的神,才能与眼前人相提并论。 或许,只有他们才能够触摸到斑斓至高。 那么是什么能将他变成现在的模样? 也许不止是外力。 “还债吗。我明白了,新向建立非一朝一夕,我王轩兰承此助,也自承袭一部分业债。 诸端落定后。龙,会有一席之地。”王轩兰严肃说道。 真龙人形却轻轻摇了摇头。 “业果繁盛,唯有填意。债不可传,更不可转移,龙也有自己的命。 不强求~不强求了。骄,你已经看向前方,便可不顾忌身后。” 真龙人形却拒绝了王轩兰的好意,脸上浮现了唯一的表情是洒脱。 “那便如你真意。”王轩兰直接应道,他们之间说话已经很难打折扣。 “意气之争、方向之争,动辄毁天没地,沉骨断苗。这一次你们做的很好,所以希望也最大。 八向旧人尽数以身偿债,最后需要靠二位外人救我族地,是我们欠你们一声感谢。”真龙人形说话间隐隐有叠音,好似无数人齐声颂念。 说话间他叠了一个古礼手势,微微欠下身子。 修铭赶紧制止道: “我她皆有私心,真龙勿怪便好,怎能受您之拜。” “人皆有私心,我看到的是二位给八向努力的行迹,身为罪龙二位却为我等还账。 该感谢,却也远不是感谢所能包含,也罢,不提了。 此番一回,旧人不可入新向,更不可干涉。 我也不行,然有些旧人不愿退场,这些拦路虎是本真唯一能够帮助二位的理由。 而后即便是新路未辟,旧道崩阻,那也只能是天地该合之相。 也请二位愿赌服输,留下一丝微末的可能给后来人。 真龙在此相求。”真前辈话语逐渐诚恳,让修铭心头发堵。 “哈哈哈哈~你这真龙,还怕我王轩兰赖在赌桌上耍赖皮,哼~我看这才是你真正在意的事情。 不过你放心,我王轩兰赌品奇好,再重的砝码我也赔的起!”或许是戳到了伤心事,小姐的语气又生硬了起来。 “真前辈放心,事不可为时。我们会尽量携带多的人离开,也会努力给这方天地留下一抹余韵。”修铭努力找补着,与小姐说话截然不同。 “哼,说什么丧气话~”王轩兰小声嘟囔。 “铭与骄,前路在二位眼中,本真不该干涉,刚才已然逾矩。 我们说回正事,二位可了解此番敌手?”真说道。 修铭看向王轩兰,她不说话。 “我不理解,她嘛~不知道。” “那好,本真先给二位介绍一下。 毕竟有些事情过去太久,这片天地也只有寥寥几人还知道。 而要说清那人的根底,或只能唠叨一二了。”真先打预防针。 “还请赐教。”修铭求之不得。 “好。”随后真一挥手,与龙宫内部出现的老龙浮相类似的雾状体,凝结成为不同的画面,辅助着真的讲述。 “从八苦城溃后开始,八向之地经历一段漫长的浑噩明暗不分时期。 但因为本真与几位故友,并未在那场劫难的中心,所以侥幸存活了下来。 或许是规则不明,导致天地无法沉淀,池满则溢。 那场灾祸倾倒了八苦底蕴,殃及了亿万生灵,却也成就了我等少数几人。 我们几个幸运儿,也间接的庇护着一些未曾完全褪相的生灵,一同渡过那段艰难的时间。 而这些生灵便是如今的大部分八族。 时间无算,月相难明。 我们也昏昏睡睡,底蕴再厚也在一点一点的泄去,几位老伙计都知道,这依然是一条绝路。 我们需要改变,这片天地需要分类过筛沉淀出形。 然而何种形?最后沉淀出什么相? 却让我们本就不深厚的情谊快速耗干。也是,围起高城后这一难题都无法解决,现在处境艰难,问题只会显得更加严重。 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当时的我们,大多也无形无相,彼此不对付产生的碰撞,也殃及不大无辜的生灵。 往好的一面看,新天地的形相,还是在折损了一部分老伙计后,逐渐在各自的心中成形。 它有着不同的方向,但总算是从一个点出发。 做事在人,成事更在人和啊。” 真前辈说的唏嘘、感慨,修铭听得却有些恍惚。 因为凝雾所现,真龙所言,他有些似曾相识。 修铭~修铭,作为人的他是在五名城出生,可是作为水下地景仙灵的它,却并不知道那个不完整的自己从哪里开始。 记忆的藩篱里面,也是不如外面看着丰茂,大部分都是重复且雷同的麦穗。 修铭的质,溯源也是一个无解。 这却不是现在的机要,或许他的问题,也只能等到斑斓时空在他眼没有秘密,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真前辈继续说着,修铭已经怀疑,这个真前辈可能还真的是他的真前辈。 “开天辟地,是一件很繁复的活。 现在所说已然是一种失真的转述。 按照既定的形体,将物相定好位置,一点点的解离各自的底蕴,游离的灰质。 再重新黏合到一起,并且让其有着自身的代谢循环,不会在天地大潮中随意的消散无形。 争斗起到了一定粗筛的作用,但更耗费时间的,还是细筛。 质当中的绝大部分内容物,并不适合在尘世浮现。 标准又是另外一个麻烦事情,由标准不一引起的水线之争,差点让刚刚起步的新天地崩塌归虚。 唉~又是几位老伙计身消,水线才能堪堪定下。 这之后,这里潜景与浮相,虚假与真实,过去与当下,质、形、相的模糊边界,方才初步有了形体。 水线高低影响着天地里生灵的能量阈值,认知结构,人心深度等等无法被忽视的核心参数。 我们大多认为,水线要定的低一点,尽可能接纳更多的潜景之灵。强大整个天地的内生生命力,即使因为这样会乱一些,也无妨。 而反对我们的人,认为人性本恶,人力所能企及的重点,终会变成压向其他生灵、压向同类,甚至压向天地的毁灭之锤。而这份破坏力,也由着这份水线决定。有可能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 他们认为水线要高过晦暗人心,让见不到光的心,烂死在见不到光的地方。而不是给它们机会,成为天地决裂的线头。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美好的冀望,能力越大破坏力越大是不变的事实。 我犹疑过,他们说的有道理。 但这份类似阉割的做法,我很难认同。如果天地的桎梏终会被打破,那么或许只有强者才能生存,更多强者不就是更多的生存? 而且还有一个条件。 当时的我们或许难以启齿,却众所周知。 水线也等于创世者的死线,如果我们设计制造的世界,却无法容纳己身。 那成世的那一刻起,被深埋在下无法发生的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呼吸所需的营养。 所有创世者都无法生存在这过于低矮的天空,会被逐渐的淹没窒息而死。 这或许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是为自己创世,还是为了身后的生灵创世? 我曾拷问过自我。 却没有答案。 直到另外一个理由欺骗了我。 强大是足以遮目的大山,望二位多走到人间观看,不过现在看起来,你们比我们聪明。 那时的我们太强大了。 创世是神的私域,而我们俨然已同于神。 神身人性,让我很早就陷入了盲目的自信,直到最后。 这种自信,让上个问题不是问题。 忌惮强大的生灵打破天地,那便给所有生灵头上增加一尊神。 我会看着世间所有人,也会照拂着世间所有人,更会守在艰难建立的新世完整! 我就是那位神!天地间的唯一真龙,众生之上的唯一睥睨者。 我从来不会犯错,更没有一点私心。 几位老伙计更是只愿相信我一人。 八向初见形梏,我平衡的很好,每个方向都在向前,每一个人大多满足身体所需、内心所想。 在这样一个不断向上,万物新开的全新世界里,答案比问题多。 一切都在以比想象更美好的速度前进,八向成形,不慕八苦! 我缔造了一个盛景,守住了巍峨高城守不住的东西! 力量在我,人心在我,方向在我,所以世界在我。 我独行于前,天地景从,无人拂意。 天地既我,我既天地!” 无可比拟的峥嵘往事,让真前辈也语气狂热了起来。 修铭既艳羡其中的风光,又遗憾眼见紧随而至的落潮,恨不得亲身踏入时光,提醒真前辈他醒一醒。 眼睛不能一直抬头看天。 “后来呢?是不是高看自己了。”浇冷水者,王轩兰小女子也。 修铭“啪~”一下拍在自己脑门,她不懂事情,我尴尬什么啊。 真前辈气养如海,饶是没有挂相,但还是因为意外停顿了一下。 “抱歉啊~活的太久,每一次重述过往,都是一次浸润在幻梦中的重活。 遗憾与美满皆是过往,此中暂且不提了。 本真还是为诸位先行解惑。 便是那亿万地灵,千万言灵,与那唯一人神——明。” 修铭已经拿过子浅浅的笔开始记录,他不会遗忘这事,这笔记是为了酣睡的孩子所做。 王轩兰眼高过顶,却还是忍不住地偷瞄这边。 她无论还有多少隐藏的信息渠道,都不及眼前几乎经历了一切的真形,所知道的全面与真实。 真前辈继续说道: “新的天地,会孕育新生的灵。 初时他们很弱小,也不识乾坤,总得彷徨。 天地很苍茫,八苦余蕴所造遗民,与新在我们的统御下安然生活了许久。 然而黄金的时代无法长久,较低的水线,让这片天空过高。 有底蕴的生灵,都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生长着,很快这片天地就变得拥挤。 而就在那时,我开始被质疑,一些激进群体当做敌人。 问题是不在于我是否公平,不在于我做过什么? 只在于我的存在,也许这并没有错。 如果要为后来的内战找一个罪人,那也只有我有资格成为那个罪人。 各族间的大战,以一种无法控制的方式爆发了。 即使当时的我,也无法找到谁才是那个首先举起屠刀的人。 因为我先看到的那人,是以复仇的名义开战,而他要复的仇是别人血的恨。 我不再公平。 我也无法公平。 我不参加战争,也阻止绝大部分高层涉入这场乱战。 然而我们都无法平息这场战争,因为我们已经是仇恨的靶子。 因为这场乱战,本就是天地容量不足导致的自我格式化。 与开始一样,战争的结束也没有一个明显的节点。 人口锐减一半后,仇恨的主体消失了,岌岌可危的天地容量也空出来了,人心中又不知不觉的灌满了爱。 我觉得可笑。 不是他们可笑,是我。 也就是在此时,我明白了我不是神。 我只是一个幸运的人,还是一个平庸的人。 站在最高处,我连人最基本需要的生存需求都无法看清,让旧人新灵都不得不暴露出兽性一面。 这本就是我的失责。 从那时起,我的确成了一个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