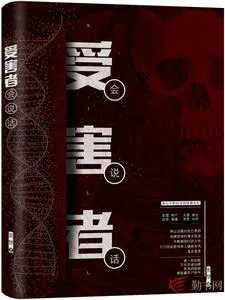在一条不太起眼的巷子里,发生了一宗谋杀案。 这边的房子大部分年久失修,市民的生活平平淡淡,周三周五会断绝供水,周四周一会停止供电,早上的八点钟开始,工地会准时施工,那震耳欲聋的机械噪音迫使沉浸在梦乡里的人们早早爬起来,工作也好,看书也罢,甚至跑步也行,总之就是不能睡觉,因为那声音实在是太嘈杂了。 在一排排的廉租房中间,有着月租形式的房子,装修程度比起政府免费入住的房子要好那么一丢丢,还能日租,但很少人会按一天天来算。无论怎么计算,都是月租房比较划算。 在街头街尾,无牌无证的小贩随处可见,如果你站在一条笔直的街道上,绝对看不到垃圾桶这样的物品,几乎所有的垃圾都被随意扔到地上,也不会有人介意这些现象。在拥拥挤挤,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人们只想争取多一点的时间,挣多一点钱,目的只是为改善生活的质量。你可以看到算命者、街头卖艺的武师、报纸商、收入极度不稳定的房产中介人员、落魄无比的文员,热心政治话题的老人家,啰哩啰嗦地凑在一起,说个不停。他们对于国际新闻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立场,习惯了美国的野心扩张、霸权主义,对美国佬的政治流氓也是不屑一顾,侃侃而谈。 这一片是属于比较偏远的郊区,相对外面的街道来说,是属于比较落后的一片地,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调侃说法。 里面就是地狱,跑到了外面就是天堂,可是你没有权利享受天堂给你带来的好处。 光鲜艳丽与落魄不堪的鲜明对比令他们对警察这个角色起了一定程度的防备,无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你的职业是警察,那么你进入这个范围,都不会受欢迎,还会处处受排斥。 于是,黄雁如带着莫求,两人都识相地将工作证件隐藏了起来,甘愿在普通市民面前扮演一个普通人。 属于月租房的右侧是凶杀案的发源地。 由于租金昂贵,很少人租得起这样的房子,以至于我们上楼梯时,都看不到几个住户。楼道里的灯光是那样的微弱,摇摇晃晃的吊灯有一种随时会倒塌的准备,在那样的昏暗环境里,我时不时会注意到黄雁如脸上那阴沉沉的神情,莫求倒是表现得很自在,她估计很喜欢这样的氛围,没有电梯的房子会增添许多好玩的东西。 我们的目的楼层就在五楼,由房东带着我们,在第三间房的不远处停了下来,只见他捂着鼻子,颇为难受地说:尸体就在里面了,你们自己进去看吧,今天早上已经有一批人进去过采集证据,里面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碰过。 我说了声谢谢,然后给了二十块她,她刚要离开,莫求拉着她的手说:你将死者的大致情况说出来听听。 “哦,是这样的,五楼一向又闷又热,蛇虫鼠蚁又多,垃圾的臭味时不时会飘到这边来,因此这里很难租出去。我记得在前几天,突然来了一个女人,她受了一点点伤,但包扎得有点夸张,又戴帽子又戴口罩的,鬼鬼祟祟地告诉我,她要租房子,我问她要租多久,她说租一个月,按照规矩呢,是要交一个月的按金一个月的上期,我本来还以为她会嫌贵,但没想到她眼都不眨一下就付了款。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她一点行李都没有,只拿了钥匙,连房间都没有进去过,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直到昨天晚上,她才突然赶回来,然后一直关着门,将自己关在里面,一句话也不说。结果到了第二天,我想找她谈谈关于这边间歇性停止供应水电的事,谁知道我一拉开窗帘,就发现她死在里面了。” 我的手触碰着所谓的窗帘,油腻腻的,灰尘又多,图案都差不多褪光了。 “你确定这是窗帘不是门帘?” “呃。门帘廉价嘛,最近物价上涨,只好用门帘来代替。” 我在门口来回地走了两次:一个租房子的地方,连个木门都没有,租客们都会放心? “哎,住在这一区的多半是生活有困难的,身无长物,他们不会介意的;问题是,那个女人还挺有钱的,身上涂了那种德国制造的香水,脖子上还戴了一条看似珍贵的项链,价值多少我没有估计,但一看就知道她肯定不是来租房子那么简单,可能是为了与某人在这里幽会,于是租了一个房间。” 我走了进去,顿时一阵浓浓的尸体腐烂的气味在空中的分子范围挥发出来,我的天呐,这所谓的房子还没有窗户,室内非常闷热,蚊子又特别多,喜爱在空中飞来飞去,直到尸体出现后,空中的蚊子也越来越多,无论怎么赶都赶不走。 黄雁如从进来开始,就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只好识相地戴上手套,开始工作。 在一盏小小的吊灯照耀下,我不难看出,死者的衣服已经被脱光,只留下一件内衣套在腰部稍微往上一点点。尸体的其他部位已经开始僵硬,但背部尤其是第三脊椎的位置附近还残留着余热,看来这里是死者生前最后被接触最多的地方。在她的脖子处,发现了一条又幼又细的钢丝,以极其复杂的形式缠绕着咽喉处,血液与钢丝的结合,导致整体上的触摸感润滑润滑的。她的头颅已经颈部被勒得很紧,自然而然地抬高了那么一点点,苍白的嘴唇吐出一个个代表着死亡的符号。 我将她的头慢慢地按了下去,深深地叹息着:哎,做了女一号也是劫数难逃。 黄雁如终于开口了:怎么样?尸体的情况如何? “死者躺在床上,没有穿衣服,只穿着内衣,所以不能算裸体;她以胸部压着床板的姿势被人从背后用钢丝缠绕着脖子,活生生地被勒死,不过不属于窒息死亡,而是失血过多,因为钢丝的锋利程度足以割破她颈部的任何一寸肌肤,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凶手足够狠毒,只要掌控着钢丝的主动权,往后稍微用一点点力扯过去,死者的头颅就会活生生地被割下来,不过他没有这样做,显然是不希望惊动其他人。” “怎么说?难道凶手在杀人的期间,就不怕被人发现?这里连最基本的一扇门都没有。” 我提醒她:你可别忘了,这里的环境是出了名的恶劣,难以忍受的。 “这么说,凶手是故意调了这边的位置进行作案。” “不,这可不成立,毕竟是死者自愿租了这里,理论上是死者租的房子位置给凶手带来了好处。床的位置恰巧是背对着门口,就算有人经过也不会发现不对劲,毕竟看不清楚她们究竟在做什么。” 黄雁如低着头观察了一小会,万分疑惑地说:凶手应该是一个女人,死者的身上只剩下内衣,而且以着这样的姿势趴在那里,一般来说,凶手是男人的概率比较高,可是死者还穿着内裤,而且我刚才检查过,没有发现湿润或者精斑,内裤是干净的,所以生前发生性行为的概率很低。假若不是性爱的缘故,那为什么死者会这样趴在那里呢? “看书?不对!” “睡觉?不对!” 黄雁如似乎很有经验地总结:是按摩,泰式按摩就是这样趴在那里的,只有按摩所产生的舒适感才能令人在短时间内麻痹了防备的意识,这时候要杀一个人就容易得多。 我很及时地补了一句:最大原因还是爱尔兰出车祸而死,张慧姗以为凶手已经死亡,自己不再存在人身安全隐患这一可能,于是她解除了所有的警惕性,包括让陌生人进来。 她被我的话击中了,心情一下子又再次沉重起来。 我不怕死地继续说下去:假设受害者名单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张慧姗由始至终都是最后一个受害者,那爱尔兰作为替罪羔羊就是为了掩饰凶手对最后一个目标进行猎杀,这一个就是替罪羔羊的好处,帮助了凶手完成整个杀人计划。 我刻意将这些事情全部说出来,借此来刺激她。 她倒是挺有觉悟的思维:换句话说就是,当你以为魔鬼离开了,其实它一直在你背后,充满着耐心,伺准机会蚕食你? 我迅速反应过来,无所谓地回答:没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呢,张慧姗的死更加令我相信,凶手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都坚持要完成自己的计划。现在倒好,她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计划,我们要抓她,只能从过去的案件中寻找线索了。 她自言自语道:张慧姗因为之前的袭击而导致受了伤,医生叮嘱了很多遍,她必须留在医院接受观察的,但她偏偏自己跑了出来,而且还跑到这里穷乡僻里的地方租了一个房间,显然是为了约见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查查她的通话记录没准会有意外收获呢。 莫求很遗憾地说:不用看了,我在进来之前已经查过,死者最后一次通话记录是用太空卡的,换言之就是一次性使用的电话卡,用完就丢,没有记录可寻。而且你会很奇怪地发现,这里一件行李都没有,这里肯定是她与神秘人见面的地方。 黄雁如心灰意冷地说:还以为救了张慧姗,牺牲了爱尔兰,但没想到,到头来,我两个都保不住。 我尝试着安慰她:别灰心,最起码我们现在百分百确定,凶手还躲藏在黑暗之中。这边厢,我已经在很仔细地研究着死者的伤口,横跨度极高,以斜边的角度一直往后延伸,钢丝的边沿已经溶进了劲动脉的地方。我摸索着血迹斑斑的钢丝,随口一说:凶手在拉扯钢丝时,用力过度,说不定她的手也被同样的钢丝的锋利度给割伤了,接着我绕到前面来,检查视察凶手当时所站的位置,果然让我发现了微量的血迹,暗黑色的,与死者的血液完全不吻合,看来这是凶手被割伤留下的血液,不过份量太少,无法采集到有效的dna分析。 突然在空气中响起一阵美妙的音乐,黄雁如接起了突如其来的来电。 一阵过后,她慢悠悠地说:很抱歉,我想,她应该来不了了。 哀伤过后,她抬起头,一脸阴沉地说:导演刚才打电话过来,让张慧姗回去拍电影,今天出了新的通告。 莫求无奈地说:可是她已经死了,而且尸体就在这里。 她随便地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捂着脸,异常疲倦地说:我跟他说了,张慧姗遇害,让他重新再找一个女一号。 莫求胆颤心惊地说:虽然所谓的诅咒并不存在,可是……所有女一号貌似真的死于非命…… 钟警官这几天一直躲在家里,半步不出门,电视机二十四小时一直在开着,她卧躺在沙发上,不知疲倦地一次又一次地跳着电视节目频道。国际新闻让她彻底了解到中东战争的局面;夜间新闻让她了解到,特案组目前正在处理的案件出了很大的问题,在大海的另一边经历着千变万化的趋势。也许她会暗中感到焦虑,但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本身也被一宗莫名其妙的案件给拖垮了。 她从来没有试过一个人独立调查一宗凶案,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很刺激很兴奋,但也很挫败。因为过去差不多一个月了,她仍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两名富翁,一个生前比较低调,但有着近乎变态的嗜好,属于色情方面的范畴;另一个则敛财无数,一身暴发户的形象。 两名受害者显然性格完全不一样,但均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属于社会的上流人士,出入高级场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发家致富的道路貌似是相同的,两人都曾经做过地产商开发,在包揽着不同项目的同时,发了一笔横财,这些就是他们的财富来源。 她躲在家里考虑了很久,正准备从多年前的地产开发商开始调查。 门铃响了,她突然觉得很诡异,刚刚搬了新的房子,怎么会有人知道她住的地方在哪呢? 作为一名警察应有的警惕性,她拿起了放在茶几上的手枪,躲在门的后面,瞥了一眼猫眼,看清楚了外面的情况。透过猫眼,她看到了一双很无助很哀伤的眼睛,她认得这双眼睛,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不会害她的。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门,她真的看到了苏樱,只见对方一句话都不说,直接扑到她的怀里,伤心欲绝地哭了起来,全身在颤抖着,这女人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的花香,似乎是满天星,但又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杂质。 她不知所措地说:苏女士……发生什么事了? “他死了……死在大海的另一边。” “谁?谁死了?” “爱尔兰医生,他出了车祸,死在了大海的另一边。” “哦,这个我知道,我一直有关注新闻。” 其实她关注的只是特案组的进展情况。 “电视上还说,他是杀害了三个女明星的凶手,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什么意思?” “小康说的话都应验了,他杀了人,可是我一直不相信。” “别这样,新闻宣布案件只是还在进一步调查,还没说清楚,他真的是凶手,案件还没终结的。” “真的吗?”苏樱慢慢地挪开了她的怀抱,爱尔兰医生早已经将小康的病历个案转交其他的医生,小康很抗拒那些医生,并且声称他们都是邪恶的本体,嚷着不肯去医院,这可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她好奇地问:爱尔兰医生怎么会无缘无故转交病历个案给其他医生呢!? 苏樱哀伤地说:我也不知道,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他早就有预感,自己会遭遇死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