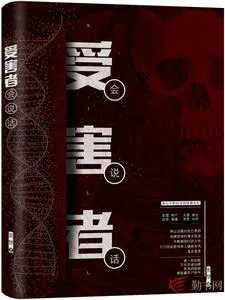昏昏沉沉的感觉,整个人好像失去了重量,我的脑袋漂浮在宇宙空间的范围里,空气灌入左脑,热量灌入右脑,我的脑袋开始发涨发热,疼得厉害,就像一个巨大的肿瘤压迫在我的脑神经里,而这个肿瘤是取不出来的,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翻天覆地的剧烈痛感,一下子使我从虚幻的梦中醒过来。 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试探性地按着自己的脑门,拼命地告诫自己,刚才的痛感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房间内的温度突然急剧地下降,寒气逼人,我不由自主地搂着自己的肩膀,瑟瑟发抖,我想,我的嘴唇一定很苍白,活像一名毫无生命的僵尸的那样。 天空中下起了一丝丝的雨点,室内顿时昏暗起来,伸手不见五指,软绵绵的床,淅淅沥沥的雨声,让我再一次确定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的确是自己的房间,但是我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沉睡了多久,这个得取决于手机上的时间。我艰难地爬到床头那边去,摸黑拿起手机,唤醒屏幕,一阵强烈的光线照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疼得厉害。我的手机没有接到新的信息,那是因为我在睡觉之前习惯了将手机进入飞行模式,这样就能确保我的优质睡眠不会被轻易地打扰,当然,如果在我不是很疲劳的情况下,倒不会设置飞行模式,因为凶案很有可能就在下一秒发生,只是偶尔太累,才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绝对与世隔绝的空间自我保护。 上帝原谅我。 我放下手机,下意识地爬到书桌的椅子上,坐在那里,打开笔记本电脑,还好我在临睡觉之前就已经将其充满了电量,这样我一打开电脑就显示我有新的邮件。 果然不出我所料,sarsh在手机上联系不到我,于是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 她的文字很简短:杜晓文的尸体已经送回实验室,请速回处理剩余的工作。她的态度很诚恳也很有礼貌,本来我还想着谁一个上午再回去完成剩余的工作,但我仔细一看邮件的日期与时间,才发现我已经睡了两天。 我换好衣服,走出客厅,crazy正在悠哉悠哉地吃着西式早餐,那鸡蛋都煎糊了,看起来虽然很好吃,可是她坐在餐桌前,那一副自信满满地样子让我心存戒备,我只好忍着不吃,匆匆忙忙地赶回实验室,完成剩余的工作。 在车子里浮浮沉沉,一阵惊涛骇浪,大起大落之下,我回到了警局。 沿着我熟悉的路线,穿过那延长的走廊,拐了好几个弯。 门被我推开,sarsh在对着铁架床上的尸体,实验室的冷气开到最低,寒风从制冷机的底下不断地冒出。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被黄主管给逼死。”听她说话的语气,像是在抱怨,但又不是抱怨,只是在责怪我而已。 “没有那么夸张,所有人都累了,不会有人催你工作的。”我走到后面的清洁室,给自己的双手洗干净,全身消毒,穿着那厚厚的塑料衣服,背着她,她给我在后面打了一个绳结。 “所有人都能休息,就我不行,私人助手还真不容易当。” “我们开始吧。”我望着冷如霜的尸体,冷冷地宣布着。 “死者部分牙齿发黄,这是牙烟,烟龄最起码有十年以上,同时他还喜欢吃槟郎。” 她不以为然地说:天哪,吸烟也算了,还喜欢吃槟郎,要知道两样都碰,会让人受不了的。 我拉起尸体的手臂,这边厢问她:怎么?你不喜欢别人吃槟郎? “何止是不喜欢,简直就是厌恶这种东西,真是够恶心的。” 我仔细地检查着手掌部位,坏坏地对她说:讨厌一样东西,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你经历了什么?拿一把尺子给我。 她从办公室拿过来,递给我说:我以前的男朋友特喜欢吃槟郎,超讨厌,平时吃也算了,那天我们亲热的时候,他嘴里还有槟郎的残余之物,妈的,全都嚼碎了,嘴巴耶! 我拿着尺子在度量手掌上被烫伤的伤痕,从外面量度,又从里面量度,心里在寻思着,不对啊,如果是自己烫伤的,伤口应该是从内到外,但这个恰恰相反,是从外到内的,难道他喜欢别人用烟头烫伤自己?他还有这种特殊的癖好?还是在重复犯罪现场时所留下的伤口?“那后面呢?你们怎么样了?他有没有进医院?”我放下尺子,摸索着左手的手骨。 她委屈地说:我看上去有那么粗暴、野蛮、有暴力倾向吗? “现在没有,我怎么知道以前有没有?”我拿着两块木板上下夹着左手的手臂,发现无法愈合。 “我们分手了,妈的,那混蛋还向我保证以后不吃槟郎,只要不分手。但是我没有答应他,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男人,他简直是视槟郎如自己的命根子那样,让他戒掉槟郎,那是不可能的。一个爱槟郎如命的男人,可想而知他的品味有多差,我果断将他打入冷宫。” 我及时补了一刀:对啊,他品味差,所以选了你。 她不太愿意但又迫不得已说出来:抱歉,是我主动追的他。没想到他相貌堂堂,竟然喜欢吃槟郎!真受不了! “呦,还真看不出来耶。”我故意调侃她,折好夹板,脸色开始凝重起来。 她很不甘心地说:这很奇怪吗?都二十一世纪了,女生追男生很正常的了。 “我没有说不正常,只不过你看起来不像主动的女生罢了。” 我重新蹲下去,检查着尸体的腿部。 死者的股骨(femu)、髌骨(patella)、腓骨(fibula)的部位有严重的受创迹象,血丝萌阴,我用刀将股骨部位的肉割了下来,仔细地观察着藏在深处的骨头,伤口未曾自动愈合,相信是近段时间摔伤所造成的,骨头往内折,很显然动力是由外至内所造成的,严重的震荡由外界所造成。腰椎也有同样的损伤,锥体(vertebralbody)但没有脚骨那么严重,折断的创口参差不齐,估计是由高处摔下所造成。 肩胛骨(scapual)有粉碎的迹象,其余的肱骨(humerus)、尺骨(ulna)、桡骨(radius)均有骨折的迹象,无法愈合,说明脱离骨质轨迹,没有及时治疗。 他生前摔得很严重,说不定内脏也摔破了,一片粉碎。 另外,subctaneousinfrapatellarbursa(髌下皮下囊)有感染的迹象,不排除有外界的刺激刺穿膝盖部位。 她看了看手机的短信,一言不发地跑了出去。 疑点重重,我决定解剖尸体,这样才能找到更深一层的线索。 我使用手术刀,刀子落在尸体的肚皮上,金属与肚皮的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 裂缝从胸口的部位一直被剖开,延伸至肚皮的位置,苍白色的肚皮被翻到铁架床上,那完好无缺的内脏器官在我眼前暴露得一览无余。肺部已经液体化,血淋淋的液体渗透在其他的肾脏器官里,像玉米粥那样。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个勺子,将那些血液盛了出来,血红色的粥,确实闻所未闻。 她从外面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我看着问:那是什么? “杜晓文生前的医疗报告,刚刚送到的。” “原来他在两个月之前,因为爬山,不小心摔了下来,摔得很伤,多处骨折的现象,就算打了石膏,他的行动仍然不方便,偶尔还要吸食止痛药进行痛楚麻醉,他摔伤的地方,与你刚刚所说的完全吻合,他肯定是作案之前就已经受了严重的伤。” “嗯……他的肺部液体化,就像玉米粥那样,他肯定不止服食了老鼠药。” “可是他摔伤了,就不可能在女子监狱的女厕所内杀害银苏苏。” 我点了点头:的确是这样,他不足以杀害那么多人,看来他这回是做了替罪羔羊。 他真的是自杀吗?她问我。 我勉强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胸有成竹地摘下手套,走出实验室,她从后面追了上来,替我解开塑料衣服,我正在清洁着我的双手,再次消毒着,在那哗啦啦的流水声里,她对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专心致志地洗着手,从容地说:我们的工作只是检验尸体,你只需要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份验尸报告即可,其余的用不着你担心,其他人自然会接手调查工作,这可不是我们的工作职责范围所在。 “但他们有知情权,我们必须要分享这些信息。”她不屈不饶地说着。 我用抹布擦干净自己的手,晦气地说:所以你要扮演正义的化身? 她斜靠在门上,叉着腰,几番思索地说:这与正义无关,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我无可奈何地说:好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你全部记录下来没有? “已经好了,可是……” 我翻着白眼说:现在要电子版的,纸质版已经不吃香。 她兴高采烈地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隔了一天,验尸报告的电子版才完成,我以工作的名义将报告发送给她的私人邮箱里,紧接着,我突然造访,亲临她的办公室,她的门没有关上,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踮着脚尖,屏着呼吸,慢慢地将门合上。 她正趴在办公桌上,昏昏欲睡,不知为何,她竟然发现了我的踪迹,头也不抬地说:鬼鬼祟祟干嘛? 我勉强地保持微笑:送验尸报告的。 她慢慢地抬起头,敲着眼前的一大块电脑屏幕说:你的电子邮件我已经收到,但我要听的,是你本人的陈述。 “我要说的,验尸报告早已写得一清二楚。” “你懂的吧?”她似乎很不耐烦。 “好吧,杜晓文的确不太可能是凶手,因为他在命案发生之前已经摔伤了,身上有多处骨折,内出血特别严重,他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连续杀害三个人,况且他服用的可不仅仅是老鼠药那么简单,老鼠药是一种慢性中毒的毒药,服用之后是不会立刻死亡的,如果发现得早,及时送院治疗或许还有得救,但我检查过他的尸体,发现他的死亡是一瞬间的,而且他的肺部化成一滩血水,一粒一粒的,像玉米那样的形状,老鼠药里还夹带了其他的病毒源,但是这种源的毒害性是极其神秘的,破坏性极强,不排除是一种新型的病毒。” “利用病毒杀人?”她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嗯,有这种可能,但问题是,我们对这种病毒的传染性以及危害性一无所知,带菌者是如何传染的,这种病毒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都是未知之数,最大的危害已经不仅仅是限制于一宗谋杀案了,更多的危害隐患就躲藏在角落里。” 她将自己的身子轻轻地往后挪,一筹莫展地望向天花板说:那就是说,我们要尽快破案,一旦凶手将手里的病毒扩散开来,那就危险重重了。 可以这样说。我简单地回应着。 她的手放在桌子上,慢慢地拍着、拿开。不断地重复着这看似简单,实质复杂的动作。 她的背部是那样的昏暗,时间在此静止,随着电梯的一声响,时间又在流动着,电梯大门缓缓打开了,裂开一条广阔的空间,她踏进了电梯的狭窄空间里,高跟鞋踏在地上发出了沉重的声音,电梯门缓缓合上。 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她的头是全程一直低着的,发光的数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跳动着,她这次慢慢地抬起头来,望着左上角的方向,眼神里流露着中分的抑郁,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奶白色的公文袋,被一条看得见摸不着的细线紧紧地缠绕着,处于密封的状态。 画面开始出现模糊的迹象。 电梯门被打开了。 她踏着沉稳的脚步,在转角处拐弯,停在一扇门的前面,她轻声地咳嗽着。 门被敲响,里面传来一声ein!她推门而进。 鉴证科的主管正低着头在研究着被透明的塑料袋装着的材料,显然是两份笔迹极度相似的信件,唯一的区别是,左手那一封是用蓝色的墨水写的,而右手那一封是用黑色的墨水写的,工整度一样,但这对她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因为答案仍然没有呼之欲出。 “听说你找笔迹专家鉴定过两份信件。”这是陈述句,并非疑问句。 他仍然低着头,戴着眼镜,似乎在研究一些重要的细节。 “阁下的消息真是灵通,结果刚刚出来,你就收到消息了。” “我凑巧经过而已,顺便问问。”她摊开双手,无所谓地说着。 “你真是死要面子!” “请问可以开始了吗?” “当然,不过我得酝酿一些恰当的情绪。” “就两份信件的字迹来看,的确是一模一样的,无论是笔画、结构、力度、字型都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的确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她失望地说:那就是没有发现了。 “那倒没有,笔迹专家的工作只是肯定地告诉我,两份文件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这样他的工作任务已经完结。相反的是,我恰巧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们看这里,右手边的这一信件是在凶案现场发现的,在开头的地方,这里写着,我杜晓文因为一时的执着而产生了思想上的偏激。你有没有发现杜晓文这个名字的写法有点奇怪。” 她指着信件的位置上:好像是有点奇怪,字迹与其他的字体好像有点不一样。名字的写法是从左至右,而其他的字体是从右至左;还有,两者的落笔力度显然是有区别的。 他拿出其他的材料说:这些是我从杜晓文的遗物里找到的信件,这是他以往写过的文章、信件,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他一直用右手写字,从来都是,而且落笔的力度比较重。 她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不是用右手写字。 他胸有成竹地说:恰恰相反,写这个名字的人,显然是一个左撇子,他落笔的力度很轻,手是压不到纸页的。这封信出现了两个人的笔迹,这个就是最大的疑点。 她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若有所思地说:你的意思是,凶手故意哄死者写这样的一封遗书,然后再用毒药毒死他,然后在信的内容里增加死者的名字,伪造信件,让全世界都以为死者是畏罪自尽,实际上是做了凶手的替死鬼。 他点了点头说:有能力哄死者亲自写这一份昭认书,凶手与死者之间的关系一定非常的密切,至少说信任度极高。 她恨得咬牙切齿地说:凶手极度精明,想不到我们苦苦追查,最后仍然被他牵着鼻子走,或许有一部分的线索从一开始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