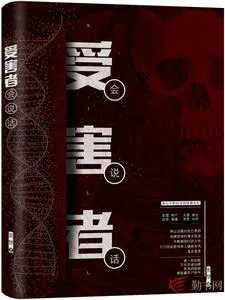李局长尚没有脱离危险期,他仍然躺在深切治疗部,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主诊医生都说,他能不能醒过来都是一个问题。 我坐在他旁边,望着他安然睡着的神情。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行凶者是谁?”我心里在默默地问着他。但他毫无反应,我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就算我没有回头,我也感觉到,外面蹲守着、不离不弃的几乎全是李局长的旧下属,尤其是刑警队,他们在窗外忧心忡忡的地凝望着。 钟警官也走了进来,两眼无光地望着陷入昏睡的李局长,不禁叹息着。 我问她:“找到那个疯子没有?” 她摇摇头说:“没有,一点线索都没有,他就像销声匿迹似的,完全找不到踪影。” “人口调查那边呢?”我捂着鼻子。 “很奇怪,他们拿着证件上的照片输入系统,但是一点记录都没有,似乎是遭遇恶意删除记录的感觉。” 我自言自语地说:“那个疯子是什么来头?竟然查不到他的过去,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钟警官无奈地摇摇头,她也是一脸茫然。 我拉开门走出去,李局长的一群旧下属纷纷以困惑的眼神望着我,我深呼吸着,说:“你们之中,有谁认识李局长最久的?” 他们纷纷摇摇头,这倒是,他们还那么年轻,不可能知道那么多详细的过去。 钟警官也走了出来,在我耳边说:“不如我们翻查李局长过往的办案记录吧,或许会有发现。” 于是,我们便双双前往档案室,翻查李局长在升职之前所处理过的每一宗案件,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破案率是最高的,只要是经过他手里的案子,都能得到全面的侦破,最关键的是,李局长似乎从来没有受过警队的纪律处分。 钟警官在抱怨着:“那么多档案,我们要找到什么时候呢?” 我突然一阵激灵,脱口而出:“枪击案件类型的记录全部找出来。” 每一沓档案都用单独的标签隔开的,她很快就找到枪击案的类型。其实也没有很多宗,到现在为止,一共也才十八宗。 她漫不经心地分析着:“有银行劫杀的、有反社会分子的刻意破坏、还有通缉犯的追捕记录……” 我嚷着:“没有特别的地方对吗?” “不对,这里还有一份,但报告上的描述不是很仔细。” “念来听听。”我的眼睛还在留意着其他的档案。 “1993年,7月15号;有警务人员因为情绪失控当街开枪袭击路人,李警官与其他警员对其凶徒进行追捕,最后凶徒挟持人质,当时凶徒的情绪极度不稳定,况且他手里还有枪械,在千钧一发之际,其中一名警员开枪制服了凶徒。”她停止了朗读。 “没有了?就这样?”我好奇地问着。 “嗯……这一宗案件很粗略地报告着,细节上的情况没有具体化,凶徒最后的下场怎么样都没有提及;是谁开枪制服凶徒的也没有明说;后来那个人质的安全程度也没有交待,整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是破案的功劳就落在李局长的身上。”我简单地说着。 她点了点头说:“没错,因为这宗案件是表彰李局长的英勇无畏,是植入他的警员生涯记录。” 我问着:“当时有份参与现场的警员是谁?” “卧底探员,还有……第五名受害者。”她不敢相信地说着,因为照片上的他们,当时是很年轻的,如果不认识他们,一定认不出来。 “难道行凶者的杀人动机与这宗枪击案有关?” 钟警官提醒我:“但是你不觉得,李局长有一种抢了别人的功劳的感觉吗?档案记录上没有写明,开枪制服歹徒的人是他,但他偏偏领了功劳,还因为拿了勋章。” 我打开蓝色的皮夹,说:“描述文件的下半截被撕烂了,我们看不到后面的结案报告。” “看来是有人刻意这样做,企图毁灭一些不希望被我们看到的记录。” 在档案室,我们一无所获。 再次回到医院的走廊时,发现在深切治疗部外面多了一个年纪老迈的男人,他个子不高,腰部有点弯弯的感觉,头发蓬松,油头油面的,看上去就像是几天没有洗过澡似的,更重要的是,他穿的衣服非常老款,而且很破烂不堪,他看上去不像李局长的朋友。 钟警官往前走一步问他:“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 他微微地转过身,邋邋遢遢地望过来,嘴里喃喃地嚷着:“我来看……李警官的。” 他肯定很久没有见过李警官,人家都升局长级别了。 我问他:“你很久没有见过他了吧?” “是的,其实我刚刚从牢狱里出来。”他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眼神是那样的失落。 我不得不告诉他一个事实:“李警官现在已经是局长了,不过目前被撤职,还在休假期间。” 他除了惊讶不已之余,脸上还浮现着敬佩的目光:“我就知道,他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也是警察吗?”我留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禁问着。 “以前是,不过现在不是了。” 钟警官咬牙切齿地说:“慢着……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李局长的家中有一幅照片,是四个人合照的,你就是其中一个……照片的背后还附带着名字……你叫陈勇,对吗?” 他苦笑着:“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记得我,那幅照片他一直还保留着。” “你们四个可是好朋友。”她轻描淡写地说着。 “很遗憾的是,死了两个,还有一个躺在里面重度昏迷,尚未脱离危险期。”我无情地说着。 他大惊失色:“你说什么?另外两个已经……?!” 钟警官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那样,低着头说:“很抱歉,他们死于一宗枪击案件中,行凶者至今没有查到。” 他很疲倦,喃喃地嚷着:“又是枪击案……我这是见鬼了吗?” 我故意地说:“看来你深有同感。”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礼貌上笑一笑,看上去笑得很勉强。 “对了,你犯了什么事,要搞到坐牢那么严重?”我凝望着他的眼睛,他躲开了:“也没有很特别。” 他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地逃离我们的视线范围。 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说着:他好像有古怪。 钟警官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躲起来接听,看来是私人电话;我还在寻思着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进行调查,她跑回来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和叔邀请我去他家吃饭,你陪我一起去吧。” “不要,最忌讳去别人家吃饭。”我随口地说着。 她竟然对着我撒娇:“去嘛……我一个人去会很尴尬的。” 好吧,我又妥协了。 在开车的路上,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她:“如果与别人不是很熟,就不要随随便便到人家那里去吃饭。” 她坐在副驾驶那里,望着窗外的不断变换的景色,无所谓地说:“上一次他儿子表现得不是很好,他想向我道歉。” “是吗?”我左右摇摆着方向盘,隔壁那家伙以为自己是车神啊,胡乱地开车。我非常不满地咒骂着。 “不过我觉得他儿子对陌生人……哦,不对,应该是对警察特别抗拒与厌恶。” “小孩子嘛,大概就是这样反叛的。”我心不在焉地说着,内心还在回想起那个叫陈勇的男子。 很快,我们就到了。 和叔一如既往的热情好客,请我们入坐,我留意到左侧房间的门是没有关的,而且门上面的锁是经过改装,似乎是调换了位置。 他很客气地给钟警官倒酒说:“抱歉啊,警官,上一次的事,是我儿子不懂礼貌,我替他喝了这一杯赔罪。” 她连忙说:“别啊,你太客气了。” “是我不好,不懂得教他,他妈妈又死得早。” 我动起身,走到一个灵牌的前面,那块暗红色的木板上放着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我摸着满满的香烛,明知故问地说:“你太太的死会不会让你很伤心,或者很难过?” “许医生!”她呵斥我。 和叔倒是很放得开,强忍着痛苦说:“生死有命,我早就已经放下了。” 我面带微笑地说:“放得下就好。”转眼之间,我又拐进了他儿子的房间,望着房间内的布局,内心深处起了一丝丝的困惑,她连忙跑进来拉着我的手说:“先吃饭吧,别捣乱了好吗?” “你不觉得这房间的布局很奇怪吗?”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说:“上一次我进来过,的确有着和你一样的感觉,可是就是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劲。” “房间的摆设、家俬的摆放位置,以及所有书籍、模型之类的物品的位置全部偏向左手边,这就说明他擅长用左手、或者习惯用左手、又或者只能用左手。“ ”这说明什么?“她好奇地问着,其实她心里估计也有结论,但就是没有大胆地说出来。 ”在心理剖析报告中,我们分析行凶者有两人,一人是担任统治者的角色;另外一人则是担任言听计从、毫无主见的角色。“ ”是的。“她默默地承认这一点。 “其中一个行凶者是使用左手开枪的,但他又不是左撇子,因为他的右手是残废的,他是不得不使用左手。” “是的。” “对于左撇子的行凶者,他对受害者产生了内疚的情感,除了是他身不由己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小,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容易受人梭摆,很有可能还在求学阶段。” “没想到,其中一个服从者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她皱着眉头说:“不可能的,这些只是推测,他还只是一个孩子,绝对不可能的!” “你们在我房间干什么?”一名青少年出现在我们的身后。 她在我耳边说:“他就是和叔的孩子。” 我胸有成竹地说:“想知道我的推测没有错,我做个实验给你看。” “你们最好赶紧离开,否则我就……”他还在孜孜不倦地嚷着,我走过去,拿起他的右手,软而无力,他很敏感地甩开我的手,情绪几乎一度失控:“你干什么!” 和叔跑了进来,忧心忡忡地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问他:“你儿子的右手是不是与其他人不一样?” 和叔很哀伤地说:“是的,他右手是残废的,但他自尊心很强烈,一直在其他人面前隐藏自己右手的残缺!” “爸爸!你别说了!”他竭斯底里地喊着。 我揪着他的衣领问:“你的同伙在哪里?究竟有多少人?!” 他用左手推开我:“我不会告诉你的!” “什么同伙?警官你们在说什么?”和叔显然是不知情的。 他挣脱我们,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我想追,但钟警官拉着我,不让我追出去。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他痛心疾首地喊着。 我面无表情地告诉他:很抱歉,我想……你儿子闯祸了。 晚上,我带着疲倦不堪的身躯回到家里,crazy一如既往地不在家,正好,她在家里,我反而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打开手提电脑,在那屏幕上,显示着新邮件的接收。 我再次踏入他的领域世界。 to:许医生 对于我来说,坐在我对面的女人,估计早就已经精神奔溃。丈夫遇害,继而轮到两个女儿,但唯一比较令我出乎意料的是,对于大女儿的遇害她倒是没有显得多在乎,她全程都盯着小女儿的照片看,大女儿的看都不看一眼。 我指着大女儿的照片说:“你女儿有没有男朋友的?” 她表现得很冷酷:“我不清楚。” 我皱着眉头说:“我在你女儿的公寓里,找到很多的安眠药,除此之外,医院的官方记录也显示,她曾经有过多次自杀的记录。” “是吗?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视线仍然停留在小女儿的照片上,眼神里尽是惋惜的情感。 “你似乎不太在乎大女儿的事情。” “谁说的,我不知道有多难过。” “从进来这里到现在,你都没有问过大女儿的事情,却由始至终都盯着小女儿的照片,很显然,你一点都不关心她。“ 她沉默了,我穷追不舍地说:“麻烦你合作一点。” “她……的私人圈子比较混乱,差不多一个星期换一次男朋友,每次失恋都极度哀伤,伤心过后就会厌世,产生吃安眠药、自杀的念头。” 我顿了顿:“为什么你没有劝她?” “两个女儿里面,其实我最看好的就是大女儿,可是她又不肯用心读书,整天就喜欢做梦,老是沉浸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那些男人接近她多半是为了拿便宜,我说过她很多次,她都不听……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引导她。” “她那些男朋友,你都有见过吗?” “没有……她换伴侣就像换衣服那样,我对她已经没有期望。” 我叹息着:“哪怕她现在遇害了,你都没有感觉?” “没有!当日我苦口婆心地劝她,乖乖读书,好好进修自己,她非是不听,乱搞男女关系,她搞到这种程度,我只能说她活该!” “是活该……!” “是活……”她的声音在颤抖着,手脚不知该往哪里放,低着头望着破旧的桌子,胸口在尝试着平伏,她还想继续说,但已经发现自己根本说不下去,眼神里很快流露出一种颓败的感觉。 唉!始终是口硬心软。我默默地递了一张纸巾给她,一开始她是拒绝的,但慢慢的,她妥协地接了过去。 我把档案往前一推,心灰意冷地说:“本来呢,想请你回来问有关于你女儿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觉得……你根本不了解她。” 她猛地抬起头望着我,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谢谢你的合作。” 我在她一片困惑的眼神中,离开审讯室。 阿娇递来一份调查报告,上面很明显地列举了死者所结交的男性朋友。 保守来计算,绝对超过一百五十个,这只是今年的前半年记录,区区前半年就已经打破了去年的记录。这一份调查报告的资料是死者的大学同学提供的,她们很要好,读书时还一起在图书馆写毕业研究论文,她对她的过往,是最清楚不过的。 我看着眼前的这一份调查报告,困惑不已,难道情杀案是针对她们两姐妹的?不对不对……受创伤最严重的是男死者,他才是行凶者的最终目标,可是又如何解释姐姐的死呢? 我一个人在走廊逛着逛着,突然留意到子虚双手抱着头,缩在椅子上,脚踩了上去,毫无仪态。不过我可以原谅他,毕竟他现在肯定以为自己鬼上身或者有严重的精神病了—可事实却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故意走到他面前,念念有词地嚷着:“陈慧慧太花心了,一年换那么多个男朋友。”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依然是牢牢地抱着自己的头,一言不发。 “陈慧慧的妈妈一点都不关心她。”我故意凑在他耳边,喊给他听。 他终于勉强地说了一句:“陈慧慧是你女朋友啊?那么激动干嘛。” 我拉着他的肩膀,不敢相信地说:“你没事吧?陈慧慧就是陈姗姗的姐姐,你前女友的姐姐!” 他甩开我的手,转移着视线说:“我说过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姐姐!” 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心灰意冷地说:“这个我相信,你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抱歉,给你添麻烦了!”他丢下我,一个人扬长而去。 我望着他远远离去的背影,不禁起了一丝丝的哀愁。 这宗案件越来越离奇,很多细节上的,我都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不过……我相信总有破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