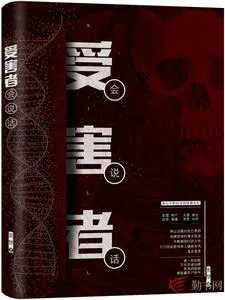我抬起手腕,发现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十一点多,全部人全部坐在大厅的位置,被点燃的烛光照亮着大厅的环境,他们不约而同地坐在吃饭的椅子上,阿群、院长、阿敏、他们全部都在等待着我的发言,还有门外的一群小孩,其实是我故意把他们留在外面的,因为接下来我要陈述的细节,简直是儿童不宜,绝对不能让他们听到如此丧心病狂的事实,否则他们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绝望的。被抓住的女人,我们没有对她使用暴力,她也没有打算反抗我们,只是乖乖地安静坐在那里,但是与所有人都隔开来,方便我对她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一个客观上的描述。 “各位,本来我是一名法医,我的同事秋雨女士是情报科的,她突然有一天向我发出邀请,来孤儿院玩一会,没想到她软硬兼施使我留在孤儿院做一个月的义工,最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邀请,但我很快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在我住进来的第二天便发生了一宗离奇的命案。死者是一名男性,偏向年轻的人生阶段,他的死亡方式很奇怪,首先他死在几乎没有人靠近的钟楼里面,他死亡的时候是穿着睡衣的,而更为奇怪的是。死者的舌头被活生生地割了下来,这种奇特的死亡方式令我深信,这一宗谋杀案绝非普通的类型,根据我以往处理过的案件里,很少受害者的舌头会被活生生地割下来,这是一种报复性的刑罚,我知道这宗案件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我有向秋雨建议过,立刻报警,让警方处理这一宗看起来很残忍的谋杀案,但是秋雨女士坚决反对报警,甚至很反感第三方介入调查,她太过于自大,以为封闭性的调查也能找出凶手,查出真相。这种自大的最终导致的后果是,引发了第二宗谋杀案的序幕。” 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会,看着被抓住的女人,双手抱在胸前,笑了一会,然后接着说下去:“第二名死者乔安纳是第一名死者的妻子,他们两夫妻一前一后地遇害,夫妻组合的谋杀案在以往的案例中也不罕见,但问题就在于,乔安纳对于丈夫的死是毫无感觉,甚至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她的反应令我很困惑,这不是一名妻子对丈夫遇害的正常反应和态度,于是我开始怀疑乔安纳。但是自然规律就是这样,当你开始怀疑一个人是凶手的时候,那个人就会离奇遇害,这不是侦探故事的情节,而是那个人可能知道某些内情而遭致杀身之祸,果然,她也死在钟楼内,而且与其丈夫一样,同样是身穿睡衣,唯一的区别在于,她的耳朵被活生生地割下来,手臂上有很多被烫伤的新伤加旧患……啊,对了,说到这个新伤和旧患,我不得不提一个小小的细节,两名死者还有一个共通点,他们身上同样残留着一些旧的、被虐打的伤痕,我相信他们是小时候曾经遭受过非人的虐待,还有一个现象,乔安纳遇害的时候,她是赤裸裸呈现在我视线范围内的,很显然,她的衣服在生前已经被活生生地扯烂,究竟凶手为什么要扯烂她的衣服呢?想到这里,我开始有一个模模糊糊预设的立场,凶手可能是男性,他扯烂乔安纳的衣服是出于压抑已久的性需求……一切皆有可能,当然,我很快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他们两个的身上同样有一个相同的印记,一个这样的印记!” 我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这样的符号“卍”,呈现给在场的所有人看,后来根据院长的说法,我才明白,这个印记是曾经在孤儿院待过的小孩都会有的,那么所有的事情就能解释清楚了,原来凶手要扯烂乔安纳的衣服并不是出于性需求,他只是想看清楚乔安纳身上的印记,他们两夫妻在同一间孤儿院长大的,长大以后回到这个曾经成长的地方,那么他们回来这里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从一开始他们都没有很刻意提起过,自己以前也是在这里长大的,他们既然要隐瞒,就一定有他们自身的原因。究竟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这个时候,我从院长的口中得知,钟楼传闻是曾经闹鬼的地方,而且在楼道内藏有宝藏,这就等于是,越是繁荣越是罪恶的表面现象,但我不相信楼道内有宝藏,如果真的有,这家孤儿院的规模不可能那么小的,你看着这范围那么小,连现代化的灯光都没有,走夜路很容易摔倒的,这样对小朋友很不好的,摔倒会很痛的,对不对?所以有宝藏的说法一早在我心里被消除了。但是秋雨女士的做法,令故事的发展推进了一步。那天晚上我发现她在楼道内挖东西,当然她只是挖了一半就被我给中断了。事后我不断地问她,在那里挖什么东西,她死活不肯告诉我,我当时还以为她真的在挖宝藏,但院长又告诉我一件非常久远又惊心动魄的过去事情,原来在很多年前,这所孤儿院有几百名小孩离奇失踪,至今没有踪影,那些小孩去了哪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找到之前,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原来秋雨女士也是这所孤儿院的小孩,她身上有着相同的印记,她挂念的是那些失踪的小孩,所以她千方百计引导我过来这边,目的就是为了调查案件的真相,但很不幸的是,在谋杀案的案例中,一个小孩失踪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现象,至少生命一定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威胁,更何况是几十年的时间,结果一定不会太乐观。这个时候,秋雨女士却遭遇神秘袭击,昏迷不醒。两件事情令我做了一个直观性的联想,于是我邀请了本案的受害者阿石,一起去钟楼继续挖掘上次未完成的工程,不挖还好,一挖……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各位,钟楼的底下一直埋藏着几百名骸骨,而且全是参差不齐的,经过我的检验,发现那些骸骨全是小孩子的,换言之就是那一批离奇失踪的小孩的骸骨,失踪的真相呼之欲出了,他们不是失踪,而是死在钟楼底下很多年,被埋葬在地下,一直无人问津。其实……他们也挺可怜的,本该好好成长的年龄,偏偏中途夭折!我身为法医,见证了无数的死亡,但这次面对着不计其数的骸骨,我自己都无法承受这种沉重的悲伤。究竟是谁杀害了这些小孩呢?会不会与乔安纳夫妻的遇害有所关联呢?我当时已经很困惑,案件一下子陷入困境,我不仅不知道谁是凶手,我甚至连谁是真正的受害者是谁都不知道。噢,对了,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她就是养殖蜜蜂的黑巫婆。从表面看起来,她具有非常可疑的作案动机,首先,她当时出现在乔安纳遇害的现场,双手沾满了她的鲜血,慌慌张张地逃离现场,然后她在外面的树林将我击昏,同时也是她提示我,那些小孩的骸骨在钟楼底下,显而易见,她是知道内情最多的一个人,那究竟她是不是凶手呢?这个我暂时不做客观上的描述,我们先跳过这个阶段ok?” “原本我以为黑巫婆如果是凶手,那么谋杀案在这个时候应该落幕甚至停止才对,但阿石的离奇死亡令我深信,案件远远没有去到结束的程度,黑巫婆虽然是疑凶,但显然只是疑凶而已,但是阿石的死亡方式实在令我过于伤脑筋。例如你玩一个游戏,它会有一个固定的通关模式,你一定要打完所有的小兵才能打boss,但是突然一声不响,到了下一关,没有小兵打,直接打boss,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无法适应,我也是这样。阿石的死亡方式同样是很怪异,他身上的刀伤一共有五处,每一处又有五个伤口,杀人的手法与之前的受害者有着天壤之别,作案模式改变,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发生了某些事情;在我还没想明白是哪些事情的时候,阿丽也接着遇害,她的情况与阿石一样,身上有五处伤口,通常是致命伤,怎么回事呢?杀人为何一定要在其身上割五处伤口呢?这样会很累的喔,每次都割五次,那么这个五的次数会不会与凶手的强迫症习惯有所关联呢?” 说到这里,我紧紧地盯着被抓住的女人,问道:是不是啊,柯斯斯女士。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怀疑到我头上来?” 我回答她:“本来我也没有怀疑你,因为死者是你男朋友,你不可能狠毒到杀害他,但是你说话的方式很奇怪,每次说一段话都不会一次性说完,而是分为五小段作为陈述,最初我还没有发现,但是随着你这个致命的习惯不断地重演,才令我开始注意你。我假设你是凶手,那么你的杀人动机在哪里呢?噢!这很简单!小丽与阿石有不寻常的关系,他们在孤儿院内偷情,阿石虽然与你谈恋爱多时,但是他从来没有碰过你,你觉得他不爱你,甚至在玩弄你的感情,于是你由爱生恨,将他们统统都杀了。你还很聪明,懂得利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替他们换上睡衣,令我产生错觉,以为所有的谋杀案是由一个凶手所策划的,杀害小孩的凶手,他的年龄不多不少都应该踏入年老的阶段,不会有人怀疑到一个年轻人的身上,但是我很容易找到了破绽。阿石在遇害的那天,外面明明下过雨,你还对我说过,他曾经出去过,那么他当时如果是穿着睡衣,那他的睡衣应该会有污渍和水渍才对,但我发现他的睡衣是很干净的,一点肮脏的地方都没有,于是我相信是凶手刻意在他死后为其换上睡衣,以此来混肴视线,扰乱我的调查方向,令我对凶手的预设产生误区。” 院长忍不住打断我的陈述:“你这是什么意思,凶手不止一个人?” 我在原地转一圈,接着说:“是的,两种作案模式,当然是有两个凶手,当然一个人有两种作案模式也不是没有可能,除非他有非常严重的人格分裂,但这种案例外国也很少,更别说这边。接下来,我就要揭开第二个凶手的真正面目,不过在此之前,这个阶段要暂时停一会。虽然我已经知道柯斯斯女士是凶手,但我又没有证据,我又能怎么办呢?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学外国电影那样,设计一个骗局引你出现!但是你是感情上动的杀机,不可能无缘无故杀人的,于是我只好来一个顺水推舟,骗你说,还在昏迷阶段的秋雨怀了阿石的孩子,一般因爱成恨,被爱意冲昏了头脑的女人都很多疑,我这样说了,你当然会心生怨恨,甚至会动杀机;为了顺利哄你中计,我更是加大赌注,把所有人引开,让我单独一人保护秋雨女士,原本我很希望你不会出现,但是没想到,你令我太失望了!你果然是杀害阿石与小丽的凶手!是你自己露出原型的!” 院长又忍不住打岔了:“那么另外一个凶手是谁,你赶紧接着说啊。” 中央火车站上,一下子站满了狙击手,全城戒备,火车站的所有平民百姓已经全部疏离现场,没有人知道尔破仑这一回会以什么作为赌注,上一次是炸弹,这一次或许会更为恐怖。黄雁如穿上防弹衣,直觉告诉她,一场战争是在所难免的,她知道吉尔探员已经在赶来火车站的路上,但她并不知道吉尔探员这次出现是以退休警察的身份还是复仇者的身份。 尔破仑很安静地坐在长椅上,享受着寂静的氛围,半点阳光偶尔会照耀在他脸上,黄雁如慢慢地走过去,问他:“尔破仑!崔西贝呢!你把她藏在哪里了?” “除非我得到想要的东西,否则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这不可能!我们警方是永远不会与恐怖分子妥协!” “那你就一辈子都别想看到她了!噢!可怜的小孩!” 她知道无法再拖延时间,只好对着传呼机说:“把她带过来吧。” 珍妮被押上来,尔破仑看到她,脸上淡定自如的表现瞬间消失,迷离的眼神里充斥着如饥似渴的欲望。 “你真的杀了那么多人?” “珍妮!没有你!我迷失了自己,回到我身边吧。” 吉尔探员从侧边出现了,他用枪指着尔破仑:她是一名好医生,她有三个孩子,可是你偏偏杀了她! 尔破仑对珍妮说:“跟我走吧,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吉尔探员说:“你杀了好几百人,就因为你母亲是一名妓女?” 尔破仑一如既往的得意笑容突然消失了,他脸上一瞬间僵硬起来。 “尔科普夫,七十年代末移民过来,她有一个非常聪明但性情很古怪的男孩,她竭尽全力都无法满足这个奇怪男孩的要求,她只有从事最古老的职业才能勉强维持生活,照顾这个男孩,她甚至很担心这个男孩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深重的危害,所以她不能让他到达外面的世界,她只想用最仁慈的母爱包容他,希望可以改变他那奇奇怪怪的性格。” 吉尔探员依然用枪指着尔破仑说:“珍妮!他只是当你是他母亲而已,尔破仑!你一点都不稀奇,冷血无情,乏味,无聊,并且充满暴力倾向,你只是一个极端平庸的家伙罢了。” 尔破仑朝珍妮伸出邀请的左手:“珍妮,跟我走吧,这个世界不值得我们留恋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珍妮像被催眠了一样,傻傻地说:是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他拉着她的手,跳下火车轨道,火车迅速驶过,将他们辗成粉碎……吉尔探员大声呼喊着珍妮的名字,可是已经无补于事。 阿丹带领着其他民警,一起闯进尔科普夫的家中,里面布满了灰尘,空气并不流通,他们在床上发现了一副已经风干的尸体,尸体上铺满了红玫瑰,红色的花瓣已经风干,但花的数量出奇的多。在狭小的衣柜里,阿丹找到了崔西贝,谢天谢地,这孩子安然无恙。 吉尔探员坐在长椅上发呆,黄雁如把手机递给他,他接听起来。 “吉尔探员,我是崔西贝,谢谢你救了我。” 他柔情似水地说:亲爱的,你以后都会没事的,好好成长起来。 所有人逐渐地离开房间,只有阿丹还在凝视着床上已经风干的尸体。 他们再次打败了可怕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