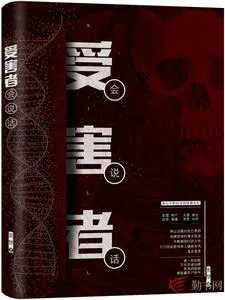审讯室的大门破天荒被合上,我被挡在门外,身上仍然穿着那天离开医院时所穿的那件病人衣服,拖着滑稽的拖鞋,焦虑不安地来来回回地走动着,黄雁如双手合十,头微微地转动着,颇不顺眼地看着我说:“不要在这里走来走去!你晃得我眼都花了!” 虽然我目前处于走廊的位置,这里没有时钟,我的手机因为暂时拘留的缘故而被强行没收,估计现在已经没电。这时候称之为万能的智能手机仿佛还不如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表实用。虽然我看不到时间,但我知道现在已经开始天亮了,外面的世界出现着令人看到一切希望的曙光。 我略为不安地说:“他进去那么久,为什么还没有出来呢?” 她安慰我说:“你给点耐心吧,无缘无故跳出一个可以证明你清白的人,在司法程序上,的确要问得很仔细。” “他的证供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同事关系而遭到怀疑?” 我忧心忡忡地问着,寻思着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她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把握,皱着眉头,声音压得很低。 “应该不会的,只要他们可以证实他的口供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信任,一般都会采纳。” 她说的是一般可以采纳,换言之也不可以代表百分百。 看着她很安然地趴在窗户那里看风景,我倒是起了调侃她的心情,装模作样地默默靠近她。 她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很容易就察觉到我的存在,她的肩膀稍微往后缩了一点,脚步往左移动,企图远离与我之间的距离。 “那天……你去哪里了?” 我故意拖长尾音,刻意制造让她紧张的氛围。 她浑身不自在,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没去哪里……我只是临时之间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所以你就一言不发地抛下我在诊所。” 我冷静地说着,其实我并不介意她这样做,但那天我醒过来之后并没有看到她,心情自然会有点失落。我只是想要知道答案而已,只是一个答案。 “我没有抛下你!后来我有跑回去,但是你已经离开了诊所。” 她固执不已地说着,极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失。 “是吗?那我还得感谢你?第二天批准我回自己的家。” 她极度不愉快地离开我的视线范围,故意用背影对着我。 或许我不应该这样质问她,我带着哄她的口吻说:“不过……我还得感谢你,如果不是康薇医生,我想,到现在我都找不到那个时间证人,用他来证明我的不在场证据。” 她那不愉快的脸部表情瞬间消失,恢复昔日的欢笑。 “被催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她好奇地问我。 耍我?我决定要耍她一次。 我故作姿态,一副很严肃的样子:“感觉嘛……其实也没有太多感触,就是有一种不在其中但又触觉非常强烈的表现。” 她好像被我弄糊涂了,不以为然地说:“这么恐怖的吗?” “不是恐怖,是一种很病态的表现!”我故意调高音调。 她果然被我吓到了,心有余悸地说:“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的潜在危险?” 我就像一个巫师那样,用着古老咒语的口吻对她实行催眠性的语言:“在那个空间里……你最为脆弱的一面将会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直到你克服它……否则你会精神分裂……” 她真的被我吓到了,面色一片苍白,转过脸庞,捂着嘴巴,深沉地作出简单回应。 审讯室的大门被打开,随着’吱’的一声,其他警员已经带着元应子走出来,他低着头,垂头丧气的。 黄雁如似乎比我好着急:“怎么样?” “元先生的口供并无前后矛盾的迹象,大致上可以采纳他的供言,放心吧,接下来的手续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她很高兴也很欣慰地说:“辛苦你们了。” “份内事而已,晚点你们就可以销案,我们要下班了。”两名警员很有礼貌地向我们告别。 现场就只剩下我、黄雁如还有元应子。 我们三个以一个很奇怪的布局互相站着不一样的平衡线,顿时安静下来了。 她率先打破僵局:“嗯……我一整晚都没休息,先回去了!你们两个慢慢聊。” 我看着元应子,但他没有看我,或者是说,不敢看我。 她轻轻地扭着我的腰,用调皮的眼神暗示我:“不要太冲动。” 我给了她一个放心的眼神,她这才安心地离去。 在这个布局里,唯一的一个女人都已经离开,我们两个大男人,终于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 “去办公室聊吧,我们。”我抢先一步说着,务求要夺得交谈的主权把握。 他很难过地点了点头,默默地跟在我后面。 进到办公室以后,他倒是很识相地关上门,我终于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这种感觉……真的久违了。 或许是我脸上的这种万分享受,提醒了他某些事情。 他终于抬起头,凝视着我问:“在拘留所待着的日子是不是很难过?” 我略显夸张地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不过,就当是体验艰苦又苦难万分的生活吧,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不起!”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我的手放在被拘禁在拘留所之前在看的那本书《大国的崛起与奔溃》的上面,胸有成竹地说:“如果对不起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也不会有霸权主义,更不需要警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令自己信服的理由。” 我轻描淡写地说着,实际上,我却很期待他口中的答案。 “我知道,那天是我陪你去酒吧喝酒,是我看着你一杯一杯地喝醉,我的确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你有不在场证据的人。” “既然你也知道自己是唯一的证人,可你为何一直保持沉默,不主动站出来为我澄清?如果不是我透过催眠的方式重新找回丢失的记忆,在那记忆中寻找到你那毫不起眼但确实普遍存在的身影,我可能一直都不知道,那天一直在酒吧陪伴我的人就是你!” 我几乎是嘶喊的状态。 他瞬间变得很颓废,不断地向我道歉,不停地向我鞠躬,我站起来,连忙扶着他,皱着眉头说:“我需要的不是道歉,你要给我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说法!” “当初我知道你被误认为是杀人凶手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也很愿意为你站出来澄清这一切。可是……我真的不能这样做!” 他还表现得很憋屈似的,让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 他咬着嘴唇说:“总之……我有我的私人原因,我不能站出来,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这下子,我更为困惑了:“现在事情已经揭露,你还有需要隐瞒的理由吗?” 他转过身,逃避我的眼神。 “你不要问了……我肯定不能说的,就当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不是现在!” 我看着他微微驼背的背影,心中不禁冒起一阵鼻子酸酸的感觉。 哲学家曾经说过,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心中秘密。如果那个人宁愿那个秘密烂在肚子里也不愿说出来,那他肯定有自己的理由,我们是不应该以任何的理由去逼问他,就算是深受其害的我,也没有任何的权利逼问他。 我将桌面上的书翻过来盖在上面,轻轻地安抚着。 “你走吧,这件事我以后再追究。” 我当着他的面,下了逐客令。 他随口地说着:“谢谢。” 下午三点半,特区政府正式撤销对我的控诉,虽然目前还没有查到凶手是谁,但疑点利益仍然停留在我身上,我已经重获自由。 换上自己的衣服,要回了那台早已经没有电的手机,浑身气味地坐上计程车,不假思索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拖着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身躯,淡入浴室,洗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热水澡,泡在浴缸里,我甚至差点因疲劳过度而昏睡过去,但还好,我还能意识到自己在泡浴缸,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无时无刻地起着不起眼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区区三个小时,我终于恢复了原来的状态,犹如凤凰涅槃般,一瞬间重生。 但我很快发现,手提电脑没有电。 冰箱里的啤酒都没了,只有一桶过期的冰冻牛奶,我毫无饮用的欲望,万分失望地关上冰箱的门。 我自己窝在家里,足足两天,直到第三天降临,我的精神状态终于恢复正常,这时候我必须要去找一个人。 钟警官租的房子其实是很糟糕的,附近居民质素差,形象粗鲁,环境恶劣,像我这种那么随和的人,都不能接受那么糟糕的环境,不过我是来找人的,这些我就无所谓了。 敲开了她的门,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望见我的到来,倒是显得很惊讶,困惑地问:“你怎么来了?” “关于这件案子,我有新的想法。” 话音刚落,她就要将我拒于门外,门即将要关上,我用左手挡着残余的一点空间:“这是要赶我走的意思?” “不是,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再碰这宗案件。” “给我一个理由。”我冷冷地说着。 “元应子是我的表弟,他是我的亲属,我们有利益关系,他既然涉案,那我就不可以再插手这宗案件的调查工作。” 我眼珠子咕噜一转,十分狡猾地说:“恰巧就是因为他是你表弟,有些调查工作需要你的配合,才能顺利展开。” “啊?”她嘴巴撑开半天,没有合起来,我真想替她合起来。 “现此声明,接下来的调查结果或许会令你大吃一惊,或者感到匪夷所思,但这的确是铁一般的事实。” 我们找了一家咖啡厅,面对面这样坐着,我们努力地保持着沉默。 她盯着眼前的咖啡,我扶着下颚。 “给我说说,你与元应子之间的关系。”我忍不住开口了。 “他是我表弟,我们在十岁那一年已经见过,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家伙,对海上的风景异常着迷,更喜欢欧洲以前的历史,在那个称之为美好的年代,1913年之前的世界秩序,他是那样的景仰。他高中还没有念完,就匆匆忙忙地跑去做船员,到处漂泊,横跨印度、英国、美国这些大国家,太平洋的风景独好;英国的伦敦使他流连忘返;停靠岸边的时光是那样短暂,他在岸上寻欢作乐,吸引异国女子,浪漫情史多半记载在寄给我的信封里,他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姿多彩,四海为家,逍遥自在,无拘无束;而我只能待在三点一刻,沉重乏味的教科书式生活,我对外界的憧憬是那样的充满好奇,懵懂与不安均与他寄回来的书信有关。” 是的,她的确说得很美好,也很吸引人,但这并不是我好奇的一部分,于是我不禁打断她的回忆。 “抱歉,我知道你的回忆很珍贵,但我想知道的是,他一直都有给你寄信吗?” 她从回忆中重返现实,不禁迟钝了一会,才断断续续地说:“呃……不完全是吧。他一直都有保持写信给我的习惯,直到2005年,他这个习惯突然停止了,我没有接到他寄的信,我感到很奇怪,按照他的性格,在船上遇到什么好玩新鲜的事情,他都会第一时间与我分享,文字是表达情感的工具;照片是表达意境的主要元素。但从那一年开始,我就失去了他的消息,我曾经写过好几封信过去给他,但全部都被退了回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写过信给他。或许他已经厌倦了海上的生活,又或者他已经回到中国,又或者他去了以色列旅游呢?这个很难说,他从小就对犹太文明很感兴趣,没准他真的去了以色列。但不管怎么样,从2005年开始,我就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直到那天,他突然回来了,并且来到警局找我,声称要找工作,对此我真的很惊讶……” 我往咖啡里加了一颗糖。 “有什么好惊讶的呢?”我问她。 “你想想,一个那么多年没有见过的表弟,突然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你生活里,甚至要求你替他找工作,换了是你,你都会感到无所适从,对吧?更何况……”到了最后,她似乎有难言之隐。 我好奇地凝望着她,她咬了咬嘴巴说:“当时我问他,擅长哪些工作。他就告诉我,在外国进修了法医助手这个职业,他这次回来就是要成为一名高级法医的助手。” 我冷冷地说:“就是指定要做我的助手。” “是的,我知道这样是很不符合规矩,但是他一意孤行,况且法医科的确欠缺一个得力助手,我只需要填一份简单的申请表就可以替他申请这个职位。” 我胸有成竹地说:“那一份所谓的申请表格肯定还需要我的签字,你冒认我签署了同意书是吧?” “很抱歉,当时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她显得很愧疚,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那样。 “这一次的擅自决定不像你一贯的作风。”我一言道破天机。 她叹息着说:“不知道为何,元应子虽然是回来了,我们的确很多年没见,可是他的眼神与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包括生活习惯,说话的方式,日常的行为模式,还有饮食习惯都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时间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一下子将他的生活习惯全部改变了,这个例子我还是头一次见!总之,他的眼神很奇怪,我们对话时,他的气场显然是压在我之上,尽管我们的年龄只是相差一个星期左右,我只是比他早一个星期降临到这个世上,他就得喊我表姐。他给我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至于哪里出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还可以聊一整晚,但现在聊不到三句就放弃了。” 我默默地补充了一句:“但他的外表就是元应子,只是性格不一样了而已。”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2001、2005……两个年份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她提出了假设:“云沛沛究竟躲在哪里呢?假如她真的回来这个地方,她一定会主动找郭文轩,可是我们已经找人调查过郭文轩平时的日常生活,发现并无可疑的人出现在他身边。” 我接着说:“现在他被刑事拘禁,她更加不可能找他。” 她还在苦苦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一下子喝光了杯子里的咖啡。 “想象一下,云沛沛当天如果漂泊在大海里,不小心被人救走了呢?顺着大海的漂流,她会途经哪些城市或者国家?” 她执意地说:“无论她会漂流在哪个城市,她脸部毁容是肯定的,这是无容置疑。” 一阵激灵,我迅速窜到她身边,在她耳边低声地嘀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