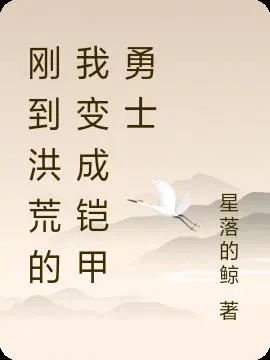当初,册立太子大典暨禅让大典,到底还是没有搞成。 这固然是有群臣规劝的缘故,也是宣仁皇帝心不甘情不愿所致。 在封建王权巅峰的时刻,谁会舍得手中的权力? 不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是没有人会选择放手的。 尤其是宣仁皇帝缠绵病榻十余年,病情时好时坏,所有人都习惯了,就连宣仁皇帝自己都习惯了。 所以,太子册封大典之后,禅让就没人再提。 而如今,宣仁皇帝一副闭眼西去的模样,他也知道自己熬不住了,直接选择了传位。 幼主临朝,老臣辅政,在大明虽然不说习惯,但早就有了章程。 内阁首辅的位置,阁老们依次上位,而八部同样如此,左侍郎递进,中上层尽量稳固。 但就在大家伙开心的准备瓜分权力蛋糕的时候,宣仁皇帝突然就来了这一出。 祁寯藻捋了捋胡须,抬起一双饱满的眼睛,直接问道:“陛下,西洋与中土迥异,不可类比。” “太祖高皇帝祖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此西方那继承人排序强多了。” 众多阁老纷纷点头。 而在一边,两位懵懂的幼童则满脸恐慌,抓着奶妈的手就不放开。 年长几个月的,则是夏王幼子朱敦浵,他被等为安邑郡王。 而圆溜溜脸盘的,则是魏王庶长子,河东郡王朱鸿笙。 两位幼童都时常被皇帝召见嬉闹,等闲不被大臣们见到。 宣仁皇帝瞥了一眼两个幼童,一个是侄子,一个是侄孙。 最后他又看了一眼太子,不由得心中一叹。 太子年幼,从娘胎里带出的病,基本上离不开药罐,内廷上下无不担心。 这个年龄的孩童最容易夭折了。 所以,必须要有储备。 按照皇明祖训那一套,夏王居长,兄终弟及之下,夏王世子将会递进为储。 可是夏王世子不能人道,病怏怏的身子,日后还得传位给他弟弟。 这不就是让大明的皇位持续动荡吗? 且,人家两个儿子都做了皇帝,必然会尊崇自己的老爹,他这个伯父指不定被忘在犄角旮旯了。 怕是身后之名都保不住。 而河东郡王则不同。 他是庶长子,父母虽然健在,但却是有嫡长子,根本就轮不到他继承魏国。 故而,河东郡王是最合适不过了。 “尔等说的有理!” 宣仁皇帝有气无力道。 他就是这个软性子,见无法达成,就立马转换了个说辞: “河东郡王,吾甚是喜爱,而朕在位三十年,虽然诞下数位皇子,但却无一成年,别人都在抱孙子的年纪,我却只有羡慕的份。” 内阁目光对视,心中顿时一跳。 余光不自觉地偏向了懵懂中的河东郡王。 其他大臣们也同样如此,虽然看着皇帝,但全心思却集中在了河东郡王身上。 “早年间,大皇子长成至七岁,就不幸弃朕而去,如今已过二十三载,前些时日,朕做着梦,见着了他的面容。” “他说别人都有香火,儿孙祭拜,他怎么没有,只有我这个父皇给他上香火……” 听到这,只要不是个傻子,立马就明白了皇帝的所思所想。 但却无一人阻止。 陷入回忆中的宣仁皇帝面带笑容,说不出来的宠溺。 片刻后,他恢复过来,指着河东郡王朱鸿笙道:“今日,朕决定将河东郡王过继给仁孝太子。” “册封其为晋王!”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 晋王之爵,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是重号王爵,在大明也同样如此。 在前明的晋王断代后,这个爵位一直留着,根本就不舍得册封。 而如今河东郡王成了晋王,那就是板上钉钉的第二继承人。 同一个枝叶下,晋王的继承权明显大于夏王。 众人的目光又投向安邑郡王,眼神中满是怜悯。 2选1,夏王终究还是比不过魏王。 果然,皇帝对于魏王的宠幸,是别人比不了的。 亲爹没机会,儿子却机会大增,真可谓是极具戏剧化。 但同时,这又留有了余地。 假使太子日后成年,真的生下子嗣,大不了给这位侄子册封个好地方。 皇帝这是坐一望二呀! 祁寯藻心中一叹,拱手拜下:“老臣遵旨!” “臣等遵旨!”一众文武纷纷拜下。 宣仁皇帝笑了笑,握住了儿子的手,不舍得放开。 小家伙瘦弱的胳膊,看上去都经不起一拽,稍微一碰就能倒下。 “父皇,父皇,疼,疼——” 太子忍不住哭了起来,撇着嘴,扑向了一旁的奶妈怀中。 而这时,在众人的目光之中,宣仁皇帝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作为首辅,祁寯藻自然是大权在握,他直接站起身,将太子的胳膊小心翼翼的从皇帝的手中抽出,安抚着,宛若爷孙。 然后他又让人抱着两位幼童。 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他安抚着太子,抱着他坐上了一旁的椅子。 只见老宦官拿起线香,伸向皇帝鼻下,一缕青烟凝而不散,他缓缓放下线香,转身碰头:“皇上归天了!” 宗室之长,驸马爷李之荣擗踊大哭出声,双手捧住皇帝的双脚,把脸埋进去,放声嚎啕起来! 这可是他的岳丈呀! 虽然公主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还有外孙不是,皇帝一死,他的富贵就真的急转直下了。 正殿中已经设了一把罩有明黄椅披的太师椅,祁寯藻把太子小身子安于其上,先一步跪了下去,碰了三个响头: “老臣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人反应也不慢,一个个得跪下,毫无丝毫的迟疑。 懵懂的太子,这时候也止住了哭泣声,他抓着奶妈的手,小眼睛滴溜溜地看着众人。 在这一刻起,他已经是嗣君,只缺一个登基仪式了。 立下了君臣名分之后,祁寯藻又安抚着急切想走的嗣君,站在一旁高声道: “先皇统御海内三十载,享年四十八岁。 先帝继世祖谟烈,修明政治,条理万端,躬勤爱民,实乃国朝之圣君。 臣以为当遵祖宗成例上以佳号,奉安龙穴,这是此时最要之务!” “现在有几件要务立刻要办。 首先,大行皇帝的谥号庙号要定。 然后召集百官宣布中外,由礼部主持拟定丧仪,稳住朝局。还有些常例恩旨,待举丧之后再议不迟。” 这一番话,不急不躁,铿锵有力,一下子就稳住了众人的心。 这就是长者的威力。 他们懂得多,见识的也就多,天然就具有领导力。 紧接着,祁寯藻就自领治丧大臣,将整个内阁,以及各部尚书,都察院都列入其中,人人有份。 目前整个大明最要紧的事,就是给大行皇帝举办丧事。 举国同哀,大明六十余藩国,都要被通知到,前来参加葬礼。 其中的礼仪之繁杂,让人咋舌。 不过好在多年的陈例在那,别管他有多么的腐朽和不堪,只要沿着礼部的老规矩进行,就不会出错。 妥善的安排了各种事宜后,祁寯藻还不得歇,他要紧急的给大行皇帝取谥号,庙号,以及嗣君的年号。 世祖皇帝大行减字,让谥号变成了两个字,实际上却只有一个字。 “元字如何?”魏源开口道:“大行皇帝行义悦民,最适合这个字。” 祁寯藻点头应下。 这个谥号四平八稳,最为适合。 众人也达成了一致意见。 所以大行皇帝的谥号就定为元孝皇帝。 至于庙号,反而不急了。 毕竟内阁大权独揽,着实太容易招人恨,还得让那些老臣们一起议定的好。 背锅也是一起背,不可能让内阁一背。 那么多年以来,除了是亡国皇帝,不然的话,谥号根本就没有坏的字眼,自然也没多少人在意。 而庙号则不同,一字褒贬,流传天下。 世人最为关注的就是庙号了。 在这种事情上,由不得他们小心翼翼。 而在年号上,那个却分裂成了好几块。 魏源直接开口:“不如采用同宪,不仅树立嗣君革新的想法,而且也能得人心。” 曾国藩则不同意,他直言道:“标新立异并不好,我觉得,可用昭华,大明繁华兴盛。” 祁寯藻则否决了两人的意见,再次推脱道:“既然无法抉择,那就交由朝议来定吧!” 接下来也同样如此。 但凡内阁之中吵闹甚多的,祁寯藻就一律推诿到朝议上。 众人也立马知晓了他的心思。 这是怕背上独断专行的骂名,所以选择了众议来堵住滔滔舆论。 一直到了下午,议程没有成几个,彭蕴章忍不住笑道:“干脆叫同治得了!” 这一下,他立马就遭受了几位阁老的眼神攻击,不得不低下头。 “阁老!” 这边,邵秋儿来到宫中,抱着满脸惊恐的儿子,准备离开宫门。 而她就见宫前东廊,几个太监穿换孝服分发孝帽,见她来了,忙疾趋而来,满脸戚容,哆嗦着嘴唇,哀不自胜。 邵秋儿看着这雪白的衣帽,又转脸看看已经糊了白纸的慎德堂和远处的正大光明殿正门和到处布满了白花花的幔帐纸幡。 在半阴半晴的天穹底下冷风吹过,金箔银箔瑟瑟抖动着作响,似为离人作泣。 她抱着儿子,感觉就像抱着一个金秤砣,睡着极为香甜。 这一天的折腾,让他早就没了之前的活跃了。 一路上,无论是太监还是宫女,对着她都露出了讨好的笑容,在这哀嚎声不绝的山庄,显得格外的突兀。 但是众人又觉得理所当然。 这就是权力,让人不得不哭,又不得不露出笑脸讨好。 邵秋儿并不觉得这是好事。 哪怕她望子成龙,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从小就沦陷在权力的漩涡之中,变成了冷冰冰的政治人物。 当一个河东郡王多好,无忧无虑的长大,然后又被封国,称孤道寡,子嗣连绵。 但如今呢? 所有人都在等着嗣君什么时候夭折,内廷都在准备着即位大典,给她的儿子丈量身子。 毕竟龙袍制作不易,没有一年半载根本就无法制成。 所有人都理所应当地奉承她,奉承她的儿子,这让她极不适应。 “娘!”二人刚上了马车,怀中的儿子就醒了过来,他喊了一声然后低声道:“皇爷爷走了!” “是的!”邵秋儿叹了口气:“你皇爷爷走了,以后就没有人宠你了,不能再那么肆意妄为了。”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调皮!” “不对!”小人儿眨了眨眼睛,调皮道:“大家伙还会让着我的。” “怎么?”邵秋儿眯着眼睛问道。 “大家都说,我以后不能叫父亲是父亲了,得叫叔父。” 小小的晋王,懵懂而又狡黠地说道:“以后我就会是太子了,谁都不敢欺负我。” “娘,你也不能再打我了!” “是吗?”邵秋儿捏着他的儿子,开始了转圈。 “疼,疼!”朱鸿笙忙叫起来:“我再也不调皮了,不敢调皮了。” “你呀!”邵秋儿抱着他的小脑袋瓜,亲了一口,然后笑着揽在怀里: “要不了多久,你爹就会回来看你了。” “咱们笙儿吓他一跳,到时候多背几首古诗,让他好好夸夸你!” “哦!”朱鸿笙点点头,然后睡眼蒙眬的应下,眼睛不自觉的就闭了起来。 待回到魏王府,门前已经是车水马龙。 各勋贵家的贵妇,一个穿着素装,登门拜访,手中的礼物一个赛一个珍贵。 见此,邵秋儿已经习惯了,她笑着一个个的收下,然后又让人记账本,准备送回去。 北京城,对于权力就是那么的敏感,消息还是一如既往的灵通。 管家也忍着笑意走过来:“娘娘,内务府刚才来人了,准备把旁边的一片住宅给划过来,把咱们的王府直接扩建。” “省得到时候再拨一个王府,让晋王与您隔开了。” “不用了!”邵秋儿忽然停下脚步,沉声说道: “让他们重新建个王府吧,我知道内务府不缺钱。” “扩建魏王府,到底是不合适了……” 管家一时间有些茫然。 他看着远去的侧王妃,一时间只觉得神秘莫测,浑身充满着贵气。 而在其怀中睡着的晋王,则紫气逼人,可谓是贵不可言。 “魏王他老人家,怕会高兴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