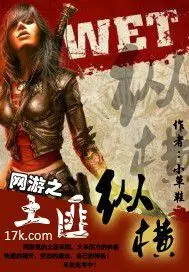姐姐正襟危坐,许是因为强忍着怒气,那张雪白的小脸涨得通红,原先交迭在小腹上的双手在他一通质问中相互紧握,白皙的手背上隐约浮现着青筋。 翌日,慕恩便因为长期任务外出,又过没多久,为了取得极其稀有的金属素材,赛菲尔跟着师傅开始南向的长途旅行,对于家乡的事情都是通过订阅的报纸以及师傅在冒险团的人脉了解。 比如爱玛终于嫁给了查尔斯,可是身体一直不太好,再比如慕恩突然销声匿迹了两年,再出现时便从现役的冒险团转为兼职,依然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出没模式。 关于她的这两年,隐匿踪迹后去了哪里,无人知晓,本业改做什么,没有告诉任何人。大概只有苍玄门那位兼任冒险团团长的,同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幽灵首领才知道。 他们就这样进入了冷战期,各自投入自己的事情,对彼此不闻不问。 不,其实慕恩有几次尝试联系过他。 但是每当通讯水晶响起来讯的美妙铃音,看到显示出来的号码,他都会犹豫好久,这番举动被师傅笑称像个别扭的小姑娘似的,只差没有长长的发辫给他拧。 可是,一想起好友临行前那落寞的背影,以及姐姐坚持己见的面庞,最后的铃音总是以嘎然而止作结。 这样的情况反反复覆发生过四五次,时间久了,那支号码就再也没传来任何讯息。 ………… “年轻人啊,听老人家一句,有的时候太过固执,到头来吃亏、后悔的,只会是你自己罢了。”喝完酒开始抽起烟的老师傅,语重心长的这么对他说。 听闻凡之上神的神使.安斯尔一族,因为侍奉的神祇乃命运之神,所以其族人每个都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展现于梦境、预兆、话语等各个方面上。哪怕是血缘稀薄的混血后裔,也会具备着被不知情的人称作“乌鸦嘴”的能力。 不知师傅是否也是安斯尔一族的后人……因为没几天后,赛菲尔确实后悔,毁得肠子都青了,也找不到后悔药可医。 就在爱玛丽丽丝不幸过世的一个月后,苍玄门冒险团传来的讯息,慕恩和雅穆尔在不归山执行任务时,遇上从未见过的新型魔兽。 雅穆尔回来求援,没有任何大碍。 至于慕恩……至今下落不明。 师傅说,冒险团的首领动用了苍玄门全部的人力,也没有找到人更没找到那头据说长得十分狰狞丑陋的魔兽,只有在现场找到大片的血迹以及破碎不堪的衣服碎片,经过缜密的检验,没有魔兽的血,全是慕恩一个人的血。 而那样的出血量,任谁看了都会觉得伤者必死无疑。 碍于不归山的深处便是落天山脉的地界,进入此处的人无一回来,连“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都难以做到,不仅如此,搜救队入山才不过一天的时间,就先后失踪好几位成员。 最终,搜索只能到此为止。 慕恩在冒险团数据上的状态,也从“失踪”被登记为“殉职”。 当赛菲尔回到爱普莉城时的第一件事,就是狠狠的揍了雅穆尔一顿。怪他为什么抛下姐姐逃跑,哪怕对方告诉他,是慕恩让他先逃的,而他内心深处其实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这个一直真心喜欢着姐姐的男人。 即便如此,他依旧放下狠话,要雅穆尔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雅穆尔没多久就离开了冒险团,听说后来先回东方老家一趟,辗转进入圣教会去当书记官。大概隔了一两个月,本来人数就不算多的苍玄门冒险团宣告解散。 那之后……那之后又经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日子,赛菲尔是怎么度过的? 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浑浑噩噩的大脑内,只记得在冒险团解散后又过了一阵子,他毅然决然告别了铁匠师傅,和刚结束冒险见习的维克、温妮莎二人向冒险者国际公会申请重建了新的冒险团,挂在苍玄门名下。 铁匠老师傅一语成谶,赛菲尔在后来的十几年光阴中,他怨过,也悔过。 怨雅穆尔干嘛要那么听话的抛下姐姐,怨冒险团为什么不继续搜索,怨慕恩当时为何要逞强留下,更怨一直没有好好听姐姐说话的自己。 他跟迪斯没有再联络──不得不说他们俩还挺有默契的,断绝了书信、通讯水晶等一切的往来方式,就像是为了要赎罪一样,更像是要挥别那些令人伤心难过的往事。 说穿了,最根本的原因只是因为赛菲尔在赌气,因为听说雅穆尔是被迪斯邀请加入圣教会的。 他将所有的心力放在了新生的冒险团。名义上他不过是冒险团的副首领,不过实质上他和维克共同打理着冒险团的事情,订定新的规矩,毕竟冒险团的团长依然是苍玄门的那位影子首领,彻底落实了何谓幽灵人口。 顶多就是在赛菲尔他们建立新的冒险团时,推荐了一对兄妹加入,任务的发布都是让苍玄门底下的人事管理来转介,平时的任务报备也都是透过讯息水晶传递。 时间的脚步就这样不疾不徐的走着,既像个悠闲散步的旅人,有的时候步伐却又快得使人感觉一眨眼便溜了过去。 称不上是刺激,也不算平淡,但总归是让一切步上了正轨──除了某个黑发青年经常打破规定,丢下自己的临时搭档偷跑去做任务以外。 【新历一百零四年.爱普莉城.龙腾酒馆】 “梦?”好友维克在听完他的话之后,低沉的声音轰隆隆如闷在厚重云层中的雷声,因某种原因而单纯的一只眼睛。 “嗯……今早作的。”这时候已化名为万的赛菲尔,瓮声瓮气的回答,将手中的红酒大口饮下。 “适可而止点吧……金格回来看到你这样喝,又要在那边鬼哭神号了。”早上出去批货的朋友回来后,见着这副情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维克不用想都能猜得着。 万没有理他,自顾自地继续豪饮着。 足足二十五年的回忆在梦境中重演,多么的精采万分,有声有色,简直就像人生的走马灯似的,仿佛又再重新经历一遍那些酸甜苦辣。 若是一觉醒来忘掉大半的内容倒还没什么,偏偏他到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包含那些想要遗忘的记忆,教他如何能好受。 这也是他为什么心情不大好,大早上的就在酒馆内和好友喝闷酒。 昨晚到三更半夜才解决了任务报告的维克,一大清早的被搭档从温暖的被窝中挖出来,坐在酒馆内迷迷糊糊地听着搭档劈哩啪啦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后,终于醒过神。 要不是看在对方明显心情不虞,他在被人掀被子的那一秒,大概会直接出手揍下去了也说不定(纯属半梦半醒的反射动作),底下两个臭徒弟都因为这样被他打过好几回。 “我从刚刚就想问了,那是什么?”他见搭档一手紧握着酒瓶,另一只手里紧握着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张照片……被万用力抓在手中都快看不出原样。 “这个?零昨晚给我的。”万举起攥着东西的手,大着舌头,看起来有些傻呼呼的回答。 他没说的是,刚结束任务的黑发青年,脸色一反常态的难看,对他的打招呼也充耳不闻,直接将一封薄得像是什么都没装的米色信封塞进他怀里后,转身一头栽回了宿舍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