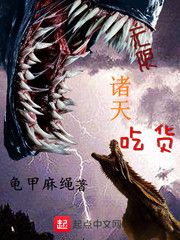罗醒了开着陆巡在马路上一点一点的挪着,堵车。刚下午五点多钟,天还很亮。冯国栋给自己的这辆车很不符合自己的心意,自己想低调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这辆车太大了。 车里正在播放着一首老歌,王迪的《不觉流水年长》。罗醒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在上高中,当时他就感觉心里似乎被勾起了几丝无法形容的伤感。虽然也有交往的女朋友,但那时的他自觉还不懂爱情。但是歌声里那对于逝去过往地无奈嘶吼,却每每的令罗醒了恍若已经沧海桑田,不能自已。 进了家属院,罗醒了特意的把车停在了自家所在的楼的后面。他抬起头看着三楼那几扇熟悉的窗户中透出的光,感觉一切还是温馨如旧。 接过母亲手里递过来的拖鞋,耳边也同时传来母亲那熟悉的絮叨声。犹如他从前每日放学回来时,一样的亲切自然。浑然不觉距离他上次回家时已经一年有余了。 “你这个倔孩子,就不能先回家吗?地球离开你一样转,可父母离你远了心里会不舒服。知道吗?再说你爸马上就要退下来了,也不会再干涉你了。你就不能先服个软?我不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往家里打?你看看你,比上次见你时黑多了。南方那边的水土养不好咱北方的苗。” 母亲说着,掸了掸罗醒了身上那本就不存在的尘,仿佛已经掸去了游子身上的疲惫。罗醒了笑着,就那么静静的听着。 “进去吧,你爸在书房呢。饭一会儿就好,你们爷俩先聊会儿。” 罗醒了推开书房的门,见父亲正低着头在练毛笔字。大字,一张半幅的宣纸就写了一个字:“滚”。地上散落的几张宣纸上也是一张接一张的“滚”字,罗醒了瞬间一脑门子黑线。这老爷子得是多大地怨念啊?不会是冲自己吧? 罗醒了的父亲叫罗逸夫,今年已经六十有五。比他的母亲文洛大了整整十岁。罗逸夫是外联部的副部长,标准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而比一般的知识分子“超标”的除了职务之外就是脾气。用罗醒了母亲的话讲:你爸就是那个意甲的球队“切沃”。罗母是一个少见的大龄女球迷,而切沃队的队徽是一头会飞的的驴。 “切沃”同志抬起头,瞥了一眼盯着地上满是“滚”字发呆的罗醒了,又低头继续写。 “那不是给你的。” “我说也是嘛,我可是您亲生的。再滚还能滚到哪里去?您这是要离休了,开始学着陶冶情操了?” 话一出口罗醒了就后悔了。跟大师兄厮混没两次,自己这情商也被拉低了许多。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你是不是觉得我以后管不了你了?你大可以试试?无论到了什么年代,这驴再怎么转圈儿,驴尾巴都冲地。” 看来“切沃”同志不但不忌讳别人对自己驴脾气的调侃,反而还每每引以为傲的要将其大而化之。 “我就说嘛,老一辈儿革命家的胸怀怎能如此狭隘?我一直期待您的“敦敦教诲”,我们年轻人还是需要你们这些老同志扶上马、送一程的。要不然会走弯路,不把牢。” “少给我贫,是谆谆教诲,不是敦敦的。你如今能得到李大驴子的青睐,也许应该会有点儿出息。” 听父亲称呼师傅李伯驹为李大驴子,罗醒了差点没憋住笑出声儿来。看来这还真是脾气相投啊?按说两头倔驴应该互相掐架才对啊?再说您要夸我就好好夸,还应该也许的?我就这么不被您看好?这才刚一回来,您的“人生指导课程”就立刻开始了。还是顿顿不拉的,不是敦敦教诲是什么? “您和我师傅很熟吗?以前怎么没听您聊起过?”罗醒了看父亲停笔了,马上端起一旁的茶杯递了过去。 “李老头是我的手下败将。”也许是觉得当着儿子的面称呼其师傅的外号有些不妥,罗逸夫随之换了个称谓,但语气中还是颇为不屑。 “当年他也追求你母亲,被小文同志果断的拒绝了。小文同志当年可是中青联的第一美女。他收你为徒我看也是别有用心。” 哇哦?师傅和自己父母还有这么一段“绯闻史”?看来调自己回来应该不是老爸的主意。难道是老妈?抑或真是如师傅所说的“知根底”? “李老头的本事还是有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手艺还不错。你要好好学,我罗逸夫这辈子从没输给过李伯驹。你不要给我丢人,学好一门手艺将来也能有口饭吃。” “我可是新时代的接班人,是要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的。怎么可能只是有口饭吃就行?您这标准定的也太低了吧?这是又不打算愉快地聊天了啊?”罗醒了在心里腹诽。 见儿子戳在一旁不说话,罗逸夫就摆摆手:“你先去陪你母亲吧?我再写一会儿。” 罗醒了将茶杯放到桌上,点了点头转身出了书房。 “又被你爸给撅出来了?这个老东西真是越活越回去了。”母亲用力地揪吧着菜叶,仿佛是在给儿子出气。 “没有,就是老爸讲了讲你们当年和我师傅的三角罗曼史。” “这个老不羞的,你个臭小子也瞎凑什么热闹?哪有什么罗曼史?还三角?你妈我那时候年轻,刚参加工作没多久。谁知一下子就碰上了个倔驴,还是两头。 我也是当时昏了头,也没琢磨是不是还有第三头?就胡乱地在两头倔驴当中选了一头。唉,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应该再等等的,还是图样图森破啊!” “别啊?您当初要是再等等,可能就没我这么英俊潇洒还雪白的儿子了。您看您现在依然还是很年轻啊?还会引用网络流行词儿呢?多时尚。” “放屁!到什么时候你也只会从妈的肚子里出来,怎么会变?这就是命啊?碰上了两头倔驴还不算,如今又生了一个小倔驴。再年轻又有什么用,不也还是养驴的命? 你现在有对象没有?马上就要二十六了还不着急?你看好多比你妈我岁数还年轻的,现在都当奶奶了?你爸马上要退了,我没两年也该到线了。到时候有大把时间给你带孩子,也不会耽误你工作。” 好嘛,您这都计划带孙子了?我媳妇还在丈母娘的腿肚子里转筋呢,您就不怕再给您添个小小驴?罗醒了没敢接话。 “你说说你,上学的时候那么多人追你,好多都追家来了。怎么参加工作倒没有了?你能比国家**还忙?有看上的没有?这点儿你还不如你爸呢?好女怕缠郎,你应该学学你爸爸。 你爸当年追我的时候,几乎班儿都不上了。成天泡在我们单位,那就是把脸别在裤腰上,没全丢也差不多了。李伯驹当年笑话你爸,说你爸是光屁股抓贼-胆儿大不怕寒碜。还说什么老房子着火-烧的快,我听了以后一生气就嫁给你爸了。 跑题了,还是说说你。你说你这条件,咱们家这家境,你是不是挑花眼了?我跟你讲啊,这人和人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分。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罗醒了点头应和着滔滔不绝地絮叨的母亲,神游天外。貌似当年老爸好像赢得很侥幸啊?当前这话头儿不能接,母亲已经聊到脚和鞋了。根据过往的经验,这个话题应该快结束了。 “要不还是娇娇吧?我看“小辣椒”也挺好的。反正这么多年她也没少给你搅和,多少好姑娘都被她连哄带吓的不敢登门了?就是岁数还小点儿,还要再等几年。” 罗醒了听到这里浑身就是一激灵,连忙收敛心神:“别!您可别介?那个疯丫头我可消受不起。” “什么疯丫头?没听人说吗?女大十八变,人家现在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昨天见面还问起你来了呢?嘴甜的很,也温柔了许多。再说人家也是你的正牌未婚妻啊?!呵呵~” 罗母嘴里的“小辣椒”名叫焦不娇,今年十八岁。是前面三号楼焦锐的独生爱女。焦锐是罗逸夫的老部下和老搭档,比罗逸夫小七岁。大院里老夫少妻的很多,中年得子的更多。因此大院里惯孩子的也多,对女孩子的宠爱更是屡创新高。 焦不娇从小就生得粉雕玉琢、晶莹剔透。八岁那年随父母到罗家串门,扎着一根冲天辫的焦不娇很认真地对罗醒了说:“你长得很好看,我长大要嫁给你。” 大家都在笑,罗醒了也笑。摸着焦不娇的冲天辫,开玩笑的应着:“好啊,我等你。” 从那以后,罗醒了的青春期躁动症就不药而愈了。除了罗母以外,一切出现在罗醒了身边的雌性生物都被焦不娇“赶尽杀绝”了。小丫头俨然已经以未来的罗家女主人自居。 一开始大家都乐呵呵的没当回事儿。又由于焦不娇的年岁小,监视罗醒了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最初并没给罗醒了造成多大地困扰。对于小丫头的执着,大人们也都当是茶余饭后的一点趣事儿,一笑而过了。 当十三岁的小丫头,依旧梳着冲天辫,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安大学门口,对环绕在罗醒了身边的花花草草郑重宣布:“我是他的未婚妻,他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你们不许再打他的主意,他是我的人。我的男人。” 直到此时,罗醒了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可能不严重,校领导都找谈话了。这是在祸害祖国的花朵啊! 后来还是焦母和罗母一起到学校才把事情解释清楚。但从那以后罗醒了身边的花花草草就少了许多,而且还得了一个“罗叔叔”的外号。暗含着说他罗某人,是一个经常诱拐小姑娘去看小金鱼儿的怪蜀黍! 罗醒了毕业的时候,十七岁的焦不娇依旧扎着一根冲天辫。小丫头对他再次宣示主权:“你把你的过往交给我,我把我的青春许给你。这辈子如此,下辈子依旧如此。” 罗醒了毕业以后之所以选择“远走他乡”,父母过度的“指导人生”是其一,焦不娇的影响是唯二。 “看来今天晚上必须回单位,家里已经不安全了。” 罗醒了在心里如是的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