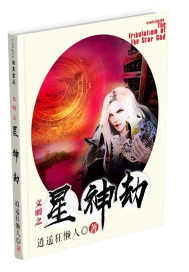刘元提了一壶酒,端了一盘烧鸡,看了一眼屋子里正吆五喝六地吃着酒,划着拳的一众同伴,微微一笑,反脚掩上了房门,走了出去。 营房之外,一株大树之下,葛彩靠在树上,正一块一块地撕着一个白面馒头吃。 “看什么呢?”刘元走了过去,将酒递给葛彩。 葛彩瞟了他一眼,接过酒壶,道:“这宝应城,也相当繁华啊,比我们武邑也差不了多少。” “这里可是扬州!”刘元笑着说,却又突然反应了过来:“你来自武邑?” 葛彩微微一笑,仰脖子喝了一大口酒,却是将刘元递过来的烧鸡推了开去:“吃不得这些了,再吃,以后就更没人要了。” 刘元哈哈一笑,撕了一只鸡腿咬了一大口,从葛彩手里接过酒壶,自己也喝了一口,“说句老实话啊,现在美酒烧鸡的吃着,心里却还在想着你的杂面煎饼子,你说是不是有些贱骨头?” 葛彩翻了一个白眼,“即便是现在你想吃,我也没得空做。” “那等以后有空的时候再说吧!”刘元笑道:“吃了你两年的杂面煎饼,还真是吃顺味儿了。说句实话,我是真没有想到,你和我也是一样的人,不不不,你的职衔可比我高。” 葛彩看了他一眼,道:“我是从武邑来的,职衔比你高一点也不稀奇。” “你以前在哪支部队?不会是右千牛卫的吧?”刘元有些吃惊地道:“柳大将军麾下有不少女军官的,你有这么硬的靠山,跑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是跟夫人的,我以前是跟着大姐头儿的。”葛彩摇头道。 “大姐头儿?是谁?怎么没听说过?”刘元瞪大了眼睛,葛彩自己都是昭武校尉了,她的上司,最起码也是将军起步了。 “哦,大姐头是李泌。现在是卫尉寺的少卿。”葛彩道:“当年在大青山的时候,我就是跟大姐头的,后来也一直跟着她。” “原来是她?”刘元恍然大悟,“你这靠山也够硬啊,干嘛还跑到这里来?” 葛彩叹了一口气,道:“当年在危月燕中,有很多姐妹的,我从小就吃得,倒是愈长愈胖了,也常被人耻笑欺负,也就是大姐头护着我,那些姐妹们学得东西可多啦,棋琴书画,针炙医药,我呢,学啥啥不会,吃嘛嘛不剩,就只剩一把子力气了。” 刘元卟哧一声笑了出来。 “有什么可笑的?”葛彩瞪了她一眼。 “两年前,大姐头嫁给了曹璋,我总不能不辈子跟着大姐头儿吧,在武邑,像我这样身份的人,打仗的机会极少了。其实即便在别的军队之中去,也不太可能让我一个女的领兵。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便求了大姐头儿让我过来了。”葛彩道。“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独挡一面的将军,就像大姐头和夫人一样,看那些当初笑我的人还笑不笑得出来。” “看来你当初受了不少气啊?”刘元若有所思地道。 “一个女军官,在军中本来就很难立足的。再加上我又这模样儿,自然就更不受人待见了。”葛彩道:“我总不能受了欺负就去找大姐头儿告状吧?也不能受了欺负就跟人拳脚相加吧?出来干这事儿,正好。” “难怪你这么凶?”刘元哈哈一笑:“来到宝应,秦疤子都被你找借口揍了一顿,是在立威吗?” “有什么办法?”葛彩道:“现在要打仗了,而且还是极凶险的仗,要让这些血里火里爬出来的人服我,就只有凭拳头,不然我一个女人,怎么压服他们。一个凶悍的母夜叉,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好的。” 刘元又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那你怎么不找我?” “估摸和你打,要输!”葛彩倒是毫不掩饰。 “我可以故意输给你的。”刘元道:“就算酬你经常给我的杂面饼子里加大肉片子的恩情。” 葛彩哼了一声,“说来说去,你不还是看不上我吗?” 刘元一滞,却是说不下去了。 “没事儿!”葛彩却是洒然一笑:“我也就是看你顺眼,你看我不顺眼,那就没啥了。拿得起,放得下,以后咱们还是砍得脑壳换得气的兄弟呢!说说吧,你怎么来的这儿?” “我是义兴社员!”刘元一仰脖子喝了一大口酒,“为万世开太平,哪里有需要,我就愿意到哪里去。” 葛彩怔怔地看了他半晌,才道:“你是个真汉子。你以前在那支部队服役?” “左骁卫。”刘元道。 “左骁卫出事了!”葛彩道:“你知道吗?覃新明秦将军跟我说的。” 刘元摇了摇头。 “说来也巧,这一次过来统筹指挥的也是左骁卫的,负总责的是李浩李中郎将,而我们这些陆上部队的头头,叫任晓年,绰号任大狗,也是左骁卫的。” “任大狗?”刘元一怔:“我认得他的。以前一齐配合作过战。” “他现在都是将军了,你不后悔吗?”葛彩问道:“要是留在部队之中不耽搁这几年,说不定你也就是将军了。” “我将来肯定是能当将军的。”刘元呵呵一笑:“迟早的事情,有什么可后悔的。” “看到任晓年,你不尴尬?以前是同僚,现在可是你上司的上司了!” “他能当上将军,也是拿命换回来的,有啥尴尬的。”刘元不以为意:“仗还有得打呢,说不定以后我后发而先至。” “我觉得你能行!”葛彩从刘元手里把烧鸡抢了过来,咬了一大口。 “你不是不吃吗?”刘元笑问道。 “反正你又不要我,管我作甚!”葛彩冲着刘元挥了挥拳头:“吃饱了,明天再去训练那些瘪犊子。” “算了,大过年的,这些本地兵丁就这个样子,再练也练不出个模样来。”刘元摇了摇头。 “咱们在宝应的自家兄弟,只有一千人。”葛彩道:“这本地兵丁也有一千人,不说能跟咱们比,至少拉出去要能见仗啊,不然到时候还没开打呢,他们先跑了,那怎么行?兵是练出来的,刘元,这一次咱们面临的局面,只怕比你想的还要凶险。咱们的地盘,离这里太远了。反正覃新明说了,钱,他有的是,那就大棒和蜜糖一起来吧,你不是觉得他们练不好,你是嫌麻烦吧!” “的确很麻烦!”刘元咂巴了一下嘴,摇了摇酒壶,却发现酒已经没有了。 “想当年我们还小的时候,是屠二爷训练我们,为了一块糖,大家都能拼命。”葛彩嘿嘿笑着:“你瞧着吧,我非得把他们练出来不可,哪怕最终淘汰一部分,剩下的,也能派上用场。” 相对于扬州的表面平静,底下波涛汹涌不同,在淮南节镇所在地楚州,却是里里外外都透露出了一股紧张的气息。 淮南节帅龚云达已经调集了三万部队,其中包括五千水师,集中到了楚州,数万人的大军在淮安城外扎下了数个大营,光是粮草的调度,军纪的维护,都足够节镇府上上下下忙得四脚朝天,又适值年节,赏赐总是要发下去的,除开银钱的赏赐,什么肉食,酒水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士兵闹将起来,可不是玩儿的。 前前后后,调集这些部队花了一个月时间,海量的银钱自然也就这样哗哗的流了出去。就算淮安富庶,这样的花钱,仍然让龚云达感到有些肉疼。关键是,现在淮南内部对于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办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内部争论不休,让龚云达也是头疼不已。 “父亲!”龚彬走了进来,看着龚云达道:“除了扬州的梅玖没有来给您拜年,其它的各知州都已经来了。” 龚云达轻轻地捏着眉心,道:“不意外,梅玖是坚定的支持大唐的,对于我一直不肯公开表明态度而极度不满。” “到底要怎么做,自有父亲这个节镇一言而决,那里需要看他的脸色?”龚彬怒道。 龚云达抬起头,瞟了龚彬一眼:“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难道不是吗?既然此人与父亲的心思不一致,那就撤了他好了。换一个听话的。” 龚云达摇了摇头:“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梅玖在扬州的根基极其深厚,而且,他在扬州这几年,扬州每年上交的赋税,都是年年上涨的,此人为官清廉,极得民心。更重要的是,扬州商会是支持他的。” “父亲,扬州商会的会长可是金满堂。” “就是因为如此!”龚云达长吁了一口气:“所以他就更有底气了。你说撤换他,用什么理由?我调兵,他没给吗?我要加赋,他不是也爽快的给了吗?” “父亲,既然扬州的兵都已经出来了,那要撤换他,岂不是更容易,一支兵马过去,旦夕可定!” 龚云达冷冷一笑:“那你可知道,我将兵撤出来之后,数天之间,梅玖就又已经集结起了一支人数不详的军队吗?虽然不知道实力如何,但你想轻而易举的拿下他,是没有可能的,倒是激起民变的可能性更大。” “父亲,我来想想办法!”龚彬咬咬牙道。 “你已经打定主意了吗?” “父亲,我们哪有什么选择?李泽是很强,可中间隔着一个大梁呢!”龚彬道。“重要的是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实力,只要有实力,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