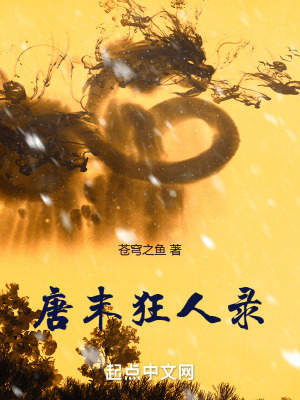“汝何人也?”一名河东牙将装腔作势的大吼。 “忠武,陈玄烈。” “为何传召两次方才入城?可知延误军机之罪?”一员披着明光甲的黑面将领站了出来,满脸虬髯,面相凶恶。 一看身边人对他的敬畏样子,就知道是朱玫。 这厮不过只是一个马步都教练使,派头弄得像都知兵马使一样。 实际地位也仅比陈玄烈的十将高两级而已,河东军怎么都轮不到他一个教练使在此吆五喝六。 教练使上面除了都知兵马使,还有马步都虞侯。 陈玄烈戟指大喝:“我忠武军只听朝廷号令,你乃何人?一无朝廷诏令,二无节度使军令,安敢在此口放厥词?” “大胆,我看尔等不是援军,分明是乱军!”朱玫先贼喊捉贼起来。 陈玄烈已然看破他的色厉内荏,咬人的狗不叫,叫声大的狗往往不咬人,他这么挺着,不过是以势压人,想要忠武军屈服而已。 但陈玄烈这种场面见得多了,冷笑一声,“谁是乱军,犹未可知,曹节帅之死,尔等难道不给朝廷一个交代么?” 此言一出,河东军的气势顿时低沉下来。 就连朱玫也是神色一变。 朝廷任命的河东节度使在河东莫名其妙的死了,这事做的太不讲究了,也太心急了。 见对方士气为之夺,陈玄烈忽然喝道:“众将士听令,我等受朝廷诏令前来平叛,若有人敢阻拦,格杀勿论!” “杀、杀、杀!” 李师泰带头大吼起来,宛如平地里的几声惊雷。 其他士卒的情绪也被带了起来,跟着大吼起来。 秦彦晖的蔡州兵立即来了兴致,歇斯底里的大吼:“杀!” 杀气、煞气拔地而起,直冲云霄。 当年安史之乱,河东军也是安禄山麾下的三大藩镇之一,安置了大量胡人,间接造成河东道的胡化,这帮人从头到尾就是一群反贼,与大唐离心离德。 所以他们勾结沙陀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朝廷遂以上党的昭义军与、河北的义武军共同遏制河朔三镇以及代北诸镇。 但昭义军自从刘稹之乱后,也成了一团烂泥,不复李抱真时之强,昭义军的衰落,让忠武步卒取而代之,为天下第一。 当年忠武大将赵犨还参与过平定刘稹之乱。 正是因为昭义军的衰落,河东道逐渐失去控制,才出了这么多幺蛾子。 “进!”陈玄烈大手一挥,两军争雄,绝对不能后退,否则就被别人骑在头顶上。 而且河东军原本就居心叵测,就像一群野狗,你强横的时候,它们不一定敢动,但一旦你软弱,它们一定会扑上来。 轰、轰、轰…… 忠武军的脚步狠狠砸在青石地面上,刀剑出鞘,长枪竖起,弓弩也上了弦。 朱玫是虚张声势,陈玄烈却早已杀心大起。 这年头身为高贵的牙兵牙将,根本不需要怂。 说实话,陈玄烈若能快刀斩乱麻,一举解决了这些河东刺头,说不定朝廷还会下诏嘉奖。 现实永远都是这么魔幻…… 而且城内巷战、步战,忠武步卒就没怕过谁。 这几十年来,河东军基本没打过什么硬仗,也就敢欺负欺负朝廷派来的节度使。 街面上烟尘顿起,阵阵秋风卷起地上的枯叶,旋即被忠武军踩在脚下。 一面面旌旗随着秋风舒卷。 六十步、四十步、二十步! 蔡州的那帮狠人已经狞笑起来,他们巴不得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好让他们能够尽情的在城中烧杀淫掠。 朱玫脸色涨红,两眼圆瞪,虬须都扎了起来,却始终不敢下令开战。 就在忠武军的长枪要顶上河东军的盾牌时,几名河东军忽然扔下盾牌,四散奔逃。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两军对垒,任何一个胆怯行为都会造成全线的崩溃。 忠武军大步向前,河东军不断裹挟着朱玫后退。 见朱玫迟迟没有下令,越来越多的河东军逃走。 胜负已分。 陈玄烈冷笑一声,贼永远都是贼。 “住手!” 就在此时,街面上数十骑狂奔而来。 “尔等皆为大唐将士,岂能刀兵相向?”几十骑泼辣辣的冲到两军之间,为首一人声色俱厉,看了一眼陈玄烈,战马打了个旋儿,转过头去,狠狠盯着朱玫,挥起马鞭,朝河东军抽下。 河东军纷纷躲闪,不敢反抗。 “足下何人?”陈玄烈不怕别人耍横斗狠,就怕别人讲理…… “吾乃河东军马步都虞候张锴!” 另一年长者道:“吾乃府城都虞候郭昢,此事纯属误会,还望忠武军的兄弟们多多包涵。” 这话说的倒有些人样。 陈玄烈扫了一眼两人,刚才剑拔弩张的时候不来,现在自己占了上风,他们就火急火燎的出现了。 巧合?还是故意为之? 心中杀意并未消退。 这时街面上又响起了整齐的脚步声和盔甲铿锵声。 陈玄烈以为来的是周岌或者秦宗权,没想到还是河东军,约莫千人上下,与朱玫一左一右,钳制己方。 形势已然不利。 都这么长时间了,周岌和秦宗权一个人影都没见到…… 果然都是靠不住的人,关键时候,还不如李师泰顶用。 “来人,将东西抬上来,犒赏忠武军的兄弟们。”郭昢大手一招,当即就有百余甲士抬着酒肉上来。 一股酒香夹杂着肉香徐徐飘来。 忠武老卒不为所动,但蔡州军一个个咽着唾沫,刚才那股烧杀淫掠的狠劲儿顿时消散。 “既然是误会,那就罢了。”陈玄烈挥挥手,忠武老卒收起刀枪弓弩。 蔡州军直接扑向酒肉,仿佛饿死鬼投胎,也不怕酒肉里面下了毒。 陈玄烈望了一眼秦彦晖,他满脸惭愧之色。 “已经为诸位备好营地。”郭昢满脸堆笑,和气的犹如一个邻家老翁。 僵持下去,已经占不到什么便宜了,这一千八百多人不可能控制偌大的晋阳城。 陈玄烈借坡下驴,“有劳郭将军。” “都是为了大唐,何谈有劳无劳?此事就此作罢,稍后便来向诸位赔罪。” 郭昢身为都虞候,没有丝毫架子。 “不敢不敢……”陈玄烈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