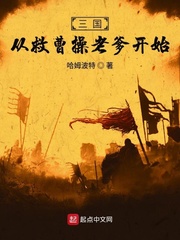钥匙,我当然是自觉又主动的配好了。 只不过是在犹豫,要不要给的问题。 “怎么?几天不见,”我还在犹豫,姜北笙勾一勾嘴角,一抹讥笑像倒挂金钩一样,挂在眉眼醒目之处:“连自己丈夫都不认识了吗?伍小柒,你是老人痴呆还是智商倒退了?” 最后一句话,他用足七分力气,震得我浑身一颤。 这一颤,正好把我的犹豫,颤去了九霄云外:给,给你大爷。我咬牙切齿的暗骂一句。 或许是咬牙的时候,动作稍微夸张了点;又或许是切齿的时候,表现过于嚣张了些。 总而言之,就是我的细微反应,没能逃过姜北笙的魔眼,让他立刻发起第二轮攻击:“看什么看?”边说,还边伸出一根手指,狠狠戳住我的脑门,将我不满的目光逼到与他凶狠的眼神,来了一场短暂的邂逅:“你这是什么眼神?害我在门外站了八个小时,你还有理了?” 这,这个恶毒的家伙,真的是我丈夫? 我头痛的一把握住脑门上这根气势汹汹的手指。 记得有人说过,苦到极致,就是甜。那气到七窍生烟,是不是就要心平气和? 我望了望我对家那张只开了一条缝的门,深深吐了口气,才轻轻问了句:“你吃饭了吗?要不要去巷子云吞店,吃一碗阳春面?” 姜北笙眉眼醒目处那抹倒挂的讥笑,瞬间凝固了,我能感觉到,掌心里的手指微微一动,似是心跳的声音。 当然,也可能是暴风雨前的……预警。 “吃面?你当现在是早上九点?”姜北笙快准狠的将手指抽了回去:“麻烦你少说点蠢话,赶紧把门打开,我很累,伍小柒。” 我绝望的抖了抖嘴角,欲哭无泪的望着那条生命力旺盛的门缝,以及门缝后那双忽明忽暗的眼睛,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张被八卦浸润得连皱纹都充满恶意的脸。 这张脸的主人,叫肖一白,是住我对家的男邻居。 我自打搬来这个小区,就极少在邻居之间走动,更别说单身的男邻居。 我不知道肖一白对我了解多少,但我对他,除了从物管人员口中偶然得到的这个名字外,再无所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跟他的梁子,恰恰就是那一日结下的。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提着几袋垃圾正准备出门,就见物管人员站在肖一白家的门外愁眉苦脸。 “呦,今天在家呀?” 等电梯的时候,物管人员冲我主动打招呼。 听说最近许多住户在恶意躲避物业管理费的上缴,物管中心的负责人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裁掉一半物管人员,留下三个对薪资要求不高的老弱病残。 眼前这个是老,便负责起上门跑腿催费的重活。 Alan就被他催过一次,我刚好碰见了,所以对他印象深刻。 “今天休息。”我礼貌的与他寒暄了一句,他立刻热情的冲了上来:“你对门这户,最近在家吗?” 如果我够聪明,一句不清楚,什么事都没有,可我那天偏偏犯抽:“在呀,怎么不在?早上我下去吃面的时候,正好看见他提了袋包子回来。估计是在家里睡回笼觉,没听到你敲门。” 话刚一说完,肖一白就铁青着脸将门打开了。 从此之后,他就开始对我的一举一动进行窥探。 我站在卫生间的门外,将肖一白的行为历数了一遍:“姜北笙,以后要是再有冤有仇的,都请你不要站在门口发泄。成吗?” 姜北笙站在卫生间的门内,淋浴的水声,远没有大到可以掩盖我们对话的声音:“听左岚说,白慕言把我生病的事告诉过你。对你丈夫表示一下关心,真有这么难吗?” 不是说状态不好吗?怎么又成生病了? “呃,你生病了?”总觉得他这句话里混入了很多杂乱的信息:“什么病?现在,好了吗?”我迷迷糊糊的问道。 “不是什么大病,”掺和着水声的口气,听起来湿漉漉的,有点感伤:“就一小感冒。” 哈?!逗我玩呢? 愧疚就像一坨眼屎,被我一指弹,弹进了卫生间的下水道里。 “小感冒大治疗,如果白慕言告诉我你生病了,我不会真的不近人情,连一个电话都吝啬得不给你打。可事实上,他只说你状态不好,没说别的。” 想了想,还是决定隐去我已经知道他害怕被人抛下的心理障碍。 “当真……”姜北笙欲言又止,过了好一会儿,卫生间里的水声停住了:“再没说别的?”里面的人十分清晰的问道。 他这一问,倒将我问明白了。 “姜北笙,你今天一回来,就跟我闹得水火不容,难道只是为了试探白慕言跟我讲了你多少内情?” “你爱怎么想那是你的事。” 话音刚落,卫生间的门开了,白色的水雾携带着淡淡的薰衣草香味,像群饥不择食的饿狼,从里面往外四窜。 瞬间就将我包围了。 “好饿,”想要逃走,却被姜北笙从后面揪住了衣领:“吃的弄好了吗?” 我反手挣开他,恶狠狠的瞪道:“你的气撒完了,我的气还憋着没放出呢?先回答我的问题,再给你吃的。” “问吧。” 洗完澡后的姜北笙不但面善许多,脾气似乎也变好了。 他裹着白色的浴袍,往厨房走去,我紧紧跟上:“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不回我信息?你知道那对我有多重要吗?工作,声誉,差点就因为你的袖手旁观,全部毁于一旦。” “我那天感冒了,”姜北笙一路走到冒气的电饭煲前,才停下望着我道:“你应该知道,感冒药吃了,容易犯困。我睡着了没听见。” “竟这么巧?” “就有这么巧。”姜北笙轻飘飘的敷衍完我,又指着电饭煲轻飘飘的问:“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了吗?” 怎么有种被他当猴耍的感觉? 可我又不能拿白慕言告诉我的事,把他的谎言揭穿。 左右煎熬后,我垂头丧气的一掌将电饭煲拍开,丢出两个字:“吃吧。” 他眼睛飕飕刮来一阵寒风:“这……这什么东西?能吃吗?” “怎么不能吃?”我指着像浆糊一样瘫在碗底的奶白色稠状物体:“这是花生酱汤圆,”又指了指旁边的暗红色物体:“这是枸杞。要是平常,我还会在里面放几颗红枣,但你来得不巧,红枣昨天吃完后了。” 如果你问我,哪种人最令我讨厌。 我会说,我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人,就像姜北笙这种,只相信汤圆跟枸杞可以煮着吃,坚决不接受蒸着吃的新方法。 彻,我翻了个白眼,没创意的男人,饿死活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