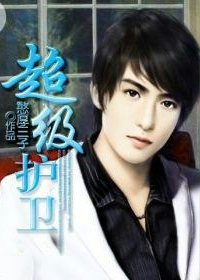铁花道:“想来应是如此,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是他们,才让他们得以施展此技如愿跟上我们,否则、否则,七煞也不会在跟前碍眼。” 杜奇笑道:“这么说来,铁花必定深悉此技咯?” 铁花道:“此技深奥博大,铁花只是略知皮毛,粗通趋避之法而已。” 杜奇道:“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别人以此技的追踪呢?” 铁花道:“这与施术者的水平息息相关,一般来说,水平越低,不但对物标的要求越严格,而且所能追踪的距离也越近,如果施术者的水平一般,只要那物件离开被追踪者的身体,纵使再放回身上,施术者也无法再行追踪;如果施术者的水平较高,一般不易追丢,除非被追踪者有所查觉,将那物件扔掉,施术者方无法可施;如果将此技练到极致,便不须借助任何外物,被追踪者本身便是他最佳的物标,所以,一旦被这样的人缠上,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他的追踪,除非他们不在同一片天下,好在尚未有人将此技练到极致,否则,天下能心安的人恐怕不多矣。” 杜奇又道:“一般初悉此技者,能放飞多远呢?” 铁花道:“此技易学难精,最难的便是炼制物标,以及将物标放在被跟踪者身上而又不让其发觉,一般初学者都能放飞数百里,在数十里之内便能清楚地查知被追踪者的具体位置,公子如此在意此技,是否想了解了解呢?” 杜奇当时听任冬明说此技乃是西域佛宗秘技,想来会者应该不多,便欲以此追查是谁在跟踪他,可此刻听到铁花的解说,方知此技会者甚众,根本无法以此追查那老和尚的来历,不过,杜奇更敢肯定,刚离京城时那老和尚和于飞跃便是凭此技追踪他们的,只不知那老和尚的物标是否便是那自称普渡慈航的尼姑给他的那枚玉佩,如果是,他们没有追上来自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他们没有追上来那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不管如何,看来此技要比用精神感应之法跟踪别人来得方便省事,确有必要了解一下此技的奥妙,于是笑道:“此技甚妙,如果习得此技,老子再也不用担心铁花跑丢了。” 铁花笑道:“既然公子有此想法,铁花又怎么会给公子这个机会呢?” 杜奇笑道:“铁花害怕了吗?” 铁花笑道:“害怕到不至于,不过到是有些担心公子习得此技后去纠缠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铁花既然已知公子之意,自然会处处小心防范。” 杜奇笑道:“既然如此,那你还不赶快说出此技的心法口诀?” 铁花望了望桌上只剩下小半的蜡烛,似有些遗憾地道:“铁花本应立即告知公子此技之法,只是时间不容,请公子去见见小乘教的使者如何?” 杜奇笑道:“铁花欲以此要胁老子吗?” 铁花道:“铁花并无此意,无论公子是否接见小乘教的使者,铁花都不会秘技自珍,更何况此技只是寻常之技。” 杜奇道:“铁花似乎不齿小乘教所为,为何又与小乘教之人如此近乎呢?” 铁花道:“铁花与那小乘教的使者毫无关系,只是他以家师特有的联络之法找上门来,铁花才不得不按他的要求通报公子。” 杜奇道:“如此看来,大乘教似乎已为小乘教所用了呢,不知铁花对此有何打算?” 铁花担忧地道:“我教本就人心不齐,有人被小乘教所用也在预料之中,只是掌教师尊竟然连这样的小事都要为小乘教办理,看来本教的形势比我们想象中要严峻得多,由此可知,掌教师尊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杜奇笑道:“你只担心贵教教主承受的压力,就不担心她的人身安危吗?” 铁花自信地道:“掌教师尊武功盖世,又有一十八位护教高手随身护卫,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打她老人家的主意?所以,她的安危自然用不着我们担心。”说着,铁花起身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屋内顿时光华大盛,原来竟已天明。站在一扇窗户前,铁花接着道:“现在,公子是否马上接见小乘教的使者呢?” 杜奇笑道:“铁花认为我是否该见他呢?” 铁花道:“说实话,铁花本不愿公子与小乘教的使者相见,只因掌教师尊授意,铁花才斗胆代为通报,见与不见全在公子,铁花不敢有丝毫勉强,但为公子及全局想,公子还是应该见见,听听他们有何要求也未尚不可。” 杜奇笑道:“既然铁花要本公子见他,本公子就见见他吧,走,移驾客厅!” 铁花道:“公子如此说,令铁花深感惶恐呢!” 说话之际,杜奇已站起身来,与铁花同时走向房门,闻言笑道:“乖乖铁花不要害怕,让本公子来好好安慰安慰你那受伤的心灵吧!”说着,伸手便向铁花腰上搂去。铁花娇笑一声,早闪身躲开,拉开房门钻了出去。 杜奇见铁花似不愿再与他亲密接触,不由暗感高兴,若能就此杜绝铁花再施美人计未尚不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接见小乘教的使者却是一件烦心之事,杜奇既不愿一人单独见他,又不宜人多,只好叫来任冬明和鲁妙儿相陪。 小乘教的使者是一位年约四旬,面相清朗,期期文文的和尚,他颈上挂着一百零八颗胡桃大小的佛珠串成的链子,左掌随时直竖在胸前,右手掌上套着小一串佛珠,拇指不停地拨动,佛珠一粒接一粒地从他弯曲的食指上滑入掌心,即使是在行进时,他也是眼观鼻,鼻观心,嘴唇不停地微微蠕动,似在虔诚念佛颂经,因而显得宝相庄严,令人无端地从心底升起一股肃穆崇敬之意。 那和尚似毫无重量般轻轻地飘进屋来,将右手中的佛珠挂在大拇指上,双掌合十冲着杜奇深深一礼,淡定地道:“小乘教光明使者见过杜公子。” 杜奇欠身为礼,客气地道:“大师请坐!” 光明使者礼毕后仍用右手拇指不停地拨动着手中那串小佛珠,佛珠一粒接一粒地从他弯曲的的食指上跳过,轻轻地滑入他的手掌,按杜奇之意在客位上坐下,仍然淡定地道:“谢过公子!” 杜奇见那光明使者毫无暴戾恣睢气息,反显得慈眉善目,沉稳端庄,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若是不知他的底细,任谁也想不到他来自声名狼藉令人人敬而远之的小乘教,必定以为他来自某处名山古刹,对此,杜奇不由暗暗称异,笑道:“不知大师光临寒舍有何见教?” 光明使者道:“贫僧乃小乘教光明左使,与光明右使并称为敝教光明使者,在教中的地位仅次于教主地佛上人,贫僧今奉教主地佛上人之命前来拜见公子,主要是想请公子大力援手,助敝教替天行道,拨乱反正,重振纲纪,驱逐外寇,救黎民于水火,还世道于清明,贫僧素闻公子仁德重义,豪情满怀,向以助人为乐为己任,想必不会拒绝贫僧的善意请求吧?” 杜奇虽已猜知小乘教光明使者的来意,但却没想到他会这样直言不讳,更没想到他居然如此振振有词,所言又与素闻大相径庭,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良久才道:“在下幼失怙恃,年幼贪愚又不学无术,实不值大师如此看重。” 光明左使道:“阿弥陀佛!公子不必自谦,向闻公子年少德彰,深受骆马帮上下敬重,只要公子振臂一呼,骆马帮上下无不响应景从,所以,敝教地佛上人才令贫僧致意公子,务请公子为天下人想,率骆马帮全力协助敝教行事。” 杜奇道:“大师谬赞,在下深感惶恐!大师应该知道,在下虽为骆马帮的供奉,但从不插手教内事务,根本无权决断此等大事,即使在下此刻应承大师,日后也难以履行承诺,若大师真有诚意,请与敝教曲教主商榷如何?” 光明左使道:“公子不必妄自菲薄,骆马帮的内情天下皆知,公子在骆马帮的地位无出其右者,即使是曲副帮主也不敢违逆公子之意,而曲副帮主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极少在江湖中露面,当今天下鲜有知其去向者,如此一来,骆马帮的话事人便非公子莫属,贫僧明白,公子之所以如此推搪贫僧,是因为公对敝教有所误会,如果公子得知敝教实情,即使贫僧不曾开口相请,公子也必会鼎力相助敝教替天行道!” 诚如光明左使之言,骆马帮的这些情况天下皆知,由不得杜奇否认,但杜奇却不知光明左使为何如此断言,难道江湖中人真对小乘教有所误会?于是模棱两可地道:“在下孤陋寡闻,尚请大师指教!” 光明左使道:“公子应当知道,敝教创教祖师德宏大师乃一代高僧,因受‘靖难’之累,被迫出走西域,辗转多方,方联同大乘教中有识之士重返中原,欲重匡天下,谁知却功败垂成,又不容于大乘教,不得已隐名埋姓,苦心孤诣创下小乘教,意在替天行道,拯救黎民,现时机已至,敝教自当为民请命。” 杜奇道:“大师是乃得道高僧,当知天道自在人心,黎民渴思清平,小乘教所想只是一厢情愿,根本不顾天下民众疾苦,这哪里是替天行道,拯救黎民?分明是为泄一己之私愤,或是图一己之私利的强词之言。” 光明左使道:“时天道不靖,乌云蔽日,世道黑暗,邪魔猖獗,而道佛相悖,诸子懦弱,外学乱道,以致人心日散,意气泯灭,民不聊生,敝教地佛上人才决定舍生取义,挽狂澜于既倒,救黎民于水火,并非为泄一己之私愤,更非谋求私利,乃是真心为天下民众造福,只是如此一来,也许会令黎民陷于兵火之灾,但长痛不如短痛,只要肃清世道,还惠于民,便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杜奇听得这光明左使之言竟与大乘教主信中所述几乎毫无二致,一时不由疑窦丛生,难道大乘教与小乘教果如江湖传言早已缔结为盟?但铁花为何要矢口否认呢?难道铁花在有意诓骗他?可是,铁花在此事上欺骗他有何益处,又有何用意呢?难道仅仅只是阻止他与小乘教合作?抑或是铁花也不知道大乘教已与小乘教结盟?杜奇百思不得其解,唯有试探着道:“大师乃出家人,为何如此在意世间的名利之争呢?” 光明左使道:“敝教从上到下皆是慈悲为怀的出家人,向以普渡众生为己任,如今舍生取义拯救黎民,实乃造福天下的壮举,并非与世人争名夺利。事成之后,定觅天下英才以承天下,敝教当退隐林泉广播佛法大施善缘。” 杜奇笑道:“大师有如此胸襟和抱负实乃天下之幸,在此非常时期,大师何不与大乘教守望互助呢?” 光明左使道:“大乘教的教宗教义均无可厚非,只是大乘教历代教主懦弱,又毫无节制地扩充,教内人众难免良莠不齐,致使教内有章难施,人心涣散,拉帮结伙各自为政相互倾轧,整个大乘教犹如一盘散沙,人数虽众却毫无力量可言,大乘教中虽有一些人愿力助敝教行事,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杜奇又道:“现下江湖风起云涌,各方势力皆蠢蠢欲动,贵教再推波助澜,天下岂非大乱,到时要收场恐非易事,这与大师之愿岂非背道而驰?” 光明左使道:“正因如此,敝教才难独善其身,到时公子也难置身事外,欲在这动荡之际安身立命,公子最佳的选择便是与敝教合作,对贫僧之请,还望公子三思。” 这一天来,杜奇接连与大乘教的圣女铁花和小乘教光明左使接触交谈,所闻皆与江湖传言大相径庭,而铁花和光明左使之言更是矛盾重重,杜奇现在唯一的期望便是知道事实真相,可是,谁能告诉他事实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