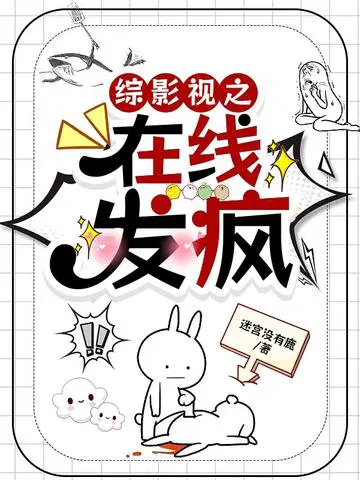晏殊言在台下百无聊赖地看着姑娘们的才艺表演,终于在她的困意来临时,台上的才艺表演才终于落幕。很快便到了竞价的环节,姑娘们鱼贯而入,站在台中。韫彧之瞧着众人俱是跃跃欲试,目光皆黏在台中那淡然的女子身上,恨不得剜了那一双双肆无忌惮的眼睛。他愤怒地一掌拍向桌子,那黄花梨木制成桌子应声而碎。茶盏中的热茶溅在他的臂上,他亦是恍若未觉。 暗影见状,又兀自叹了口气。 台上的姑娘们一个个被买主们带走,到后来,便只余下三两个相貌极佳,气质上乘的女子留在台上。这几个姑娘,便是这雕花楼老鸨重金培养出来的花魁人选。老鸨让晏殊言上前两步,自己则在一旁为看客们介绍:”这是雕花楼的潋滟姑娘,不仅舞艺上乘,相貌自然亦是不俗,那可叫倾城倾国。依旧是按惯例由各位爷出价,价高者得。” 话一出口,无数看客便开口竞价,更有甚者,将手旁的红如焰火的花丢上台,倒与晏殊言这一袭红衣相称。叫价声不绝于耳,似乎大家都志在必得。 “一千两!”楼上的一间房中传来冷冷的叫价声。 大厅寂静了片刻,一千两,于那些达官贵人们而言,也只是些小钱罢了。有人嗤之以鼻,又开始轮番叫价,大厅又喧嚣了起来。 “一千两,黄金。”那声音又冷冷地传了出来。这厢,将才那些个还壮志满怀的达官贵人们都噤了声。一千两银子,倒还能说得过去,可这一千两黄金,用来买一介青楼女子,倒还是令人有些不舍了。一时之间,大厅中的人们皆抬眼打量着幽兰筑,欲知晓能如此大手笔的人是何来头。 晏殊言低垂着头,她无须抬头便能知晓出声之人乃韫彧之最为器重的暗卫,暗影。 老鸨闻言,自是喜上眉梢。这潋滟虽有些才艺,相貌亦算上乘,但她素来清冷,不如其他姑娘那般讨客人的欢心,她倒不曾料到她今日竟能如此大出风头,倒令她的脸上光彩极了。老鸨对这价格虽是满意至极,倒还是希望有人能抬价,与韫彧之争上一番。这潋滟,倒是一棵摇钱树!思及此,老鸨一脸喜色地望着台中那清冷而又浓烈的身影。 台下一片寂静,众人皆是不愿再出声喊价了。 “可还有人愿出价,若是无人,这潋滟姑娘便归这位爷了。”老鸨笑着道。 晏殊言兀自叹了口气,她终究还是逃不出韫彧之的手掌心,试问,这雕花楼的在座之人,还能找出几个比韫彧之更位高权重之人? “黄金两千两。”碧落居中亦有人出声道。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厅一改此前的寂静,又喧嚣了起来。看客们交头接耳片刻,这才知晓,将才出声喊价之人,正是城主洛千城的随身侍卫。 众人皆是敛声屏气,不敢出言,生怕惹了这位骄纵的爷。这洛千城深得东垣女帝的宠信,且与太子殿下素来深厚,即便日后他无法继承皇位,登基为帝,这身份何等尊贵,亦不比皇帝低多少。 晏殊言听闻看客们将才的议论,眼睛顿时添了一丝光彩,转头望向碧落居。将才台下的看客们议论纷纷,”洛千城”这个名字,她自然是听见的。洛千城不仅是”三公子”之一,在这东垣国,也算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他的传奇,不仅因他的皇子身份,更因他自身的能力。凉城乃东垣与南韫的交界之处,背倚龙苍山,倒也不易攻下。然而,几年前的凉城,却不是如今这般繁华模样。当年,洛千城主动向女帝请旨来此,将凉城这一片流寇之地,打造成为东垣国中仅次于京都的繁华之地。若是借洛千城之手,自己逃离韫彧之,倒也多了几分胜算。再仔细思索,她的心倒是极为平静,笑意盈盈地望着洛千城的所在。她知晓,自洛千城的侍卫叫价的那一刻,韫彧之定然带不走她。 “五千金!”暗影又出声道,又将那一众看客给惊呆了去。 “一万金。”这次叫价的不是洛千城的随行侍卫,而是洛千城本人。细听之下,晏殊言便能听出他语带笑意。 韫彧之脸色沉了几分,这出价之人,定是有意与他相争,不管自己如何出价,此人亦会跟价。他站起身,正欲发难,暗影行至他身边,低声道:”主子,暗卫将才打探得知,此人是东垣大皇子洛千城,且这雕花楼,亦是隶属于他名下。不管我们叫价多少,亦是无法从他手上买下晏小姐。且主子此时若是出面,不仅会暴露主子的行踪,于晏小姐而言,亦是大大不利。” 韫彧之心中气急,难怪将才他见晏殊言一脸笑意地望向碧落居,她定然是知晓了洛千城在此处,而自己,定会以大局为重,无法表明身份,带她离开。他大掌一挥,雕花楼的小厮们将将才搬来幽兰筑的紫檀香木桌,便又被他一掌拍碎。 老鸨等了半晌,见无人再喊价,便抬高了声气,道:”既然无人再出价,潋滟姑娘便归城主大人了。”说罢,便有婢子前来,为晏殊言带路。众人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城主大人看中的人,谁若是敢染指,定然是活腻了。 暗影见状,道:”主子现下可有何打算?” 韫彧之未曾回答,只是视线一直追随着那道火红的身影穿过重重人影,在碧落居前站定。暗影有些焦灼,主子对晏小姐情深意重,奈何晏小姐却不领情,主子现下定然难过不已。 半晌,韫彧之才开口道:”在你心中,她是怎样的人?” 暗影沉默了片刻,继而道:”回主子,暗影岂敢对晏小姐予以置评?” “无妨,你只管说便是。” 暗影听韫彧之这番说辞,便开口道:”晏小姐,是像狐狸一般狡猾的女子。” 韫彧之笑道:”确是如此。她向来狡猾,饶是洛千城他亦是非池中之物,我想,他定会在她手上受挫,是以,我倒也无须再担心她的安危。” “既然如此,主子接下来有何计划?” “回南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