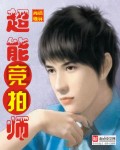那个人影提着剑,穿过了夜色,出现在了明合坊中。 两旁有灯笼的光照亮了来人的脸庞。 是寒蝉。 刘春风沉默了下来。 而叶寒钟的唇边则是微不可察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寒蝉提着剑,踏入了那些还未完全被破开的冥河之国。 一身衣裳破破烂烂,应该是从那些剑气里走出来的。 连怀里装着两万贯的包袱,都被斩破了一些,看得出来,应该是掉了不少钱。 寒蝉一面咳嗽着,一面站在了冥河岸畔,向着叶寒钟那边走去。 “剑渊的赴死剑诀,确实厉害。” 寒蝉轻声说道。 一旁的叶寒钟大概也是好奇寒蝉遇见了怎样的一个人,转过头来,看着一身剑意萎靡的寒蝉。 “出鞘收剑之间,剑势便会不断攀升。” “而一次次赴死之间,更是另一种意味的出鞘。” 寒蝉远远地看着随着星痕游走在冥河之上的刘春风,又低下头来,不住的咳着血。 叶寒钟看着身旁这般凄惨的寒蝉,倒是皱了皱眉,说道:“你差点输给了他?” 寒蝉站直了身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道:“那倒没有。” 这个模样凄惨的剑修,很是淡然地说道:“虽然我的左腹被他捅了一个洞......” 寒蝉如同展示伤口一般,将自己的剑放在了一旁。 掀起了自己的那身衣裳。 叶寒钟的目光下意识地跟了过去。 只是下一刻,叶寒钟的神色便变了。 衣裳之下,自然没有什么左腹破洞。 而是藏着另一柄剑。 那柄剑被寒蝉快速地拔了出来,一剑便刺向了一旁的叶寒钟。 好在叶寒钟及时反应了过来,那一剑虽然得手刺入了胸口,但却在那一刹那的侧身之中,偏了许多。 寒蝉一剑得手,便带着自己的剑向后退去。 果然受了一剑的叶寒钟,在反应过来之后,却是径直一剑刺向了寒蝉。 寒蝉横剑身前,堪堪拦住了那一剑,却也是被剑意击退而去,落在了巫河之中。 只不过叶寒钟收手看着自己心口那一剑,大约也是明白再留下也未必能够杀死刘春风,神色漠然地将那柄剑拔了出来,远远地向着刘春风抛了过去。 带着凛然剑意的一剑,在空中便转向而去。落在了另一个不知何时坐在了巷口的年轻人手中,年轻人身前竖着一个剑鞘,那柄剑乍一落入手中,便被收入鞘中。 剑势再起。 只是叶寒钟已经化作剑光,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巫鬼道之人在剑渊剑修的突袭之下,狼狈而去。 那些冥河渐渐散去。 刘春风重新回到了风雪之中,看了一眼一旁在那里吐着血却仍然在比着耶的寒蝉,很是不解地看向了街头的齐敬渊。 齐敬渊轻声说道:“这是我们欠他两万贯的意思。” 寒蝉很是满意地点点头,丢了剑,昏死过去。 他与叶寒钟的那句没说完的话其实是——但是我输了。 他是实打实的输了。 只不过齐敬渊并没有杀了他。 就像最开始说的那样,剑修是要讲道理的。 寒蝉没有被什么大义感动,只是道理没讲赢而已。 刘春风挑了挑眉,只是却也没有说什么。 有老人在那扇打开的门口等了许久,终于在一切故事结束了之后,将一些东西递了过来。 刘春风神色疲惫地向着老人点了点头,说了声多谢,而后将那些东西交给了走过来的齐敬渊。 又走到一旁,扛起了地上昏死过去的寒蝉,穿过了那些在处理着后事的剑渊剑修,向着明合坊外走去。 ...... 悬薜院中。 两个小少年在小居室门口烤着炉火,很是忐忑不安地握着手里的剑,警惕地盯着那扇剑院大门。 先前寒蝉离开的时候,帮二人点燃了炉子,还嘱咐了他们,今晚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去开门,就在这里烤火,什么都不要听,也什么都不要去看。 二人本来以为寒蝉是开玩笑吓唬他们的,是以尽管寒蝉说得很是严肃,但是二人起初都没有在意。 直到他们听见了一些窸窣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院外走过去。 而后整个书院之中,没过多久,就开始燃起了古怪的火光。 在那些如幕如屏的雪色之中,看起来很是明亮。 两个小少年正打算穿过剑坪,跑到院门口去看看,只是才始在炉边站起身来,便听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了门上。 两个小少年至此才终于相信了寒蝉的话,于是在角落里翻出来了自己领来的剑,抱在怀里,靠在一起,正对着那扇大门,很是紧张的看着。 外面似乎有着一种无声的骚乱。 时有剑光飞梭在雪夜里,也有一些道术或是巫术的痕迹。 但是偏偏安静得很,除了一些脚步声,一些坠落声。 小少年甚至依旧能够听得到那种雪落的簌簌声与身前炉子里的柴火偶尔的爆裂声。 只是远远的看着那些夜色里的雪色,总觉得他们无比鲜艳。 也很是深沉。 赵高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联想的原因。 而一旁的宁静则是抱着剑紧紧地盯着那扇门,很像一些话本里,一个沉默的冷静的主角。 这样的夜雪便一直持续着。 赵高兴有些忐忑不安地捅着靠着一起的宁静。 “他们应该不会打开门跑进来把我们都杀了吧。” 宁静缓缓摇着头。 “不知道。” 两个小少年的声音很小,便在炉边交谈着。 “今年书院是不是要出什么事啊,要不我们明年再来吧。等外面没动静了,就偷偷跑出去。” 赵高兴一面静静地抱着剑,一面很是不安地说道。 宁静则是摇着头,也没有说话。 赵高兴唉声叹气地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不知道寒蝉去哪里了,也不知道齐先生去哪里了。 初来乍到,什么也不知道,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剑院里待着。 一直到夜深的时候,外面似乎终于没动静了。 但是两个小少年也没有敢去看看,只是缩在炉边带着困意打着哈欠。 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那扇门被推了开来。 两个小少年很是警惕地看着那个走进来的年轻人。 年轻人身上扛着看起来很是凄惨的寒蝉,穿过了院坪走来。 两个小少年锵地一声就拔出剑来,双手抖个不停。 “你是谁?你把寒蝉大哥怎么了?你不要过来啊!” 年轻人在剑坪里停了少许,正想说自己便是齐先生,只是说了一半就改了口。 “我是齐先生.....的儿子,他有事回老家了,明天起,就由我来教你们。” 两个小少年狐疑地看着那张和齐先生确实很像的脸庞,犹豫了少许,而后把剑收了起来。 “寒蝉大哥怎么了?” “哦,没什么,想钱想得昏死过去了。” ...... 那样一个故事在夜色里很是漫长。 所以柳三月今晚清醒的时间大概也是极为漫长的。 一直到故事落幕,一切的东西都藏在了黑夜里,等到第二日人们醒来的时候,大约也只能够看见一些埋在雪里的宁静。 瑶姬与柳三月安静地走在人间长街上。 “神女大人会想要见一见那个叫做刘春风的道人吗?” 瑶姬平静地说道:“见他做什么?” “他正在与您作对不是吗?” 瑶姬安静地走在雪里。 “人间与我作对的又何止一个刘春风?” “但人间被格外照顾的,却也只有我柳三月。” 柳三月很是平静地说道。 “生生死死来来回回,我不知道神女大人要看多久,才会承认有些东西,本就是错误的。” 瑶姬只是平静地松开了手里的铁索,向着皇宫方向走去。 “有些东西,现在说,尚且为时尚早。” 不远处便是那条长河。 柳三月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瑶姬远去的背影,在雪色之中,有双碎花小袜子若隐若现。 “所以神女大人要我看什么?” “看看世人们的无用之功,一如你的挣扎一样。” 柳三月没有再说什么,转过身去,安静地穿过了那些雪色石桥,将铁索重新锁在了桥下,而后安静地在那里坐了下来。 有个身影便在不远处看着。 是叶寒钟。 这个黑袍剑修胸口有些血色,只是他并没有在意,抱剑在那里看了许久,而后转身离开了这里。 云竹生的无用之功自然已经证明了一些东西。 这个青天道的弟子,已经变成了人间不可左右的存在。 ...... 夜色里有一个身穿巫袍的人正在带着一身狼藉向着假都之外而去。 寒蝉的那一剑他自然看见了。 在寒蝉出现在巷子里的那一刻,他还曾感叹过,这三万贯确实很值。 只是没有想到,寒蝉的倒戈一击,反倒成为了压倒巫鬼道谋划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当他看见了那一剑的时候,便离开了那里。 他要离开黄粱,前去流云剑宗。 用那枚铜钱,控诉寒蝉的所为。 只是没有走出多远。 他便在假都某条街头看见了一个带着剑而来的人。 那个大巫看见叶寒钟出现,正要上去质问一些什么,只是话还没有说出来,自己的头便飞了出去。 而后飞在雪夜里的头便看见叶寒钟弯下腰来,从他身上摸出了那枚铜钱,放进了怀里,而后平静地转身离开。 作为一个剑宗门下的杀手,自然或多或少,都得到过投诉。 但是叶寒钟从来没有。 今日之事虽然是寒蝉接的单子。 但是终究他叶寒钟也收了钱。 ...... 刘春风便安静地坐在春风院的院子里。 书院的故事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二人回来的时候,都还没有结束。 只是当刘春风与齐敬渊二人没有死在明合坊的时候,这里的故事便可以结束了。 刘春风也没有再去看那些东西,只是坐回了自己的小院子,点起了炉火,气色有些萎靡地坐在那里烤着火。 只是今日并没有周在水来给他送一碗面吃。 因为那个剑修已经死在了院中内乱之中。 是青牛院的人杀了他。 刘春风路过那里的时候,正好看见了那一幕,什么也没有说。 当寒蝉通过周在水之手走入悬薜院的时候。 有些东西便不难猜了。 正如方知秋在谣风所想的那样。 不是所有的巫鬼院之人都会选择背叛人间。 但也不是所有青牛院的人,都会忠于世人。 刘春风也没有心思再去找一找周在水的背后是什么。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在院里有很多。 所以才叫内乱。 在他刘春风露出破绽之前,没有人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只不过刘春风大概也没有想到,破绽真的便差点成为了故事的结局。 寒蝉引来了叶寒钟。 那样一个人,刘春风也好,齐敬渊也好,自然不会是对手。 只不过叶寒钟是寒蝉引来的,也是寒蝉送走的。 刘春风一面咳嗽着,一面烤着火,倒是有些想不明白寒蝉在想什么。 但是这样的事情,显然已经无关紧要了。 刘春风咳嗽了一阵,终于觉得舒服了一些。 虽然道人道韵入体的时候骨头硬,但是毕竟那是硬接的数剑。 难免会伤到一些神海。 从院子里捧了一捧雪塞进了炉子里,刘春风便回房睡觉去了。 ...... 瑶姬离开了假都街头,在风雪里一路向着皇城而去。 只不过这一次她并没有去往迎风楼,而是去了那处废弃的楚王宫前。 黄粱的陪帝陛下也在那里。 只不过今日的陪帝,已经换了一身衣裳,是一身黑红二色,看起来很是古老肃穆的帝袍。 那个大肚子看起来很是显眼。 不过谁也没有在意。 瑶姬走上去的时候,陪帝便在那里看着那扇门上的那柄剑。 磨剑崖灵台。 自从在南衣城中被机括之力射到这里,便一直留在了门上。 很是轻巧的剑身之上,倒是落了不少的雪,甚至在漫长的冬日冰雪里,在剑身下方还悬着许多冰柱。 倘若世人见到,大概也不会知道这样一柄雪中之剑,便是曾经磨剑崖的镇崖双剑之一。 瑶姬一步步踩着积雪深厚的古老石阶,向着殿前走去。 “我以为你会在楼上看着人间那场闹剧。” 瑶姬的目光落在了那身衣袍之上,这是宫中去年开始,便在赶制的衣裳。 曾经的楚王之袍。 “第一次做楚王,难免有些紧张,自然看不下去那样的闹剧,而且......” 陪帝转过身来,总是肥肥胖胖的体态,看起来很是臃肿,但是在这样的风雪孤殿之前,神色肃穆而立,总归是多了几分帝王的气势。 “您应该先称呼我为王上。” 您应该先称我为王上,是一句很是古怪的话语。 大概类似于突然坐上了辇车的轿夫,在那里呵斥着——您他妈的慢一些,颠死我了,这样子。 至于王上与陛下,究竟哪个词代表的地位更为尊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取决于国势而非词性。 只是对于黄粱而言,也许王上会比陛下更好。 毕竟黄粱的陛下,两千年来,便一直屈居于槐安的陛下之下。 瑶姬站在雪阶抬头看着上方那个转过身来的陪帝,倒是平静地说道:“是的,王上。” 在曾经的巫鬼神教构架之中,楚王,自然是与神女同样地位的存在。 为巫部灵修大人。 在以整个古楚大地为范畴的巫鬼神教之中,巫字当先,也能够代表一些楚王的地位。 瑶姬走上了殿前,安静地站在那里,长久地看着在岁月里沉寂下去的楚王宫。 “我什么时候可以拔剑?” 虽然先前说了那样一句话,但是陪帝心中自然很清楚自己应该是什么位置的人,哪怕被那身衣袍唤醒了一些身体里沉睡的野....心。 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都只是陪衬而已。 大概人间也不会在意是谁坐上了那个位置。 他们只会沉默的惶恐的不安的或是虔诚的,看着他们的神女大人。 瑶姬平静地说道:“什么时候都可以,明日也可以。” 陪帝静静地看着瑶姬许久。 “明日是悬薜院春考的日子。” 瑶姬并没有去看身旁的胖男人,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 陪帝回头看着人间说道:“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闹剧很是可笑。” “从京兆尹那里取了名册,而后改换九司,来谋取在假都之中的主动权。” 陪帝轻声说道:“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我有时候很不能理解。” “他们为什么都没有问过我,便如此笃定的认为,我会同意他们的那场闹剧?” 瑶姬平静地说道:“说不定明日,他们就会来问你了。” 悬薜院的人会带着一些写好的东西,交由京兆尹入宫呈上来。 瑶姬说着,转身看着陪帝,缓缓说道:“所以你会说好,还是不好?” 陪帝看着瑶姬说道:“神女大人觉得我是要说好,还是不好?” 瑶姬转身向着殿外走去。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当一个向来只会说好的人,突然问自己应该是说好还是说不好的时候。 他便已经决定了说不好了。 如果依旧是像从前一样说好。 那么还需要问什么呢? 陪帝安静地孤立于风雪中。 一个将会说不好的人,会是孤独的。 他要适应这种孤寂的意境。 这个穿了一身黑底红纹帝袍的男人转头看向人间风雪。 正如他所说,那是一场闹剧而已。 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建立在他会说好的基础上的闹剧。 这样的故事,自然没有什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