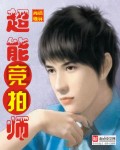白鹿。 这片南方山火之中烧得最凶的土地在少年的伞下最终停下了一切声音。 对于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场死伤无数的战争,绝对不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山月的人们不再来了,云绝镇的人们只是守在了云绝镇。 而在他们的前方,是一个撑着伞等待着白鹿安宁下来的少年。 西门曾经问过程露,有没有想过故事会是这样解决的。 程露没有回答,只是安静地站在镇子里,想着崖上那个被自己用剑指着的少年。 他当然没有想过。 但也许这样确实是当下人间最好的解决办法。 至少在漫长思考过后,这个故事远比两族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之上进行一场血战,使愤恨增生愤恨,要好得多。 山照水说的,自然是有道理的。 所以,便让他们去吧。 看他们是否会在冬天回来。 ...... 秦桑自然不会觉得他们会在冬天回来。 人间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她觉得妖族是坚韧的,坚韧得哪怕面对得只是黑土,只是风雪,都会顽强地生存下去。 所以当那个撑着伞的少年穿过了平原草甸,带着他的师侄过来,在海崖边看着那些将大船从山林里扛出来推到海里去的妖族,并且问了她这样一个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比少年高出不少的青衣女子很是平静地站在一旁说道:“他们不会回来的。” 今年冬天不会,明年冬天也不会。 南岛沉默了很久,而后缓缓问道:“为什么?” 秦桑安静地看着那些入海而去的妖族。 伞下的少年一度想过很多解释。 譬如他们和千年前的不一样的,譬如他们比当年的妖族要更为强盛,更为繁荣,更能开创一片新的妖土。 只是少年没有想过,秦桑最后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 南岛愣在了那里,转头怔怔地看着一片的青衣女子。 秦桑很是平静地说道:“愧疚会使他们长久更为长久,坚韧更为坚韧。” 一直过了许久,南岛才缓缓说道:“我以为他们只有愤怒与惶恐。” “曾经是的。” 秦桑很是淡定。 “只不过我告诉了他们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白鹿之事,是我拱的火。还有更多,总之在那些真相的驱使下,那种愧疚便压过了愤怒。” 秦桑静静地看着风平浪静,万舸待发的那片海,无数大大小小的船在浮浮沉沉,像是许多人间的叶子落到了海里。 “愤怒会让他们时刻想着要回来,而愧疚只会让他们无地自容,远远的,如同赎罪一般地躲在那片高山风雪里,从而安宁长久地生存下去。” 南岛没有说话,一旁抱着剑的小少年眼睛却睁得很大,陆小二觉得自己好像渐渐听不明白了,但是又觉得似乎很有道理。 在漫长的纠结之后,陆小二问了这个看起来很是平静的青衣女子一个问题。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能同流者方能同流,能渡河者方能渡河。”秦桑大概也知道小少年并不能够听得懂这样一句话,所以她有追加了一句。 “世人可以接受叫自家可可爱爱蹦蹦跶跶的小土狗儿子。但是不会允许他家的小土狗娶了他的女儿。” “......” 同流自然是能力也是意愿。 这便是那句话的解释。 秦桑静静地看向南岛。 “人间依旧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存在会出现。也许代表着更替——我们是世人的磨难,世人是我们的前尘。二者可以交错,但是不会同流。在我们的岁月成为古早的历史之后,世人们也许会传颂着他们当年如何战胜了一些强敌,护卫着人间。妖族也许也会惊叹着消亡在历史里的古人类——从娘胎里生出来,世界上真有这么奇怪的人吗?” 南岛听到这里的时候,却是突然明白了许多东西。 看着秦桑缓缓说道:“我终于意识到了.....” 秦桑低头看着伞下的少年。 “你始终是将世人与妖族看做对立的存在。” 秦桑低下头去,笑了笑,只是那短暂的使得这个高挑而冷漠的青衣女子带了一些温暖之意的笑容,又更快地消失在了那张脸上。 “难道不是吗?” “那生死是对立的吗?” 是还是不是。 这永远是一个无法说清的道理。 所以秦桑深深地看着伞下的少年。 南岛很是平静地继续说道:“出发点决定了你看待人间的态度,站在山里看水与站在水中看山,永远都不会得到相同的答案。” 秦桑转过头去,远眺广海缓缓说道:“十六岁的少年很难意识到这些东西。” 南岛同样看向了那片大海。 “是的,我有一个师弟。” 那个师弟叫做乐朝天。 秦桑并没有去问南岛那个师弟是谁,也没有再驳斥南岛的话语,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你能丢了伞看人间吗?” 二月海风吹拂而过。 少年在伞下沉默了下来。 至善至美,至和至同。 一切都是因为不可达方能有一个至字。 理性无法胜任经验之外的一切。 世间万般,都是异流之中根深蒂固的礁石。 “前途未卜,人间不尽。南岛。”秦桑无比平静地说道,“我们只能在已有的路上前行而去。” 那个青衣女子离开了这里,带着青绿的剑,向着南方走去。 在南面的云绝镇里,有一个人间剑宗的师兄正在那里等着她。 两个少年安静地站在崖上看着海,还有海里的一切。 至于楚腰,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向着岭南方向而去了。 那些占据了白鹿一月之久的妖族们,正在浩浩荡荡地向着大海之中而去。 陆小二虽然不是很清楚二人究竟是在说些什么,但是他也能看得出来,自家师叔最终还是没有说赢那个青衣女子。 所以他转头有些担忧地看着自家沉默下来了的师叔。 后者却并没有什么沮丧的情绪,只是抬手拍了拍陆小二的肩膀。 “我们也走吧。” 陆小二一时间有些茫然。 “去哪里?” “东海。” 东海是一片海,也是一座崖。 陆小二怔怔地站在那里。 “白鹿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当初面对着西门的时候,小少年曾经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也应该参与进来这个关于守住人间小镇的故事里来。 结果来来回回,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站了一些屋檐,喝了一些酒,越过了一些山水,吃了一些鱼。 南岛轻声说道:“如果真的等到白鹿的故事真正结束了我们才走,那么西门便要追过来了。” 陆小二深吸了一口气。 妖族之事喧嚣尘上,差点都让他忘记了这个故事了。 两个小少年向着海崖之下走去,一点点地穿过了那些妖族洪流,向着北面而去。 ...... “如何定义为人?” “抛却一切非人的定义。” “只是人间无不同则不存,无同亦不存。” “所以无法定义如何是人。由此而来,无法定义如何是人,便是世人长久以来,无法定义妖的原因。” 南面的山火苗头渐渐低了下去。 只是没有任何一场山火会干脆地止息。 总有某些地方,依旧会存在着一些烬火。 散发着热气,随时都可能会死灰复燃。 世人与妖族渐渐有了一些间隙,若存若亡,若即若离。 卿相与云胡不知便安静地并肩走在南衣城有些安静的长街上。 白鹿的故事自然已经传到了这一边。 卿相对此不置可否。 也没有提及白鹿妖族渡海而去之事,只是与云胡不知在街头讨论着一些没有答案的东西。 谁都知道没有答案的东西,自然很难长久地说下去。 所以二人也只是随口说了几句,便没有继续了。 云胡不知抛去了那些杂乱的心思之后,在南衣河一处桥边停了下来,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当初四人在夜色里闲走的事情。 陈鹤带的头,一路拉了南岛云胡不知还有梅先生。 四人在一切故事未起的春日夜晚,很是轻松地走着。 一直到了这一处桥头。 云胡不知依旧记得当时陈鹤那般开心的模样。 一面笑着一面也有些惆怅。 “陈鹤也不知道哪去了,倒是那个少年,这一次的声音很大,世人大概很快就会知道,有着那样一个少年,带了一伞的风雪,截停了白鹿的战事。” 卿相一脸无所吊谓的模样,拿起酒壶喝着酒。 “谁知道呢?” 云胡不知转头看着卿相,笑着说道:“卿师好像从来都不会提起陈鹤这个人。” 卿相轻哼一声,转过头去。 “谣风有个叫做张三的,我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山月城也有个叫做张三的,不过大概卿相不认识。 云胡不知轻声说道:“我以为这是不一样的。” “有锤子不一样。” 卿相提着酒壶就要给云胡不知来一下。 后者则是轻声笑着抬手拦了一下。 卿相倒是古怪地看着这个当初在河边洗衣服,结果一棒子打人头上了的书生。 “你结丹了?” 云胡不知诚恳地纠正着卿相的说法。 “是结石。” “......” 卿相真的不知道是云胡不知脑子犯抽还是南岛脑子犯抽。 好好的结丹不好吗?非要叫做结石。一听就让人觉得好像腰子不好一样。 重点是云胡不知还觉得这个名字很好。 撰写的那本书上还真就写着——论‘结石’境在成道时的存在可能性及其趋势。 卿相默然无语许久,颇有些咬牙切齿地看着云胡不知。 “你小子以后千万别说是我卿相的学生,我好歹是人间白衣书生,哪怕骂人,都是骂得文采飞扬酣畅淋漓,你他娘的取个结石这样的名字,简直他妈的......” 云胡不知偷偷擦了把汗。 卿相大概没有看过那本书。 因为在末尾,云胡不知很是诚恳地加上了一句感谢卿师如何如何。 一粒结石吞入腹,我命由我不由天。 云胡不知心想这有什么不好听的。 好听得很。 有趣的很。 像卿师这样的老头子,自然不能理解。 二人互相腹诽了许久,倒也正经了起来。 卿相喝了好几口酒平复了一下把自己这个得意学生掐死的想法,而后认真地看着桥上的云胡不知说道:“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变化?” 云胡不知抬起手,南衣风起,有元气在春风里而来,吹得这个书生衣袍纷乱不已。 那些元气落在了书生指尖,又向神海而去。 卿相很是敏锐地察觉到了那些天地元气并非全部落入了神海之中,大部分都是在神海提纯之后,沿着四肢百骸,一路向下而去,最后落在了云胡不知的腹部。在那里隐隐形成了一个颇为凝练的元气奇点。 老酒鬼深吸了一口气,连喝好几口酒,而后看着云胡不知说道:“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给你叫个人来看下。” 云胡不知一脸茫然地看着自家老师,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卿相提着酒壶就向着长街远去而去。 没过多久,便带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过来了。 手里还提着一个褐色的药箱。 卿相很是紧张地看着那个老头子说道:“您帮我看下这小子是不是得了历结病了?” 那个曾经给卿相诊断出酒疸的老大夫神色凝重地观察着云胡不知许久,而后又把了脉,还摸了摸书生消瘦的肚子,最后神色凝重地说道:“多半是的了。” 说着又回头看着卿相,瞪着眼睛说道:“不是说了院长你已经酒疸晚期了吗?怎么还天天喝酒?” 卿相默默地将酒壶藏到了身后。 老大夫这才看回了云胡不知,神色凝重地说道:“不过云胡先生的倒还好,如果院长不放心,可以带他去槐都,槐都那里的大夫可以帮忙给你开刀取出来。” “......” 云胡不知默然无语。 待到大夫留了几方药离开之后,云胡不知这才看向了卿相。 “卿师你是不是故意的?” 卿相一转头,大口的喝着酒。 “你小子不要信口胡说,为师是担心你的身体。” “......” 二人自然不会真的跑去槐都开刀。 修行者自然会像世人一样得病。 只不过像卿相这样的,酒疸不知道几百年了,还不是照样好好的喝着酒。 修行对于人间而言,自然同样是需要继续摸索下去的。 不过听说槐都确实一直在尝试着进行修行者健康监测管理,只不过至今为止,依旧没有什么消息。 大概确实是很难确定的一些事情。 二人站在桥头吹了许久的风。 卿相倒是有些感慨。 “你结丹的速度,确实有些快。” 云胡不知散去了那些汇聚的天地元气,轻声笑着说道:“那是因为这是已经研究了许久的东西,一切水到渠成,自然会快上许多。继续往后,我还有继续研究很久。成道境既然存在这样一个极限解,小道境也许也有。” 卿相挑眉说道:“如果你又解出来了,打算取个什么名字?” 云胡不知想了想,说道:“我已经隐隐有些眉目,只是还有许多关键数值需要数理院的先生帮忙,所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概会叫长生胡芦娃。” 卿相握紧了拳头。 云胡不知连忙躲远了一些,诚恳地说道:“开玩笑的,卿师,不如你来取吧。” 卿相看着云胡不知说道:“为什么会想叫长生葫芦娃?” 云胡不知说道:“因为从已有的一些数值模型来看,也许会形成一个婴儿在胎中的模样.....数据模型过于庞大,一己之力很难算出来,最近南衣城事又多,数理院的先生们也静不下心来,所以我们也不能确定。而且越往后,这样的东西只会越难算。” 卿相沉吟了少许,而后缓缓说道:“既然这样,那就叫元婴吧。至于你说的难算的问题......” 白衣酒鬼抬头看向北面,轻声说道:“到时候我带你去一趟缺一门。” 云胡不知轻声说道:“是了,要说算,自然没人能够比那些终日算着庞大命运之流的道人们更能算。” 卿相只是微微一笑。 “我还不想把他们都累死在那里,世人必须要承认,人力有时而穷。” 云胡不知有些不解地说道:“那我们去做什么?” “去借一些东西。” 卿相说着,很是感慨地说道:“那是缺一门的最为宝贵的东西,卜算子的毕生精血所在。” 云胡不知有些晕晕乎乎。 “卿师究竟在说些什么东西?” 卿相喝着酒,笑呵呵地向着南衣城春日长街走去。 云胡不知跟了上去,对于缺一门这个虽然建观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事迹流出,却能够与人间剑宗这样的地方并列三剑三观的存在,自然无比好奇。 卿相抬头看着那些长街屋檐之上的天空,轻声笑着说道:“不能说,说了他们就会算到了,算到了,可能就不想借了,你要知道,作为一个从当初青天道的故事里走出来的地方,他们对于因果剑与因果二字,向来很是不喜欢。” 当年丛刃那一剑,震惊了整个人间。 本该灿烂过一生的白风雨,虽然没有死,但却也就此沉默下来。 这也就导致了自此之后,世人都不敢看见没有剑的丛刃。 只是那一剑的影响自然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