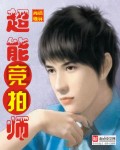这场绵延了整个假都新年的风雪在某一刻停了。 刘春风颓然地坐在高山上的某一刻,忽然便感受到了春风拂面。 于是他抬头看向人间。 人间不知何时已经变了模样。 雪霁云开。 万般明澈。 原本应该是阴沉的天色,此时却像极了一片风平浪静的大湖,无数条冥河像是从人间倒映至天穹的一般。 好像从来没有过那场雪一样。 那片神光之柱的烈火之侧,那些祭舞已经进行到了最为热烈的部分,巫舞之女们在热烈之中欣然起舞,颂唱着,迎接着那样一个代表一切开端的至高神鬼。 一身神光辉耀,几乎不可直视的瑶姬,肃穆清冷地立于诸般光景的中央。 拂袖之间,冥河纤舞,云雨以降,光尘倾洒。 遗世而独立。 也许正是这个人间最后一个神鬼的写照。 只是清冷的不可直视不可侵犯的巫山神女脚下,却穿了一双碎花小袜子与一对干干净净的小布鞋。 这也许是违和的。 也许是融洽的。 赤足的神女翩然立于人间山河之上,以神光为舞袖,以春风为轻纱,也许会更令世人痴迷。 那是一种来自于不可直视的神辉之中偷窥赤足的,世人所能仅有的罪恶的沉湎的亵渎感。 然而穿着碎花小袜子的神女,也许更能让世人觉得亲近。 只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观感,才是人神相亲的开始? 刘春风并不能明白。 只是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一切已成定局。 太一春祭快要结束了。 人间风雪也结束了。 神女以不可侵犯亵渎的威严带来风雪,是为人神之间的警示。 又以春祭将万般柔和的春风春光洒落人间,是为神人相亲的柔化。 刘春风转头看向假都,看向人间。 一切都在不断地消融着,春天是一个一听到就会觉得滴滴答答的化雪之声不会停止的名词。 他所见到的也是这样。 那些神辉所及之处,一切都在消融着,沉积了一整个冬天的厚厚冰雪,如同于一轮炽日近在咫尺一般,无比迅速地融化着。 同时也将那种震撼与折服,像是笑意青青的春草一般,爬满了所有站在街头的世人脸上。 润物细无声。 刘春风缩手立于山巅,远眺着人间,像极了一个面对着一切倏然的变化,不知所措的老头子。 尽管他只是一个三十岁的道人,甚至依旧可以用青年来形容。 那些祭祀的尾声还在持续着。 而瑶姬却已经离开了主位,任由那些冥河与那些神光牵连着缠绕着,像是一片神国的壁垒一般,高悬于春风之川上端。 一身神辉渐渐敛去,却没有再像过往一般,毫无展现,而是化作了无数春露一般的东西,悬浮在身周。 刘春风看着向自己缓缓而来的神女,总觉得自己像是在看着一片古老的青翠的山林,林间繁花遍地,花蕊中有春风吹着一滴圆滚滚的晶莹的露珠正在微微颤动着。 于是这个假都玉山垂下头去,看着那双停在了自己面前的碎花小袜子,也滴落了那样一滴泪水。 “下民刘春风,见过神女大人。” 是下民了。 自今日起。 人间都是下民了。 有春风吹过这片冰雪消融的山岭。 就像神女瑶姬的声音一般。 “该回京去见我们的王上了。” 神女身影带着春意的芬芳,自刘春风身旁擦了过去。 那名叫做子渊的书生没有跟上去,只是握着未写完的书卷背着手,不无缅怀地看着这样的人间。 其实与当年也是不同的。 子渊这样想着。 当年是热烈的,像是一山春花一样繁盛的人间。 刘春风也回过头,看了一眼那片春祭之地。 唇角又有一些血色涌现。 刘春风在这场春风里,好像大病了一场。 再也得意不起来了。 只是面色苍白而憔悴地,跟上了神女的脚步。 ...... 当那场春风在战斗的余韵里,覆盖过整片人间的时候,寒蝉便不再面对着那条风雪长阶。 他从迅速消融的雪地之中,拔出了自己的剑,转过身去,看着那座古老的楚王殿。 柳三月已经站了起来,站在了另外一边。 那些岁月里布满了风雪的砖墙,正在湿漉漉地滴着水。 第一抹新绿的青苔在神光之下从雪色里爬了出来,继而如同被快速催化的一切生命一般,那样的青色,很快变成了更为粗壮的藤蔓,虬曲着,蛇行着,攀援着每一处岁月里尘封数千年的古老殿墙。 有鲜红的雪白的明黄的深紫的花在青绿的藤蔓与漆黑的瓦檐上盛放着。 天穹之上的神光洒落。 这样的一处古老的宫殿,正在重新焕发着生机与威严。 在一切细微汇聚而成的浩瀚的声音里,褪去了万般沉寂,凌然立于南方京都之中。 而寒蝉立于殿前,如同立于这片人间之巅。 寒蝉越过了那柄灵台之剑,停在了楚王殿前,抬手按在了那扇深沉厚重而古老的有着烈火与神鬼图腾的大门上。 一如当初站在议事殿前一般。 但是那时他没有推开那扇门。 而这一刻。 寒蝉闭上了眼,手上青筋显露。 在一声浩瀚却也沧桑沉闷的声音里,那样的一扇大门被一点点的推开来。 春风带着大风历一千零四年的气息自那些门缝里吹了进去,又带着一种古老的气息翻涌而回。 推门的声音是沉重的。 然而好像整个人间都听见了一般。 最后一道剑光带走了最后一个没有来得及离开的南楚巫的头颅,高高地抛向天穹,洒落着鲜红的血液。 最后一抹积雪融化,在檐下像雨水一样滴落着。有人推开了那扇寻常的吱呀吱呀的人间之门,探出头,小心翼翼地看着街头的动静,而后怔怔地站在了那里,看着春光扑面而来。 最后一抔土被洒向那个在皇宫角落里新掘出的坟墓,埋葬了黄粱两千年的传承。 而最后一阵古老的尘风吹向了寒蝉,吹开了他的双眼,将殿中一切,被尘封的数千年的,古老的神秘的岁月,玉体横陈地展露在了他的面前。 寒蝉沉默地站在那里。 身后有脚步声传来,回过头去。 是已经回到京都的,穿着碎花袜子,带着神辉春风款款而来的神女瑶姬。 “王上为何踌躇不前?” ....... 假都冰雪消融的长街之上,两位老大人正站在那里,远眺着如同层层春山的宫中大殿。 世人往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因为那里是沉寂的,毫无声音的。 但是今时自然不同往日。 奉常大人静静地看着那里,轻声说道:“听说当今王上,与当年的先帝陛下很像。” 京兆尹大人笑着说道:“奉常大人也是入过宫的人,宫中有没有先帝的画像,难道大人不清楚吗?” 皇宫之中,自然没有当初先帝的画像。 名为阑的女帝,毁去了关于当年之事的所有痕迹。 尽管她当年是真的,被世人所熟知的与先帝极为相似之人。 但有些东西,既然要成为悬案,便要彻底一些。 奉常大人转头看着京兆尹说道:“所以那大概就是京兆尹大人与悬薜院开的一个玩笑。” 京兆尹却是摇了摇头,说道:“那不是玩笑。” 奉常大人抱着暖炉沉吟了少许,说道:“是的,确实不应该是个玩笑。是真是假也好,终究需要给世人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否则天天人人皆有此心,自然乱了伦理纲常。” 京兆尹转身向着明合坊走去,轻声说道:“我没有奉常大人想得那么多,我只是不想悬薜院自己都不相信这些东西。” 奉常大人沉默了少许,看着那些血色未褪的宫殿,轻声说道:“看来他们真的信了。” 京兆尹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春风渐盛,晨光欲来的长街里,缓缓走远而去。 奉常大人回头看着他的身影许久。 “京兆尹大人去哪里?” 京兆尹只是且行且停地看着京都长街。 “回乡去了。” 古楚自然没有京兆尹。 身为拥立寒蝉入京的老大人,也许会有别的官职,只是大概也不想参与进这些事情里来了。 京兆尹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参与进来。 是悬薜院在年前,送了一车年货,将他卷了进来。 这个故事既然讲完了,京兆尹大人自然便要想着好好休息了。 至于将会是谁来接替京兆尹的职责,那是人间新的王上的事。 ...... 方知秋没有入宫。 身为一个世俗的风物院先生的他,在院里某个修行者的帮助下,爬上了人间高楼,远眺着宫中那些被春风化雪的水流,冲刷着的狼藉的宫道。 一个名叫齐近渊而非齐敬渊的少年剑修满身血色地走出宫去,抬头看见了方知秋的所在,于是也攀上了那处高楼屋脊。 “所以悬薜院算是赢了,还是输了?” 齐近渊看着方知秋说道。 方知秋缓缓摇了摇头,说道:“黄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悬薜院有什么输赢呢?” 他们自然争到了帝位,将代表着悬薜院的寒蝉送到了那个上承神女下接人间的位置。 只是悬薜院所想要的,自然不止是这样。 他们也许成功的在复楚的人间之中,谋得了关于世人的话语权。 但是依旧远远不够。 而且随着这场宛如神迹一般的春祭的开始,悬薜院所做的一切,似乎也变得微茫起来。 一切好像仍自在起点。 然而方知秋明白,那只是因为终点过于渺远了而已。 “世人会在神光的辉耀之下,慢慢积蓄属于人间的力量。”方知秋轻声说道。“过往的他们是混沌的,横流的,不知所措的。而悬薜院所争取到的一些东西,可以给他们一个方向,一种希望。” 方知秋抬起头,看着天穹,人间夜色完全沦陷于那些冥河异象与神辉之中,缓缓说道。 “绝望当然是有的,我相信不止是我,也是你,还有刘春风,与一切在血与火之中,蓦然抬头,看见那些神鬼之威的世人。” 方知秋低下头来,微微笑道。 “但绝望愈发令人觉得仓皇恐惧,自其中迸发而出的希望便会越发具有一种坚韧的力量。” “疾风知劲草。我希望世人如那风中劲草,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这样的话,哪怕知秋逢雪,也不需向谁祈祷。” 齐近渊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身旁面对着这般结局依旧怀抱希望的方知秋,轻声说道:“我以为你一直会是坐在谣风小镇,喝着冷酒的模样。” 方知秋轻声说道:“正是因为喝了冷酒,才知道人间需要怎样的热流。” “你是吗?” 齐近渊看着他问道。 方知秋笑着一层层跳下楼去。 “我当然....不是的。” 方知秋落在了人间长街上。 “我只是一个悬薜院风物院的先生而已。此次来京都,大概也是存了一些见见人间风物的心思。” 方知秋当然不止是见见人间风物。 寒蝉入京为帝,便是出自他手。 方知秋站在长街上叉着腰喘着气,毕竟是书生,爬上爬下的,很是费力。 “对了。” 方知秋抬头看向高楼之上的齐近渊。 “你们剑渊,到底是因为什么愿意搅进这些事情里来?” 剑渊虽然在这场故事里,冒头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却也是一大不可忽视的力量。 齐近渊抬起头,看向东面丛冉方向,平静地说道:“天下神鬼,无非伪神。” 人间不接受的神鬼的理由有很多。 但唯独剑渊之人是以伪神为辞。 只是方知秋什么也没有说。 剑渊这是一个极其古怪的地方。 人间一切剑意,到了那里,都会被压制下去。 这也是剑渊亦有葬剑之渊名字的由来。 当年青衣离开人间之前,都是亲自去其中看过。 然而无人知道那里面究竟有什么。 ...... 楚王殿中自然只有古老这样的名词,譬如那些陈设在殿左的一排排落满了灰尘的编钟。 那是当年古楚时候,楚王宴臣的礼乐之器。 还有诸多形制古老的用具。 一切都尘封在了其间。 然而这并不是寒蝉停下来的缘由。 这个一身血色的帝王,只是静静地看着瑶姬,缓缓说道:“因为孤有一事不解。” 瑶姬立于殿前,声音温和地说道:“王上何事不解?” 寒蝉看向春风人间,沉声说道:“神、王之事何解?” 瑶姬平静地说道:“王权神授,分而治之,各行其是而已。” 一如方知秋他们所想的一样。 这个重临人间的神女,不会在意是谁做了楚王。 巫鬼神教早已崩塌在岁月长河之中。 楚王是寒蝉,还是阑离,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寒蝉执剑立于殿前,沉声说道:“分而治之?” 瑶姬也许意识到了什么,然而依旧没有在意,只是平静地说道:“分而治之。” 寒蝉拄剑而立,春风里雪色衣袍凛凛。 “那么神女大人,您越界了。” 此话一出,无论是一旁的柳三月,还是立于黑色的湿润的长阶之上的齐敬渊,都是下意识地变了一些神色。 寒蝉送剑入鞘,转身向着大殿之中而去。 “此是人间之都,神都在东。神女以降人间,自是人间盛事,当颂舞而迎之,然而神女大人不请自来,人间怠慢迎之,是为陷人间于无礼之境。” 寒蝉停在殿中,重新转回身,神色凝重地看着瑶姬说道:“此事,孤无法向人间交代。” 楚王殿内外一片沉寂。 然而瑶姬并无愠意,只是轻声笑着,看着寒蝉说道:“灵修大人以为如何?” 寒蝉平静地说道:“明日孤诏令人间,神女垂怜而来,天下患生患死患寡离苦忧之人,可入京都,祈受神女垂降之福,如此天下既无怨言,亦无惶恐,神女大人亦可得天下民心爱戴,如何?” 瑶姬收敛了笑意,静静地看着寒蝉。 柳三月在一旁挑了挑眉,却也是明白了寒蝉的意思。 天降异象,便想要人间,这是不可能的事。 神女大人既然想要人间,便要拿出自己的诚意来。 一如先前所说,人神分治,那么这便是寒蝉的人间。 世人如何,理应由寒蝉来管,而非瑶姬。 瑶姬平静地说道:“灵修大人虽然悟性惊人,但是却忽略了一件事。神鬼垂佑与垂怜,是两回事,前者为本职,后者为妄行。而神鬼垂怜,需要至上之诚意。楚人好巫鬼,同样好淫祀。垂怜生死苦忧,未尝不是权柄所在,然而天下没有凭空而来之礼,以小生死换大生死,才是垂怜之意。世人不祭而得,是大乱之始。” 瑶姬转头看向人间,缓缓说道:“灵修大人倘若真要神鬼垂怜,还请奉上人间的诚意。” 寒蝉轻声笑着,说道:“原来如此,是寡人失礼了,那不如换一件事吧。” 瑶姬平静地说道:“灵修大人请讲。” 寒蝉看向殿外的柳三月,缓缓说道:“寡人孤离,难免思念故土,不如留一故人给寡人如何?” 醉翁之意也许不在酒。 在乎柳三月。 寒蝉大概自己都没有想过,在这个故事的尾声,他会这样的肆意无忌。 都像东皇太一出剑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柳三月怔怔地站在那里。 “孤不相信,神鬼之权柄,留不下一个世人。” 瑶姬眸光平静地看向一旁的柳三月。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