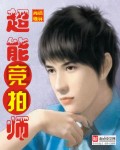秋水。 穿过了那片山下林子,前方便是一条极为险峻的山道,两旁黝黑的山岩向上而去,只留下中间极为狭小的一些空隙,暮色浮在天穹之上,又洒落向人间,远处有一条滔滔大河自极高之处浩荡落下,河水击打在高山黑土山石之上,层层向下坠落而去,将来自两千丈的磅礴的坠落之力溅成霞光之后,而后终于化作了那条承载暮色而去的秋水。 冥河绝大多数时候,其实都在世人头上。 所以黄粱有些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很是古老的说法。 不叫归冥。 而是归天。 先前那个曾经在秋水河畔见过秋水的人间大妖,便在那些黝黑的山道上走着,两旁伞树身承华光,倒是有些五彩斑斓的黑。 倘若按照人世的境界而言,这个大妖应该是小道境左右。 算不上低,但也不会太高。 自然是这样的,倘若那些依旧以幽黄山脉为祖地的妖族们,过于强盛,神河也不会千年都不曾理会他们。 虽然同为妖族,但是神河是这片人间的陛下,自然不会允许存在着什么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难得同流的两族之间。 那人一直走了很久,才走出了那条山道,出现在了一处近千丈高处的颇为广阔的山坪之上。 南拓虽然没有雪。 但是幽黄山脉有。 这片不属于人间的高山,在数百丈之后便开始因为高空气温过低,常年覆盖着冰雪。 所以世人看见幽黄山脉是黑色的,也可以看见那些黑色往上,一些融化的乳糖一般覆盖着的雪色。 暮色在这里并没有下方那么浓郁了——在山下的时候,觉得是天穹的色彩照亮了秋水。但站在山上,又好像是人间的色彩涂抹着那些风雪。 山雪是斑驳的,因为伞树是黑色的,也有些黑土顽强地自雪下露了出来,一同构成了这些山间漂浮着一些霞云的斑驳的世界。 山坪里有着许多人间一样的镇落。 向着那些高崖之中四处延伸而去。 这里便是人间少有的,纯粹的妖族汇聚之地。 那人穿过了那些建筑,一直向着深处而去。 深处有山崖。 崖上没有人,只是孤崖风雪,崖下有人。 是一个模样很是寻常的老人,老人没有瘸腿,但是也被叫做了妖主。 因为他是很多年前,曾经目睹过万妖越过秋水而去之人。 当时的他只是小妖,一只留在了枫叶林中小妖,与那些留下来的妖族们一同看着北去的人们。 他没有什么悲伤。 因为秋水之上的高山,确实是他的祖地。 这是人间少有的,真正意义上诞生在幽黄山脉的妖族。 是一株伞树下的某块黑土,后来有了一个很是古怪的名字,叫做却冉,是他自己在人间的书籍上随便找的两个字。妖族的名字大概总有些莫名的陌生感,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传承,无法将自己的姓氏传承下去的原因,于是才会让世人听见的时候,有着这样的感觉。 现在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悲伤,只是安静地在山崖下的一块空地边站着,山崖之下也是山崖,层层叠叠的不止是覆着的风雪,一阶一阶像是广阔的台阶一样的也不止是那些高低不一的崖坪。 同样活了很多年的却冉便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人间秋水,看着秋水人间。 那个人站在了却冉身旁,轻声说道:“崖主不愿见您。” 却冉静静地回过头来,看着那个同样名字古怪的非谷。 “她说了什么?” 大约是人间小道境的非谷轻声说道:“她说除非山上的人下山去.....” 非谷并没有说完,但是却冉自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却冉转回头,安静地看着山下,高山风雪之下,秋水无比渺远,也许就像这里与人间一样。 也许本身就是从人间之外到人间的距离。 “妖族从来都不是一定要活在人间。”却冉说得很是平静。 这个当年只是一只懵懂的小妖的老人,在历经了千年岁月之后,却也是想过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在山里,他们在山下,千年来相安无事,有什么好下山的。”却冉轻声说着。“她秋水离不开故土,我们自然也离不开故土。” 幽黄山脉自然是贫瘠的。 人间的黑土是肥沃的。 但是幽黄山脉的不是。 这片土地如同被焚烧过一般,将那种黑色残留在整座山脉之上,有时候人们都会想着,也许在很久的岁月之前,那时还没有聚落,没有语言,没有文字,这座高山之上曾经起过一场大火,焚烧了一切,包括生灵生长的养料。于是这片横在人间西南的高山之上,除了伞树,再也长不出任何的植株,哪怕是稻子,哪怕是稗子。 只是贫瘠的故土,终究是故土。 再破旧的草庐,也是曾经让自己寄身天地的住所。 非谷沉默下来,没有说什么。 却冉转回了头,看着身旁的那个人。 却冉是山上的妖,但是非谷不是的,他是山脚的妖,就像那些山坪之间的妖族镇落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 因为对着人妖共存心存着怀疑,于是认了却冉做妖主,认了高山做祖地,走上了这座贫瘠的山。 世人都无法真正同流。 妖族自然也是的。 活在人间,与不活在人间,只是两种选择而已。 非谷知道却冉在看自己,但是却没有回过头,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 过了许久,才轻声说道:“妖主想见崖主,应当只是见一见当年的那些岁月吧。” 却冉平静地点点头,说道:“是的。崖主虽然未必能够记得我这样的小妖,但是当年秋水之人,不会有人不认得崖主,千年岁月,当年妖族能够活至今日的,已经没有几人了。妖族虽然寿数悠久,但是并不代表着所有的妖族都能够活得很久远。” 非谷倒是很诚恳地说道:“但我想的与妖主不一样的。” 却冉淡淡地说道:“看得出来。你想在当下人间的乱局之中,借一些崖主的势。” 非谷轻声说道:“是的,人间风声虽然落到黄粱的时候,已经很是零星,但是总归还是有一些,槐安妖族面临乱世,岭南瘸鹿剑宗被人杀尽,世人难免会想到秋水这片土地。只要崖主曾经上过山,当妖族真正面临一些不可摆脱的局面的时候,便会看向这里。” “这样是卑鄙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却也会想起很多的东西。” 却冉静静地看着身旁的大妖,缓缓说道:“比如?” “比如......”非谷看向人间,轻声说道,“世人已经很老了。” 世人已经活在人间很漫长的岁月了,从神鬼时代之前,便已经存在。 所以也许他们真的已经老了,老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人间。 “两千多年前的人间便已经开始修行大道,然而两千年后,他们依旧还走在同样的路上,没有丝毫的长进,世人的寿数,限制了他们继续往前的脚步。” “风朝是一个很好的过渡的时代,神河陛下成功的让妖族在人间开始延续,开始生存。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时代,依旧是由着已经老迈的世人做着主导。” “老旧的东西,该慢慢退出舞台,将肩负着人间向前而去的任务,交给新生的妖族。” 非谷静静地说着,这个只是人间小道境的大妖,却有着颇为宏远的图谋。 “卑劣兴起于平和之中,然而在乱世之时,它可以变为一种很是伟大的东西。” “神河是伟大的,但他的目光是短浅的,我们后来的人要看得更远一些,前代妖主的夙愿,其实还没有完成,我们要为后人做世人,便要做真正的世人,而不只是同流而已。” “人间自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非谷说完了这最后一句话,便安静了下来,转过头,静静地看着身旁的老人。 当非谷看向老人的时候,老人便不再看着他,而是转过了头去。 “我先前只是觉得镇落里有些异常。”却冉轻声说道,“却原来你已经想了这么远。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什么?”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洗过脸了?” 非谷沉默少许,说道:“大人想让我照照镜子?” 却冉轻声笑道:“不然呢?” 非谷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这处风雪之崖。 “妖土十三镇,我已经说服了九镇。” 却冉并不在意这些东西。 没有悲伤,也没有愁苦。 只是安静地看着下方秋水。 冥河在世人头上,同样也在妖族头上。 所有人顺流而来人间,同样也会逆流而去。 ...... 南方秋水之上的故事,对于整个人间而言,自然都是极为遥远的。 世人要操心的事情很多。 站得低的要想着今年过年怎么过。 站得高的要想着神女大人想要做什么。 至于那些幽黄山脉之上,关于人间有过怎样的看法,大概没人在意。 忙碌了一日的京兆尹回到自家府上的时候,便看见院子里多了一些东西,自家夫人带着下人正在那里清点着。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只是一些腊肉年货之类的东西。 然而京兆尹还是很纳闷,谁会想着来给自家府上送东西? 毕竟老大人兢兢业业大半辈子,从来不收礼的事,假都的人应该都清楚得很。 “这是谁送来的?” 京兆尹神色古怪地踱步走了过去,围着那些东西来来回回的翻看着。 他夫人抬起头来,很是愧疚地说道:“悬薜院。” 京兆尹沉默了下来。 过了许久才说道:“你们怎么收了?” “是个青牛院的人,带了把剑——没有带剑鞘,客客气气地把这些东西送到了门口。” 快过年了,院里带剑送礼,哪怕再客气,他们自然不敢不收。 京兆尹叹息了一声,放下了手里的那块腊肉,向着院子里走去,走了一半,又停了下来,看着一院子的积雪,沉默了很久,说道:“能退吗?” “能。”夫人同样叹息着,“但是他们说了,要你亲自去退。” 京兆尹没有再说什么,叹息着说道:“算了,算了,收下吧。” 身后的下人们神色忧愁地清点着那些东西。 京兆尹穿过了前院,去了后院的书房里,在桌案前发着呆,解着衣裳。 过了很久,他夫人端着一盆热水进来的时候,年迈的京兆尹依旧在解着衣裳,火炉也没点起来,一屋子寒气。 京兆尹夫人叹息了一声,把那些水盆放在了桌案边的椅子上,又过去帮他把衣裳解了,这才走过去点着火炉。 炉子点了起来,屋子温度上来了一些。 只是大概屋里的二人还是觉得有些挥之不去的寒意。 “悬薜院今日之事,是不是因为明年开春的一些事情?” 京兆尹夫人一面拧着热毛巾,给这位兢兢业业的老大人擦着脸,一面很是忧愁的问道。 “除了这件事,还能因为什么?”京兆尹叹息着说道。 黄粱的京兆尹,在人间一些大事面前,总有些进退两难。 有些权势,但是不多。 却偏偏又管着假都的诸多事情。 夫人也跟着叹息着。 京兆尹推开了脸上的热毛巾,深吸了一口气,问道:“奉常府那边呢?” 三公九司大人的府邸往往都是在同一坊中。 奉常府自然便在京兆尹的府邸旁边不远。 夫人把毛巾重新浸回了热水里,低声说道:“院里的人没有去,我之前让人出去看过,整个明合坊,只有我们这里来了院里的人。” 倘若坊里还有别家也收到了东西,那么京兆尹这里自然还可以装一会傻,充一会愣。 但是偏偏只有他家收到了。 所以大概悬薜院的意思也很明显。 就是要拉这个老人下水。 京兆尹紧锁着眉头,靠在椅背上,不住地捏着眉心。 夫人在那里拧了许久的毛巾,而后试探性地说道:“要不就去告诉他们,就说太一春祭之事,京兆尹这边只是协同奉常府,不知详情?” 京兆尹轻声说道:“污水已经泼在了身上,你去和泼污水的说并没有意义,要想办法向假都证明。” 夫人沉默了下来。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 谁都知道现而今的悬薜院,与假都大流不同,他们是独立于假都之外的存在,从这个冬天的一些事情里,便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 哪怕是院里的巫鬼院,亦是与人间巫鬼道没有走在同一条路上。 神女重临人间,许多人仍在观望,但是很显然悬薜院里的态度是鲜明的拒绝的。 所以送一车腊肉也好,送一车银钱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些泼向京兆尹的污水。 而且这场污水京兆尹躲不了,青牛院的人带剑送礼,他们没法躲。 哪怕世人知道京兆尹不得不收,总归还是对于这处司衙是否已经站在了神女的对立面,开始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三公已经废除,剩下的九司依旧保持着沉默。 至少当今黄粱,一切明面上的态度,依旧是以倾向神女重现巫鬼神教为主。 二人在书房里沉默了许久。 “怎么证明?” “去宫里求见神女。”京兆尹轻声说道,“但是.....” 但是以求见神女洗掉悬薜院泼来的污水,也便意味着,京兆尹彻底站在了神女那边。 站在神女那边未必是坏事,站在悬薜院这边也未必是好事。 只是当下人间,真正明白槐安与黄粱之间差距的人,都不会想要跳出来,主动去做这样一个选择。 站在了神女那边,也便意味着,日后将会面对北方那位陛下。 世人这才是真正听闻神女的第一个冬日。 而北方的那位陛下,他们已经听闻了一千年。 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二人再度沉默了很久。 京兆尹轻声说道:“你让人再去坊里看看,拜访一下九司大人们。” 夫人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是要把九司一起拖下水?” 京兆尹叹息着说道:“只能尽量挣扎一下,那些腊肉的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未必肯开门。” 夫人轻声说道:“好的。” 于是端着那盆已经冷了的水匆匆走了出去。 书房的门关了上来,窗外天色昏暗,只有炉火在不远处散发着一些光芒。 门外传来了一些声音。 “你们再去奉常府典客府那些地方逛逛,行迹可疑一些。” “要让别人看见吗?” “要让别人看见的行迹可疑,最好是让人怀疑你们有什么事。” “......” 京兆尹愁眉苦脸地坐在桌前。 虽然这样的事情很是无耻。 但是没有办法。 不能得罪悬薜院,也不能得罪神女大人。 那边只能得罪一下九司那边的人。 这位兢兢业业的老人,活到了下半辈子的时候,本以为能够安安分分的退下来,结果却偏偏遇见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晚节不保啊,晚节不保。 京兆尹苦笑了两声,而后从一旁抽出来了一张白纸,压在了桌面上,而后拿来砚台,倒了些水,开始磨着墨。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京兆尹才停了下来,将笔架在一旁,安静地等待着外面的消息传回来。 倘若真的整个明合坊没有一个开门的。 那他便只能给悬薜院写信了。 神女与世人之间。 总要做出一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