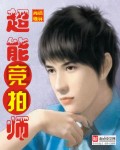原本认真的在那里劝诫着尤春山的二人到了这里却是沉默了下来。 事实证明,有时候,确实不能提前把事情想得太好。 尤春山反倒是如释重负一般,既有些释怀,也不难看出有些失落,坐在轮椅上笑了笑,回头看着南岛说道:“现在好了,师叔,我们不用纠结了。” 南岛并未说什么,只是一旁的替余朝云背着剑匣的余朝云很是惆怅,看着老大夫在巷子里走回去的身影,叹息了一声说道:“那咋办呢?” 三人大概确实都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如果天工司都无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确实有些不知所措了。 尤春山倒是平静得很,抬起头来,很是诚恳地说道:“先去吃饭吧,我有些饿了。” 那就先点菜吧。 ...... “其实那些走街串巷的,拿着旗子给人算命的人,一般都只会说你有血光之灾。” 卜算子站在天狱之外的巷子里,看着从槐都街巷里走回来的柳青河,很是突然的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柳青河虽然有些诧异这个缺一门的道人为什么还在这里,只不过大概更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会突然说着一句这样的话。 六月底的槐都街头很是喧哗热闹,于是生长在巷子里的槐树的叶子,也很是应时地在风里飘落着。 大猿的肩头落了一些叶子。 倘若是往常时候,他只会微微笑着抬手拂去。 只是当看见谢朝雨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有些很是寻常的东西,也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命中注定会垂落肩头的叶子。 它为什么早不落晚不落,偏偏这个时候落下来呢? 柳青河伸手从肩头拿了一片叶子,走到了卜算子身旁,抬头看了眼天色,天色不算很晚。 “为什么?” “因为趋吉避害,是世间生灵的本性。” 卜算子并未说一个人字。 事实上也确实不止是人,天下万物,能够蠕动的一切,自然都是有着趋利性。 柳青河好像明白了什么,微微笑着说道:“所以算命的会说你近日会有血光之灾,必须要如何如何去做,你才能化解。倘若你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便是确实化解了,倘若你做了,正好运气不好,路过巷子被掉下的瓦砸伤了脚指头,你就会想大师真的神机妙算,倘若你做了,运气实在倒霉到了极点,犯了一些事被砍头了,你就会想着,早知道当时就多给大师一些钱了。但我如果对此不屑一顾呢?” 卜算子低头轻声笑了笑,说道:“那对你而言,我就是江湖骗子又如何,一个人不信,并不耽误天下人不信。” 柳青河低下头来,看着身旁那个老迈的道人,说道:“所以观主这是想说什么?” 离命运三尺的老道人淡然地说道:“能够许人命运期望值的,自然是本身便有着这样的本事的。” 柳青河挑眉说道:“那观主能不能祝我天天清闲,不用工作,只要饮酒看花便行?” 卜算子默然无语,看了柳青河许久,缓缓说道:“狱主大人有些强人所难了,小道确实没有这样的本事。” 柳青河站在巷子里哈哈大笑。 一直笑了许久,柳青河才重新低下头来,看着卜算子微笑着说道:“观主为何还在槐都之中?” 卜算子轻声说道:“这便是我所说的,许人命运期望值的故事。” 柳青河挑了挑眉,又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转头向着巷子的另一头看去。 槐都繁华的街头,有少年好像怕晒,撑着伞在那里默默地走着,也有年轻人好像怕累,很是慵懒地缩在轮椅里叫人推着,更有穿着道裙的少女如同渴望做剑修,背着一个极为精致的剑匣。 天下万物,只看一眼,当然是看不到本质的。 柳青河一直看了很久,才颇有些惊意地看向身旁的老道人:“观主当初便已经看到了现而今的这一幕?” 卜算子想了想,说道:“倘若我说我确实看见了,狱主会不会觉得扯犊子?” 柳青河诚恳地说道:“会的。” 卜算子轻声笑了笑,说道:“因为这确实是扯犊子的事。” 这大概也是与卜算子所提出的缺一粒子观测谬误值是相悖违的。 “所言务虚,所见未实。”卜算子很是认真地站在那里,“知道酒旗会动,那便不要去想什么时候风来。” 柳青河立于巷中,缓缓说道:“风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的。” 这个天狱之主好像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先前卜算子会开口说着寻常算命之人,一般只说血光之灾这样的东西了。 卜算子大概确实不一般。 他敢开口说尤春山必定会成为一个大剑修。 柳青河站在那里眯着眼睛看着巷子里那三个似乎是在寻找着食肆的人许久,而后轻声说道:“悬薜院的风物院与数理院,在万灵拟态方面强于天工司,那么缺一门呢?” 老道人微微一笑。 “是机括精密程度。” 毕竟,当初天下机括之道,青天道一直都是走在人间前列。 柳青河很是唏嘘地说道:“原来是这样。” 这个天狱之主转头看向卜算子,想了想,说道:“需要我来做命运的推手?” 卜算子只是平静地说道:“狱主大人亲自去说这样的东西,未免还是太刻意了。” 柳青河叹息了一声,说道:“但存在着信息差的命运,有时是很难走出去的。” ...... 三人之中,大概也只有南岛在槐都逗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尤春山和余朝云,都是在来了槐都之后,便匆匆去了天工司,所以大概那次余朝云受南岛所托,上来听听槐都风声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些裂开的南瓜一样的人间,才会有着那般的惊叹。 三个人都是没有什么钱的,所以最后南岛还是带着两人去了当初的那个面馆。 顾小二总觉得这三人有些眼熟,只是大概有些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了。 唯一印象深刻一些的,便是那个撑着伞背着剑的少年,少年模样并不出众,只是这般姿态,很难让人忘记。 应该是叫南岛吧。 顾小二其实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如果祝从文在的话,一定会知道。 可惜那个书生去了国子监之后,就音讯全无了。 只是大概少年是叫做南岛,还是叫做北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就连丛刃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对于顾小二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自然更不用说这个坐在窗边的少年。 这个中年男人跑过来,问了三人要什么面之后,便匆匆进了后厨。 余朝云把尤春山从轮椅上搀扶了下来——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毕竟他只是坏了一条腿,又不是全身瘫痪了,先前在崖上的时候,还能拄着拐在那里看着仙气瞎溜达。 只不过因为尤春山过往喜欢平地摔的缘故,余朝云还是下意识地将他扶了下来。 尤春山坐在了南岛的对面,扭头看着一旁在那里整理着轮椅的余朝云,又转回头来,看着少年师叔,很是诚恳地说道:“其实想一想,走到了这里,也挺好的了,师叔,以前我能走能跳,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就突然瘫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现在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是自然也算得上好事。再说了,无非便是不能做剑修的事而已,天下难道只有走剑修这一条路吗?” 天下当然不止是做剑修这一条路。 倘若这个年轻人未曾牵扯进某些故事里。 自然想做什么都可以。 南岛默默的看着尤春山,倒也没有说什么那个说着命运的老道人该怎么办。 毕竟对于少年而言,哪怕那是一个十三叠大修,终究也不过是命运里萍水相逢的路人而已。 只是少年哪怕不说,尤春山自己也不可能真的便将这样一件事忽略了过去。 只是有些东西说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 面端了过来要趁热吃才是有意义的。 提前准备了料子的面,来得确实很快。 余朝云还没有想好剑匣要不要取下来,面馆里的小二便已经将热腾腾的面端了上来。 东海那家面馆的面确实是很好的,只是那是遥远的。 三人坐在那里,都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各有心思地埋头吃着面。 余朝云与尤春山虽然在这里吃过面,但是大概也已经不记得了,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 只是南岛却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着在那里擦着旁边桌子的顾小二,问了一句。 “祝从文不在了吗?” 书生与少年的交集其实也不算多。 只是终究在这样一个人间以北的都城里,能够见到了一些南衣城来的人,大概确实是能够有着一些慰藉的。 顾小二抬起头来,看着窗边的伞下少年许久,又重新低下头去,笑着说道:“他去国子监了,日后大概很难回来这处面馆了,毕竟坐在小馆子里吃面这样的事,可能有些不体面。” 南岛其实有些听不明白顾小二说的那些东西,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少年也确实不是什么多话的人。 三人坐在那里吃完了面,少年付了钱结了账,又一同站在了槐都的悬街之上。 街头人来人往,有向下踩着台阶,去往下层街巷的,也有向上而去,去到高层楼台的。 尤春山很是惊叹地站在那里。 天工司属于槐都,只是槐都当然不是那样一个总是被一些水汽弥漫遮掩的地方。 它首先是人间的槐都。 三人有些无事可做,于是便顺着那些熙熙攘攘的人流,在街巷里随意地穿行着散着步。 在走到斜月台附近的悬街的时候,坐在轮椅里的尤春山却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着南岛问道:“师叔,我记得那次来的时候,这上面不是有着很多剑修的吗?怎么现在都不见了?” 南岛抬头越过伞沿,静静地看了那样一处在白昼时分尚未升到槐都顶端的宽阔平台许久,里面确实很是寂寥,既没有月色,也没有剑修,只有一些孩童在里面跑着玩耍着。 事实上,这样一个问题,不止是尤春山会好奇,人间诸多世人也会好奇。 人间剑宗匆匆而来,最后与巳午妖府的故事一同沉寂下来了。 世人不免猜测他们落得了与巳午妖府一样的下场。 当尤春山这样问着的时候,身旁其实有着不少的路人在侧目看着三人。 伞下剑修,轮椅上的年轻人,背着剑匣的道修少女,这样的组合,无论走到那里,都不会有人觉得他们只是普通的世人而已。 所以或许也确实有些好奇是否会在这样一个被叫做师叔的少年口中听到一些答案。 南岛当然知道。 只是当他发现世人并不知道的时候,便意识到大概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 所以他想着那日那个帝王与自己说过的大漠之事,却也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 尤春山显然有些遗憾,叹息了一声,说道:“好吧,其实当初刚来槐都的时候,抬眼看见那些坐在台子里的剑修,倒是想过,到时候要是病治好了,就去找个有眼缘的拜师学剑。” 毕竟那是人间剑宗的剑修,槐都之中有过这样想法的,大概也确实不在少数。 余朝云倒是笑了笑,说道:“你不是说你的剑,是和丛刃前辈学的吗?” 尤春山说道:“如果真是,那何至于此?” 说着这个东海年轻人倒是有些痴心妄想地说道:“倘若我师父是丛刃,那我怎么说也得去南衣城干上几回吃饭不给钱的勾当。” “......” 三人一面闲谈着,一面向着槐都更高处而去。 这样一座都城虽然不是山上之城,只是有时候大概远胜于山上之城。遍地楼阁悬街层叠堆砌,一如陈鹤所说的云川之事。倘若有人畏高,大概还不敢往着上方走去。 尤春山托着腮,被余朝云推着,一直到了上层悬街边上。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这个东海年轻人倒是突然抬头看向了那片头顶渐渐带了一些橘色光芒的天空,很是感叹地说着。 余朝云虽然不知道尤春山为何要说着这样的东西,却也是好奇地抬头看向那片天穹,轻声说道:“难道真的有天上人?” 尤春山看了一眼一旁的少年,后者很是平静地撑着伞站在那里。尤春山于是又转回了头去,看着松开轮椅,背着剑匣站到了另一边的余朝云,认真地说道:“当然有,我还见过。” 也许还曾经笑摸他的狗头,说很好,现在你可以长生久视了。 余朝云大概并不会信,只是看着那片渐渐向着黄昏里垂落下去的天光之处,不无感叹地说道:“难怪那日陛下会说着人间的黄昏是看不腻的。” 没有什么解释。 只是真的是看不腻的而已。 然而看着看着,这个青天道的少女神色便有些古怪起来,蓦然低头看着自己的搭在护栏是的手背。 那上面似乎有着一片雪屑,只是正在迅速地消融着。 这个青天道少女下意识地便看向了身旁的那个少年师叔。 少年伞下风雪的事,虽然不是人人尽知。 只是。 只是东海开始有了名声的细雪剑南岛,大概并不算什么隐秘的事情。 她本以为是这个师叔拔剑了。 只是并没有。 那个伞下少年,见不得人间雨雪的伞下少年,同样低着头,看着某片被吹入了伞下的细雪之屑。 人间暮雪。 只是这又好像是少年少女的一种错觉一般,六月末虽然代表着人间立秋。 然而哪怕是槐安以北,都不会有着风雪。 除非是地势极高之地。 槐都高吗? 当然很高,但是远不至于会有雪的地步。 有些后知后觉的尤春山,却也是看见了一片细雪落在了轮椅上,只是抬头看去的时候,分明什么也没有。 这个东海年轻人却也是看向了南岛。 毕竟余朝云只是听说了细雪剑的名字。 而尤春山却是在东海崖下亲眼见到细雪剑这个名号的诞生的。 少年站在溪畔,面对着那些东海剑修的问题,很是平静地说着细雪二字。 南岛当然知道二人在看自己。 这个伞下少年只是平静的将手翻转过去,将那片还未来得及消融的雪花抖落下去,轻声说道:“与我没有关系。” 事实上,在这一刻,整个槐都的那些人们,都是神色惊奇地抬起头,看着天空,似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细雪的垂落。 只是。 只是抬头看去,一天暮色悠然,并没有什么大雪将临的征兆。 三人在悬街之上看了许久,南岛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骤然自身后拔出了那柄鹦鹉洲。 一旁的余朝云与尤春山很是不解的看着这个少年师叔。 少年只是眯着眼睛,静静地看着剑上那些正在缓缓消退的剑意。 一直过了很久,才神色复杂地将那柄剑收了回去,抬头看着天空,轻声说道:“也许是草为萤死了。” 余朝云听着这个名字,有些茫然地站在那里。 只是一旁的尤春山却是露出了很是惊诧的神色。 “师叔没开玩笑?” 这个东海年轻人确实有些难以接受这样一件事情。 他虽然只见过那个青裳少年一次,只是却看见了更多的东西。 南岛心底有些失落,并未回答尤春山的问题,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长久地看着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