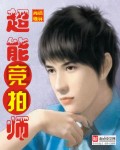陈鹤最后还是没有去看看那一场战争的模样。 在小楼与草为萤喝了很久的酒之后,便回去了藏书馆。 暮色降临的时候,那些城外的声音也平息在了风里。 张小鱼抱着剑面朝南衣城坐着。 白衣之上有着不少的血色。 这些血色自然不会是张小鱼的。 而是那些借助巫鬼之术,成功地突破至南衣城下,又踏着巫鬼之术登上城头的黄粱之人的血。 一直到最后僵持了许久,在城外留下了无数尸体,黄粱之人才退了回去,停留在了大泽边。 张小鱼没有去看,也没有去过问岭南剑修的死伤情况,只是转过身来,沉默地看着南衣城。 梅曲明便在一旁,身后背着剑都还没有擦干净,正沿着剑鞘往下滴着血,这个在南衣城渡人过河过了很多年的师兄此时正歪头看着张小鱼。 “师弟?” 梅曲明没有叫张小鱼的名字。 张小鱼过了很久才转过头来看着梅曲明,轻声说道:“怎么了师兄?” 梅曲明没有说什么,只是拍了拍张小鱼的肩膀。 张小鱼又转回头去,看着南衣城中安静的街巷。 过了许久,张小鱼才叹息了一声,缓缓说道:“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都不是想想而已的。” “什么?”梅曲明转过头看着张小鱼,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说出一句这样的话。 张小鱼看着天边那些昏黄的色彩,想了很久,说道:“御剑千里杀人,与当面杀人是不一样的。杀一个人与杀一千人也是不一样的。我以前也杀过人,以后也会杀人。但在这样的故事里,我却有些不敢杀人。” 梅曲明沉默了少许,说道:“为什么?” 张小鱼轻声说道:“我能够理解战争的意义——是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正义的不正义的,本质都是这样的。但是当那些巫鬼道人远远的站在一切的后面,任由这些世人冲上南衣城城头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无比的......” 张小鱼说到这里,停了很久,眯着眼长久地看着那些如血一般的天空。 “惶恐。” 张小鱼轻轻地吐出了这个字眼。 “不是悲哀,不是怜悯,是惶恐,也是愤怒。” “在最开始的时候,当我看见这场战争的一丝雏形的时候,我也曾畅想过,一人一剑,自南杀到北。” “但是真的身临其境之后,我却发现我还是找不到那样的切入点——我修行的意义不是为了杀人,更不是为了杀世人——修行在我,而不在如何让世人看我。” 梅曲明沉默了很久,说道:“但是他们既然选择了随着巫鬼道人一起跨越大泽而来,便代表了,他们也是选择中的人。我知道师弟你的意思——战争的思维来自于高层的判断,下层往往是被簇拥着向前的。但生于两地,所见人间本就不同。那日明先生的话,我以为你听进去了,却原来你一直都是糊涂的,反倒听明白了的人,是我们。” 张小鱼只是看着南衣城,摇头不语。 “仁爱,世人,信仰,忠诚。所有的这样的词语,都是带着立场的,站在南衣城的城头之上,我们便没有怜悯黄粱之人的权利。” 梅曲明说得很平静,也很冷酷。 但这是最真诚的事实。 梅曲明拔出了张小鱼背后的鹦鹉洲,看着上面的血色,轻声说道:“剑上的仁爱,是没有立场的愚蠢。” 张小鱼叹息了一声,从师兄手里接过了那柄剑,轻声说道:“我知道了师兄。” 梅曲明拍了拍张小鱼的肩膀,笑着说道:“好好休息一会吧,如果不想成为南衣城的旗帜,我会让曲莎明他们代替你。” 梅曲明说着看向了大泽那边,继续说道:“他们既然已经开始攻城了,那么师兄们应该也快回来了。” 张小鱼点了点头,抱着剑跳下了城头,向着南衣城的酒肆而去。 城头暮色洒在人间,大概也是种像血一样的色彩。 张小鱼背着剑走在寂寥的街头,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影子歪在东面的墙上。 “今日打赢了吗,张师兄?”有行人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看着一身血色白衣走在街上的张小鱼问道。 那人自然不是修行者,只是或许与张小鱼打过牌。 但是今日没有叫张点炮,而是客气地叫着张师兄。 其实世人一直都知道许多的事情。 张小鱼勉强笑了笑,说道:“还行。” 那人转身回到了院子里,摸了些吃的递给了张小鱼,还有一条湿毛巾。 “你先擦擦吧,然后吃点东西。” 张小鱼也没有拒绝,接过来擦了擦脸,而后拿着那些已经凉了的吃的,一路边走边吃着。 那人还在后面说着。 “师兄们加油!” 张小鱼当然在加油。 坐在暮色城头上沉默的是他。 那柄剑自始至终没有回过鞘的也是他。 但正是因为剑上见血太多。 张小鱼看什么都有种悲哀的色彩。 杀一个人与杀一千个人当然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是一样的。 一样地归属于不同程度的罪恶。 张小鱼沉默地吃完了东西,在白衣上擦了擦手,沿着长街继续走去。 鼠鼠的小舟便停在城南河边,看见张小鱼走过去,却也没有说什么。 张小鱼走了过去,又走了回来,看着鼠鼠问道:“你怎么不问我打赢了没有?” 鼠鼠坐在舟头托着脸耸耸肩说道:“既然你都能够在街头闲逛了,那肯定打赢了啊,我还问干什么,不如让你一个人安静的待会。” 张小鱼觉得很有道理。 原本他也应该能够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来。 但是现在脑子有点乱,所以看起来痴痴傻傻的模样。 于是和鼠鼠挥了挥手,继续沿着河走去。 “师兄。” 鼠鼠在后面叫住了他。 张小鱼回过头去,只见鼠鼠歪头想了想,说道:“其实我后来想明白了,你们当然是对的。” “有些时候选择让一些人死去,是可以理解的。” 鼠鼠说着,又想起来这应该是与陈怀风说的话。 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你听不懂,可以问问你陈师兄。” 张小鱼在河边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个那日曾经愤怒过的小鼠妖,缓缓说道:“我能够听懂,但那是错的。” “?”鼠鼠一头雾水地看着张小鱼,不知道他发什么癫。 张小鱼平静地说道:“当一段岁月以一个错误的开头开始的时候,里面的一切决定,都是错误的——不可更改不可追悔的错误。” “柳三月的死是这样,人间剑宗的诸多决定是这样,人间的许多选择也是这样,一直到这场战争的开始,与不知道什么时候的结束。一切都不应该有。”张小鱼转过身去,平静地说着,“因为故事的开头便错了。” 鼠鼠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张小鱼在说什么。 所以她只能干巴巴地问了一句:“错在哪里?” 张小鱼转头看向北方。 北方也有暮色,也有人间。 只是不知道是否有人一身血色站在余霞里,想着这样的事情。 “任何以一己私欲裹挟人间去做伤害他们的事情的故事,都是不被允许不可饶恕的。”张小鱼轻声说道。“有人犯了用错误来证明错误的逻辑悖论。” “又或许,他们本就知道一切的对错。” “但是一意孤行了。” 鼠鼠沉默地坐在舟头。 张小鱼在暮色河边向着某个酒肆而去。 但是远远地还能听到他的低喃的声音。 “我不打牌了。” 鼠鼠一头雾水。 他在说什么鬼话? 这和打不打牌有什么关系? 鼠鼠挠了挠头,却发现自己许久没洗的头发里突然掉出来一张红中。 ???? ...... 陆小小坐在城墙之下,砍出了豁口的剑放在大腿旁边,嘴里咬着个沾血的包子,正在给自己包扎着伤口。 虽然张小鱼与南岛后来都没有见到这个小小的剑修。 但是她当然还没有死。 岭南剑修死了很多人。 但是陆小小很幸运地没有死。 只是在面对数十把长剑的乱捅时,被捅到了右肋。 当时她都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了。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涌上了城墙,在他们的身后还不断有着成型的巫术鬼术落向城头。 但是陆小小完全没有想到剑宗的张小鱼师兄那么勇猛。 一人一剑,无比强悍地守住了整个墙头。 同时还不忘施展着道术山河,与那些远道而来的巫鬼之术相抗衡。 在张小鱼与几位剑宗师兄的协助下,陆小小他们这些岭南剑修却也成功地在那三十万人前赴后继的登城之中,顽强地守了下来。 陆小小包子咬了太久,嘴角都开始流着口水,于是匆匆的包扎完毕,又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包子,想去塞给师兄们补一补。 只是一转头,便发现张小鱼已经不见了人,不知道哪去了,而那几个师兄们都是在城头盘坐调息着。 陆小小倒也没好意思去打扰一下他们,于是自顾自的又吃了一个包子。 在城头有些疲倦地呆坐了一会,陆小小又站了起来,去分辨着城头的尸体。 是岭南剑修的尸体,便拖到墙边摆好,有人会将他们带下去,烧成灰送往凤栖岭。 如果是黄粱人的尸体,便踩上两脚,再丢下城头去。 多拖了一些尸体之后,陆小小也有些疲倦了起来,与也没有再踩,只是丢下去便没有再管。 陆小小也有些疑惑。 她下山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面对的会是黄粱这些普通人。 黄粱与槐安在一千年前便已经统一了,为什么还会有这场战争的存在? 陆小小没有想明白。 她下山的时候,以为自己会面对很多大泽里爬出来的东西,比如想象里的鬼怪,吃人的妖兽。 但是没有。 什么也没有。 只是人。 从大泽很远的另一头赶来的人。 陆小小叹了一口气,她也想说点什么不一样的,很玄妙很震撼的半懂不懂的话。 但是她没有接触过那样的东西,所以只好一面叹着气,一面和旁边的岭南某个剑修说着一些‘他们真是疯了’这样的话。 “他们真是疯了。” “可不是嘛,大老远跑这一趟,他们遭罪,我们也遭罪。” “那些修巫鬼的人真该死啊!” “......” 一行岭南剑修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拖着尸体有气无力的走在城头上。 陆小小他们当然可以不来。 也可以在见到这样一场发生在人间与修行界之中,极为微妙的战争之后,转身回到凤栖岭上。 但是他们走了,谁来帮南衣城守城呢? 所以只好一面抱怨着,一面带着陈怀风所说的,那种愚蠢的热爱,留在了城头之上。 陆小小搬了许久的尸体,才停了下来,靠着墙边看着西面的暮色歇息着。 带血的斗笠与染血的剑,还有小小的倚在暮色城头的女子剑修。 似乎是一幅意境极佳的画卷。 但是意境的背后,自然是一个并不如何动人的故事。 陆小小看了一会,觉得有些疲倦了,于是又坐了下来,好好的歇息一下。 毕竟不知道黄粱的那些大军何时还会卷土重来。 ...... 南岛是被黄昏时分的晚风吹醒的。 睁开眼睛,身周剑意渐渐弥散。 满目残阳照落墓山,无比寥落。 风里有血的味道。 南岛看向一旁,小少年胡芦又抱着剑睡着了。只不过这一次他抱的是自己的剑,而不是那柄方寸。 南岛又看向墓山上面,陈怀风依旧安静的坐在那里。 只是身周不止有剑意,还有风雨。 南岛看见陈怀风身周的那一帘风雨的时候,却是愣了一愣。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那些风雨格外的熟悉。 真是古怪,自己为什么会对他身周的那些风雨感到熟悉呢? 南岛皱起了眉头。 师兄既然名字叫陈怀风,那么怀里有点风雨也是正常的吧。 有扳手才是不正常的。 南岛坐在那里按着膝头的桃花剑胡思乱想着,又看回了最初睁开眼的时候看见的那些满地残阳余晖。 今日的夕阳的风格外的古怪啊。 南岛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些寒意,打了个寒颤。然后站了起来,抱着桃花剑向着墓山顶端走去。 陈怀风好像抱着一帘风雨在睡觉,南岛踩着一地杂草的声音很是嘈杂,然而陈怀风便是什么也没听见一般,静静的面朝同归碑坐着,一手似乎放在怀里,一手伸在旁边,握着不知何时插在泥土中的枸杞剑。 南岛一直走到了陈怀风的背后,后者都没有任何反应。 应该是睡着了? 南岛这样想着,站在陈怀风的背后探头向前看去。 然后便与陈怀风那双乌溜溜的黑眼珠对视在了一起。 南岛蹭的一下把头缩了回去。 老实巴交的模样,讷讷的说道:“师兄你怎么一直不说话。” 陈怀风平静的说道:“因为我在听风声。” 听风声做什么? 南岛有些费解。 不过既然叫陈怀风,那么爱听点风声,也是合情合理的。 南岛没有再纠结下去。 南岛正想着该如何委婉的提出来,离开墓山。 陈怀风便已经先行开口了。 “你把胡芦叫醒,便离开吧。” 南岛总觉得自己的思想被这些剑宗师兄窥探完了。 不过也只敢腹诽两句,而不敢像那晚一样,说着今日我应该有资格拔剑之类的年轻的话语了。 毕竟已经老大不小了——老一日也是老,老两日也是老。 “好的,师兄。” 南岛抱剑行了一礼,转身向下走去。 满山墓碑寂静林立,在暮色里拖着长长的影子。 南岛一直走到了先前与胡芦坐着的地方,推着胡芦的肩膀。 “你师兄找你,快醒醒!” 胡芦打着哈欠,说道:“什么师兄?” 南岛站在伞下默然无语。 胡芦打了好几个哈欠之后,似乎清醒了一些,擦了擦嘴角——其实并没有口水。然后睁开眼睛茫然的看着四周,却也是像南岛一样似乎被暮色里的寒意吹了一下,身体抖了一下,然后拢了拢衣裳,抬头向墓山上看去。 “怀风师兄找我做什么?难道找到师父了?”胡芦自顾自的念叨着,撑着剑站了起来。 南岛说道:“我也不知道,冻死了,我先走了。” 胡芦也没有挽留,抱着剑打着哈欠向上走去,头也不回的摆了摆手。 南岛走了一段之后确实突然有些愤怒。 凭啥小少年葫芦也可以这么帅? 南岛想着胡芦方才那在暮色里抱剑而去头也不回的摆手模样。 甚是潇洒。 自己怎么就不能这么帅呢? 南岛觉得下次这种情况,自己一定要先发制人,南岛如是想着,抱着剑撑着伞愤愤不平的向下走去。 “张小鱼在城南酒肆里。” 陈怀风的声音从墓山之上传了下来。 南岛转回头,看着墓山之巅安静坐着的陈怀风。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张小鱼在酒肆告诉我做什么? 还有张小鱼不是应该在城头上吗? 南岛站在那里想了许久,却是突然想起来刚刚醒来的时候嗅闻到的风里的那种古怪的味道。 愣了一愣。 难道外面已经打起来了,然后张小鱼被打断了腿,正在酒肆买酒消愁? 南岛皱着眉头想了许久,把剑背到了身后,撑着伞走下了墓山,向着城南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