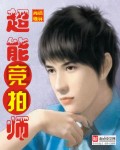夜色之中人们欢声笑语,没有人注意到某个河畔的曾被烟火短暂照亮过的角落里,有人平静地抽回了自己的剑,而后头也不回地踏着风雪离去。 带剑而去的人一直向着来时的方向而去,而后停在了某个已经死在了迎风楼下的老人曾经提着灯笼坐过的位置。 一直坐了许久,才有一个身穿巫袍的人匆匆在风雪里赶了过来。 那人停在了夜色里,安静地看着这个来自北方的剑修很久。 “三万贯不是个小数目。” 那人缓缓说道,而后从怀里摸出了一个软绵绵的包袱,递给了那个坐在风雪台阶上的剑修。 “巫鬼道的人会等着。” 寒蝉笑眯眯地打开了那个包袱,随意地看了几眼,便将它塞进了怀里。 而后从怀里摸出了一枚古朴的铜钱,丢到了那人怀里。 那是一枚色彩斑驳的古老铜钱,并没有什么特殊功效,来自一千多年前的槐安第二帝,或许是因为鬼帝自焚于摘星楼的缘故,背面是一栋被方孔截断的烈火之楼,正面是安宁圣明二字。 明皇帝一朝过于短暂,而且夹在鬼帝与槐帝之间,毫无存在感。 是以这些铜钱铸造的并不多,大多数都已经在岁月里流失重铸,只有一小部分还留在流云剑宗手中,作为交易的凭证。 “如果我没有完成,你可以拿着这枚铜钱,去流云剑宗继续找下一个人,哪怕是找到了宗主头上,也是可以的。” 寒蝉站了起来,很有耐心地解释着。 “如果我完成了,你可以将这枚铜钱还给我,也可以自己留着,观摩收藏一段时间,但是每年年末,都会有剑宗的人前来把它收走。” 那人很是古怪地看着寒蝉,说道:“你们流云剑宗的脾气都这么好?” 寒蝉轻声笑道:“你也知道三万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新年新气象,开年便有单子,谁会不开心呢?” “当然我们也确实会有脾气不好的时候,比如有时候,你遇见了一个看起来很是落魄的流云剑宗的人,千万记得语气要好一点,不要再说什么巫鬼道会等着这样的含义不明的威胁的话——因为他一看就是很久都没有开过张了,才会那样落魄。这种时候,我们的脾气比寻常剑宗的人还要差。” 那个巫鬼之人沉默了少许,将那枚铜钱收进了怀里,轻声说道:“原来是这样。” 寒蝉将剑抱在怀里,向着那些热闹终于开始冷清下去的长街里走去。 “而且,对于一个流云剑宗的人而言,所谓的巫鬼道的威胁,确实不如何。” 那人静静地看着那个抱剑而去的剑修。 “什么时候动手?” “不确定,我再看看。” 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云竹生这样昂贵而且好杀。 ...... 让双方都满意是一件很难的事。 尤其是在杀人的事情之中。 不知道是寒蝉真的打算让云竹生也满意,还是那个从北方关外咳了一路走来的道人神海里有些白梅之韵的原因。 云竹生并没有死,还有一口气。 神海里仅存的一抹元气,吊住了他的心脉。 道人虽然身躯强于剑宗之人,但是那样近距离的一剑在体内爆发,哪怕他是大道之修,自然也承受不住。 这个山河观道人撑着伞,没有再握住那个暖炉,扶着河岸护栏大口的喘息着,身躯之上不住地有剑痕游走着,如同剑纹一般,遍布全身,如同一身裂痕,看起来很是凄惨。 也许是为了不惊到世人,道人的那柄伞压得很低。 所以河岸时有归家行人路过,却也没有谁注意到那些覆在风雪里的星星点点的血色。 只是觉得这个人也许有些失落。 大概无人一同过年。 云竹生喘息了许久,才终于平静了下来。 平静当然并不意味着能够活下来了。 与之相反的是,平静意味着体内只剩下了摧毁一切的剑意。 有些来自那个流云剑宗的弟子,有些来自更早一些,残存在体内的如同顽疾一般不可祛除的磨剑崖剑意。 但是云竹生没有在意。 只是安安静静地压低着伞沿,沿着长河慢慢地走去。 一直到穿过了某条大雪覆盖的巷子,停在了一处桥边。 京兆尹的人已经离开了这里。 一河雪檐白墙,在夜色里格外的宁静。 云竹生当然没有告诉寒蝉许多东西。 譬如当初路过这里的时候,他便认出了那样一个人是谁。 柳三月现而今的模样,自然是难以辨认的,哪怕是他曾经的好友,张小鱼路过的时候,也只是将他当成了一条路边失家的野狗。 但是可以从一些别的东西看出来。 譬如那些带着青天道风格的铁索机括。 山河观来自青天道。 所以云竹生一眼便能够看得出来那些东西来自哪里。 遥远的黄粱,出现了这样一个青天道的东西。 那个被锁之人的身份并不难猜。 云竹生站在桥头伞下,一面捂着嘴咳嗽着,一面长久地看着那个风雪桥头坐在风雪里的人,而后拖着虚弱的身体,一步步向着桥那头走去。 也许是那些踩在雪里的声音,也许是云竹生压抑的咳嗽声。 总之总有一些声音传到了这座风雪孤寂之桥的另一头。 所以那个容貌丑陋的男人抬起了头。 脸上的表情是扭曲的狰狞的。 但是表情有时候并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情绪。 云竹生眼睛里有些血色,是自己身体里的,许多的血管被剑意搅碎,这使得体内的血液在胡乱地流淌着。 但是那种带着血色意味的风雪里,那个坐在桥头抬起头来的人眼眸之中的茫然,依旧是清晰可见的。 表情当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情绪。 他的眼神才是。 云竹生带着那种肺叶被切开的呼吸声,停在了柳三月身前。 也许是柳四月。 云竹生并不知道。 这个一路从北方风雪走到了南方风雪的山河观道人,张开嘴,也许是要说些什么,只是才始张嘴,一口鲜血便自喉中涌了出来。 血里有着剑意,但是没有道韵,也没有元气。 那些剑意随着鲜血一同落到柳三月身前的雪地里,瞬间便荡开了无数的风雪。 这个混混沌沌的男人,坐在风雪纷乱的桥头,怔怔地看着面前的这一幕,有些惶恐,有些不知所措。 云竹生痛苦地弯下腰,抬手捂着自己的心口,不住地喘息着,又重新抬起了头来,看着伞沿边缘的那个也许经历过无数痛苦的年轻人。 这个曾经青天道之中天赋极高的年轻道人现而今只是万般卑劣的模样,坐在风雪里,怔怔地看着面前的这个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为何而来的看起来病恹恹的人。 他想了很久,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些堆在雪中的石堆,又重新转回头来,看着面前的道人,很是生疏艰难地开口说道:“新....年快乐。” 云竹生浑身颤抖着,不住地笑着,眼眶有些湿润地看着这个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人曾经代表着怎样的美好的丑陋之人。 他没有再说什么新年快乐。 只是无比叹惋地看着面前之人,一面咳嗽着,一面轻声说道:“柳师弟,抱歉。” 坐在风雪桥头的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那个快要死了道人穿过了那些被自己咳出的血里的剑意搅乱的飞雪,跌跌撞撞地弃了伞,像是跨越万里的奔赴,而后仓皇地扑进所思之人的怀里一般。 但是这样的故事,自然不是多么感人的奔赴。 云竹生只是确实没有力气再去稳住自己的身形。 他原本想折断了手中的伞,就像在山月城中将那一枝梅枝插进自己师兄的心口一般,将伞骨插进面前这个人的胸膛。 但是他没有能够折断那柄伞,甚至于在穿过那些剑意风雪的时候,都没有握紧它。 柳三月茫然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那样一句今晚四处都听见了的新年快乐,可以感动得一个人以身相许? 混沌的柳三月只是在模仿着世人的言辞。 但是他看着那个跌倒在自己怀里的道人,犹豫了许久,轻轻抬起手,像是安抚一样地拍打着这个道人的后背。 只是下一刻。 柳三月便睁大了眼睛。 那个道人伸出双手,环抱着自己的腰部,而后借着自身的重量,用力地向着一旁滚去。 柳三月仓皇地想要伸手将这个道人推开,然而才始触碰到他的手臂之上,无数凌厉的剑意便迸发而出,当他因为吃痛而缩回手的时候,整个人便已经被带着,一同向着桥下滚去。 首先是铁索擦着雪下结冰的桥面叮叮当当滑动的声音,再然后便是沉闷的声音。 寂冷的风雪孤桥边有落水声响起。 ..... 那道剑光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刘春风站在春风院的檐下,安静地看着那一剑在夜穹之中留下的痕迹。 是带血的一剑。 看来某个在假都逗留了很久的南楚巫死了。 刘春风静静地看着夜穹里的被分开的风雪。 院里也许也会有些一些剑光。 但是他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只不过,总应该是在春招之前。 所以今日的悬薜院,大概会依旧平静下去。 刘春风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些破绽。 但是这样的破绽不能太明显,也不能太招摇。 这个三十岁的男人微微皱着眉头,站在雪檐之下,静静地想着。 书院里并没有什么声音,更多的那种细微的声音,是来自院外的假都街头,人们互道新年的祝福。 刘春风和院里的先生们大多没有这种想法,都是早早地,便回到了自己的小院子里。 因为他们很清楚。 新年是不快乐的。 于是连祝愿都免了。 ...... 南方的故事也许很是匆忙,在那片大风历一千零四年的第一个时辰里,便有着许多的故事在夜色里开始躁动着。 但是越过大泽而来,这座屹立于南北之间的古老之城却只是热闹。 尽管在南衣城外,便是那片有着许多不好的风声传来的大泽,也有着无数驻扎在城外的人间大军。 然而南衣城只是如同大风历一千零二年一般,在风雪之中散发出诸般平和且热烈的光芒。 今年的南衣城,也许少了一些人了。 梅先生早早地在家里打扫了卫生,做好饭,给李蝶在房间里准备好了明日穿的新衣服,而后便热酒去了。 谢先生如约而来,顶着一头风雪,还有一些烟花坠落的碎屑,穿过那条巷子,推开了梅先生家的院门。 三人便上了桌,在桌下点着小炉子,关了房门,开始吃着年夜饭。 谢先生回来南衣城之后,每年的年夜饭,都是梅先生家里吃的。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只是今年的梅先生家里,少了一个人。 只不过谁也没有提起,哪怕梅先生烧得那条鱼并不是怎么好吃,盐放多了,芡勾薄了,葱花姜叶也切得乱七八糟。 但是三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过年吃鱼,自然是为了一个好彩头。 谢先生挑着一块鱼肉,轻声笑着说道:“年年有鱼年年有鱼。” 梅先生拿着酒杯喝了一口,看着他笑道:“那你今年应该存了不少的钱吧。” 毕竟缺油灯了从梅先生那里拿,缺伞了从梅先生那里拿。 生活的琐碎小事都落在了梅先生头上,这个青牛院五先生大概确实能够存起不少的钱。 谢先生只是笑着摇摇头,而后把那块鱼肉放到一旁正在埋头吃着饭的李蝶碗中。 李蝶很是茫然地抬起头。 谢先生看着他说道:“我和你爹都是要老的人了,少余一些没关系,倒是你啊,小李蝶,你要多余一些。” 谢先生的笑意很诚恳,所以像是打趣也像是劝告。 李蝶歪着头想了想,说道:“好。” 大年三十,自然不会提及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是以这两个数十年的老朋友,也只是喝着酒吃着菜,说着今年一些开心的事情。 但是今年大概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南衣城外那场战争的阴霾,其实让整个南衣城都沉寂了很久,不止是战火燃起的时候。 几人吃完了饭,又带着李蝶出了门,在巷子里闲走着,看着人间的烟火。 谢先生与梅先生在巷子里闲走着,李蝶大概是有些困了,走了没多久,便在巷子的某棵树下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抬头看着那些像是一颗颗红果子一样悬挂在檐下的灯笼,又托着腮看着渺远天空里的绽放的烟火。 谢先生与梅先生走得并不远,只是在附近的一段路上来回的踱着步。 “你决定好了吗?” 梅先生看着谢先生问道。 谢先生停了下来,静静地看着那些雪檐之上的热烈的光芒。 “来之前,我已经在院里收拾好行李了。” 梅先生有些沉默,但并没有叹息,只是站在巷子里,看了许久,而后笑道:“你有什么行李吗?” 谢先生挑眉说道:“当然有,譬如十多盏油灯,七八把伞。” 梅先生哈哈笑着。 那些自然都是谢先生在梅先生这里的不良所得。 “当然,还有存了很多年的薪水,在院里做先生,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也是可以存下一些的。年年有余,二十年了,自然便余了很多。” 梅先生只是笑着没有说话。 一直过了许久,二人才颇有默契地看向不远处那个坐在雪里看着夜空的小少年。 “李蝶呢?” 梅先生轻声说道。 谢先生低下头,看着雪中一地凌乱的脚印。 “依旧是看他自己。” 梅先生至此终于叹息了一声,轻声说道:“明日我与他说一下吧。” 谢先生点了点头。 二人继续向前走了一段,梅先生停了下来,而谢先生继续向前走去,直到走出了巷子,身影消失在一片繁华热闹的风雪里。 梅先生在那里站了很久,才重新往回走去。 李蝶大概确实有些困了,托着腮坐在那里,眼皮其实已经有些分不开了。 梅先生走了过去,一把将昏昏欲睡的小李蝶抱了起来,就像过去几年那样,李蝶的头倦倦地趴在梅先生的肩头。 但其实梅先生现在这样抱着李蝶,已经很吃力了。 只是这个其实姓李但偏偏喜欢别人叫他梅先生的男人,大概总有些好面子。 所以一面抱着李蝶,一面故作轻松地与巷子里偶尔开门的人们打着招呼。 二人快回到自家院门口的时候。 李蝶却是趴在梅先生肩头揉着眼睛。 “爹。” “嗯?” “刚才你和谢叔在笑什么?” “没什么,你谢叔说了一个笑话。” “哦。” 李蝶没有再说什么,揉完了眼睛,又继续趴了下来。 梅先生以为他真的睡着了,于是在积雪的巷子里走得又慢了一些。 只是抬手按在院门上的时候,李蝶的声音又低低的在这个老男人的耳边响起。 “爹,我想娘了。” 梅先生怔怔地站在院门口。 微微抬头看着人间风雪,烟火璀璨的夜空中,有疏落的光芒洒落在梅先生的眼里。 褶褶生辉。 这个在悬薜院做了很多年门房的男人低下头去,缩回了那只按在门上的手,抚摸着李蝶的后脑勺。 “我也想她了。” 小李蝶低低地嗯了一声,而后安安静静地趴在梅先生的肩头之上。 推门声吱吱呀呀地,像是一首风雪里孩童哼唱的曲子一般。 关门的沉沉闷闷的。 像是中年老男人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