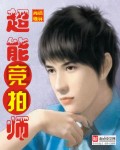少年在听见那样一声极为平静的带着询问之意的话语的那一刹,便径直握住了鹦鹉洲。 然而寒光之剑根本未曾出鞘,便被人按回了鞘中,分毫不能动。 南岛缓缓转过头来,身后不知何时站了一个很是平静的道人,少年在看见道人的那一刹那,便怔在了那里。 梅溪雨。 青天道梅溪雨。 当初在岭南的时候,南岛与青椒曾经在听风溪畔见过这样一个道人。 而后这个道人与陈怀风在岭南交手一番,带着许多的愤懑离开了南方。 只是少年大概没有想过,他会在这里再次看见这个道人。 当初人间的那些风声,南岛自然是有所耳闻的。 譬如青天道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背负上了瘸鹿剑宗灭门之事的罪名——尽管在最后,所有人都以为那样一个故事被安抚下来的时候,张小鱼跳了出来,正式掀起了那样一场两族的乱世。 只是少年大概没有在意过。 毕竟那样一些故事发生在北方,而他是岭南的剑修。 少年怔怔的站在那里。 梅溪雨很是平静的将少年身后的剑最后一寸,也完全按了回去。 于是少年再拔不出剑来。 南岛当然曾经与张小鱼打过。 只是那样一场战斗的含金量,大概懂的都懂。 “剑出鞘的声音是很硬朗的锋利的。” 梅溪雨收回手,站在那里平静的看着少年。 “在阴雨的沉寂的巷子,剑出鞘了,大家就会都听见了......” 这个道人顿了一顿,轻声说道。 “彼时你就真的走不出这条巷子了。” 南岛的手握在剑柄上,沉默了很久,而后缓缓松开来。 回过头去,那样一个黑袍人已经转回了身去,便在那条悬街之上,不知道在看着什么。 但无论在看什么,都不像是在看着这条的巷子的少年与道人。 南岛重新回过头来,沉默的看着这个站在巷子里的道人。 道人撑了一把伞,很是安静的站在巷墙边,长久的看着少年,像是在思索着很多东西。 一直过了许久,梅溪雨才缓缓说道:“原本从天狱那里听说那样一个撑着伞的很是可疑的少年的时候,我还很好奇,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少年。” 南岛皱着眉头,总感觉这个道人很是古怪。 梅溪雨并没有在意少年在想什么,只是如梦初醒般说道:“原来我见过你的,在岭南,那时还有一个穿着红衣的东海剑修。” 南岛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是的。” 梅溪雨听着少年的这个回答,又看着少年那很是复杂的神色,挑眉说道:“我怎么感觉你有些愧疚的样子?” 只是还没有等到少年回答什么。 这个道人便似乎想起来了很多东西,静静的看着少年。 “岭南与青天道向来毫无瓜葛。近年来唯一的一件事,大约便是那样一封自岭南零落阁送出的信.....” 少年听到这里的时候,便已经清楚,面前的道人终于明白了许多东西。 只是梅溪雨并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长久的安静的站在那里。 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些寄往远方的信,最后还是会落回少年自己手里。 少年沉默的站在那里。 他知道面前的这个道人其实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只是道人却是没有再提起那样一件事,只是平静的看着少年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南岛沉默了少许,轻声说道:“初来乍到,不小心走进来的。” 梅溪雨轻声笑了笑,转头看向巷外,也看着那些高层的悬街青檐。 “好一个不小心过来看看,天狱封锁了周边一切街巷,这也是不小心就绕过去的吗?” 南岛此时却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是的。” “就像当初那封信一样?” “是....的。” 南岛下意识的说着,顿了一顿,却还是完整的说了出来,抬头看着道人,道人脸上并没有什么情绪。 梅溪雨转身向着巷子里走去。 “其实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戴罪之人。” 梅溪雨也没有让少年跟上来。 少年自然只能跟上去。 那个道人在愈发昏暗的巷子里平静的走着。 “或者说囚犯。” 南岛沉默了少许,而后缓缓说道:“但我没有看见镣铐枷锁。” 梅溪雨回头看了一眼南岛,平静的反问道:“镣铐一定是锁在脚踝上枷锁一定是戴在脖子上的吗?” 南岛沉默了下来。 当然不是的。 “我的镣铐是脚下的石板,我的枷锁是九万贯的宅子。” 梅溪雨很是平静的说着。 “就像你在看见我的第一眼,肯定万般不能理解一样。我的镣铐枷锁过于宽广,于是我不得不被某些人驱使在其中奔走着,充当着许多工具。” “就比如现在,有人不知道抱着何种心思,犯了事不好好躲藏起来,反倒还要跑回来看一看,于是便需要有人来提醒一下他,你的剑不要出鞘,你的人不要出现。” 南岛怔怔的站在了那里,不知道梅溪雨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梅溪雨亦是停了下来,这条巷子深处很是寂静,只有一些绵密的雨声。 一直过了很久,梅溪雨才转过身来,向着巷外看去,这里的视线被两旁的巷墙与楼房悬街拦住了,于是再不能见到那样一个窥花之猿的柳青河。 梅溪雨收回视线,落在了那个伞下少年身上。 “你猜猜为什么柳青河柳狱主会站在那样一处悬街上看雨?” 少年沉默了很久,而后缓缓摇了摇头。 梅溪雨平静的说道:“他站在那里,你就不敢过去。不敢过去,便不会暴露出来。” 所以其实理由很简单。 只是为了让某个少年望而却步而已。 南岛骤然睁大了眼睛。 所以这样一个少年的到来,自然不可能瞒得过那样一个天狱之主,那一眼,也确实是在看这样一处巷子。 梅溪雨的声音依旧在巷子里很是平静的落下,像是雨水一样砸落在少年的脚边。 “你见过侍中大人?” 南岛沉默了少许,而后轻声问道:“没有。” 梅溪雨长久的看着这个少年。 南岛在漫长的沉默之后,说出了与某个书生一样诚恳的话语。 “尚书大人不是我杀的。” 梅溪雨平静的说道:“我当然知道不是你杀的。虽然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你,只是有些线索,过于刻意了。” 南岛皱了皱眉,说道:“是什么?” 梅溪雨轻声说道:“巷子里的剑意。” 南岛愣了一愣。 这个道人缓缓说道:“一个能够以踏雪境力敌五境剑修的少年,倘若面对一个垂垂老矣,毫无防备毫无护卫的世俗兵部尚书,还需要用上剑意.......” 梅溪雨说着与柳青河某句话极为类似的话语。 “大概这样一个剑修确实是烂泥扶不上墙的。” 当今剑修,依旧秉持着手中之剑不可久离的理念。 哪怕剑意之道再如何兴盛,终究任何一个剑意之修,在手中之剑上的造诣,都是不差的。 倘若少年真的想要杀人,大概会一如当初南衣河边一样,很是干脆利落的拔剑,无比平稳精准的刺进了另一个少年的心口,而后才是用剑意去摧毁那个一个少年剑修体内的神海。 少年长久的站在巷子里,什么也没有说。 梅溪雨却是有些好奇的看着少年突然问道:“你为什么最后没有拔剑杀人?” 这样一个问题或许也并不突然。 这个故事一切破绽的由来,便在于面前的少年没有拔剑。 于是有人不得不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杀死了那个兵部尚书。 南岛沉默了很久,轻声说道:“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梅溪雨安静的看着少年。 “什么问题?” “在南衣城与岭南面临着诸多困境的时候,槐都为什么选择了那样一种处理方式。” 梅溪雨并不觉得意外。 好像少年本就应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一样。 “那个老人当时看了我很久,或许也是猜到了我的来历与我的来意,而后平静的告诉我,这不是兵部能够决定的事。” 梅溪雨挑眉说道:“你便信了?” 南岛站在伞下淡淡的说道:“我当然不会信,只是有些东西确实很是古怪。” 少年眯着眼睛抬头看着远处渐渐昏暗下来的人间。 “当我在想着我应该去找谁的时候,有人便在不远处交谈着兵部之事,当我思索着兵部尚书会在哪里的时候,有人便在议论着那样一个老大人的所在。” 所以少年大概确实没有去什么很是特殊的地方,只是走到哪里,都好像有人在点明着方向一样。 倘若少年生命里没有发生过南衣河上的鼠鼠死亡的故事,少年也许真的会什么也不说,在巷子里直接拔剑出鞘。 只是有些故事,一如梅溪雨在走入这条巷子前都未曾知晓一般,对于世人同样是陌生的。 他们不知道,少年因为自己当初的那封信,悔恨过多久。 就像当初陈怀风在岭南与少年说的那段话一样——修行界与人间是不一样的。世人如果有仇怨,无非提刀而去,跨过几条街去,如果太远了,走到半路便冷静下来放弃了。但是修行界不一样,我们走得太快,从南衣城,到关外,像我们这样的人,倘若真的很急,点燃神海,也许都用不了一日。倏忽之间,很多仇隙来不及冷静,便成了人间动乱的根源。 所以少年有着愤怒的自由。 也有着冷静的自由。 杀人之前要磨剑,不止是为了剑更锋利。更是为了认真的想一想许多东西。 带着克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巷子里的少年很是认真的思考着。 那个老大人很是平静的告诉他,如果不信,可以去兵部看看,那里有着自大风历一千零三年开始到南方叛乱期间,所有被侍中大人驳回的用兵疏议。 少年其实依旧很犹豫。 毕竟哪怕兵部尚书再如何垂垂老矣,终究这是在槐都。 这些故事,或许只有一次机会。 只是看着那个很是坦然的站在巷子里的年迈的兵部尚书,少年最终还是没有拔出剑来。 南岛很是平静的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 “我又回到了那样一个巷子里,认真的看着人间看着自己的剑想着许多东西。” “只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兵部看一看,昨日见过的那个老人就死了。” 少年从怀里摸出来了一面令牌。 梅溪雨静静的看着。 那是兵部尚书的腰牌。 “所以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南岛静静的看着那块令牌。 “但却也很是后悔,后悔自己离开的太早了。” 少年沉默了下来。 梅溪雨大约也明白了少年的一些心思。 那样一个兵部尚书这样安稳的在槐都某些暗流里活了这么久,却被自己的鲁莽闯入,带来了一些破绽。 于是死在了巷子里。 少年终究是会有着一些愧疚的。 一如少年最开始看着自己的那一眼一样。 梅溪雨安静的看了许久,而后平静的转身继续向着巷子深处而去。 二人安静的走在雨水渐渐稀疏下来了的巷道上,谁也没有再说什么。 梅溪雨带着少年安静的穿过了许多槐都底部的街巷,在夜色落下的时候,停在了某处很是沉寂的短街处。 这个道人在那里站了许久,而后轻声说道:“是天狱的人杀了兵部尚书。” 南岛皱眉看着这个道人。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样一句话,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梅溪雨平静的说道:“天狱从镇鬼司演化而来的时候,那些天狱吏中的一些人所修之剑,便是来自陛下的教授。” “陛下是极为正统的人间剑宗剑修,一千年前的人间剑宗,依旧是修行的磨剑崖剑法。” 这自然是南岛也知道的事。 然而这个伞下少年并没有说什么,皱着眉头沉默着。 他只是突然想起了在东海的时候,那个自己一度以为是来自西门那边的天狱剑修。 梅溪雨依旧在看着长街缓缓说着。 “天狱自然不会是铁板一块,哪怕这样一个地方存在着极为严苛的自查体系。只是只要是人,便有走在不同河流的可能。” 南岛大约明白了许多东西。 “另一条河流,便是你们所说的门下侍中?” 梅溪雨平静的说道:“是的。” 少年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那样一个天狱之主,会长久的毫不遮掩的站在那样一条悬街上。 “柳狱主与我说过,许多东西,我们都是心知肚明的,然而那是没有证据的事,这样一个故事里,唯一证据确凿的,便是你曾在尚书大人死去的前后,出现在了这片街巷附近。” 这有一个黄昏里负剑执伞而行的少年,却是容易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梅溪雨转头静静的看着南岛。 所以少年不能拔剑,不能露头。 只要未曾被世人被某些来自巳午妖府的人看见,天狱便有理由,长久的将这件事情拖下去,直到某个人没了耐心,自己跳出来。 一如便在槐都南面的某处酒楼里。 那个天狱吏问的许春花的那个问题一样。 你会说不吗? 会说不,那就否认一切。 于是那条由许春花牵引而出的关于少年的线索,便可以长久的停留在天狱找不到许春花这个问题上。 这个来自青天道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的道人,此时却也是很是诚恳的站在那条短街的尽头,看向前方很是认真的给少年指着路。 “走出去,走进夜色里,找个地方安定下来,不要出来闲逛。” 梅溪雨很是认真的说着。 哪怕面前的少年是导致自己不得不在槐都戴着枷锁镣铐而行的罪魁祸首。 只是大概正如梅溪雨当初在吃那碗阳春面时所看见的一些人带来的意味一般——青天道,确实是与天狱,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尽管这样一个当初躲在山下镇外溪畔清修的道人并不能够明白许多联系的由来。 南岛长久的看着面前的道人,一直到过了许久,少年才站在夜色里轻声问道:“将这个故事拖下去,又能怎样?” 这个出来乍到的少年亦或者大多数世人,都无法理解槐都这样长久的凝滞的意味。 那代表着天狱全面掌控槐都之治,让巳午妖府彻底从这些故事里被割离出来。 对于某个巳午妖府的侍中大人而言,这当然是极坏的一件事情。 当然,更坏的事情在于。 “陛下就快回槐都了。” 梅溪雨平静的说道。 神河回到了槐都,一切便只能云在青天水在瓶。 南岛虽然并不明白这里面的诸多事情,却也是没有继续问下去,撑着伞向着短街之外缓缓走去。 那个道人在那里看着少年的背影,却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叫住了他。 “对了。” 南岛在夜色里转过身来,只见那个道人很是平静的说道:“李大人说的没有错。” “什么?” 梅溪雨缓缓说道:“确实是侍中大人驳回了兵部一切关于南方战事的决议。” 南岛撑着伞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深吸了一口气,轻声说道:“多谢。” 少年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 有时候在某些地方人人心知肚明的一些东西,却是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苦苦追寻的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