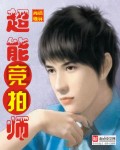张小鱼站在巷子里,抱着剑鞘歪着头看着这幅画面,觉得很是古怪。 哪有这样的剑客? 这个地方处处透露着不寻常的气息。 张小鱼沉默地想着。 不是诡异。 是不寻常。 就像有人在槐都建了高大的楼宇,最后却放了一张破木床一样。 张小鱼的脑子里有点混乱。 正想回头看看那个剑意大湖边的铁匠台。 却发现在自己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个一身青裳的少年,手里拿着个酒葫芦,正在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酒葫芦里的酒有股烧味,就像之前张小鱼闻到的那种味道一样。 “你是酿酒的?”张小鱼将目光从少年的酒胡芦上移开,看着少年问道。 青裳少年摇了摇头,说道:“我是喝酒的。” 张小鱼皱眉看着这个少年,想了很久,说道:“我感觉你有点眼熟。” 青裳少年笑了笑,只是说道:“为什么觉得眼熟?” 张小鱼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觉得眼熟。 于是如实地说道:“我也不知道。” 张小鱼很老实。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老实。 青裳少年也不说话,只是笑眯眯地喝着酒,看着他。 张小鱼看向巷外,问道:“这里是哪里?” 青裳少年想了想,说道:“小镇子,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子。” 张小鱼点了点头,说道:“那就是无名镇?” 青裳少年喝着酒向着巷外走去,平静地说道:“也可以叫做三绝镇。” 张小鱼挑了挑眉,说道:“什么三绝?” 总不至于是第一绝不意气用事? 青裳少年没有回答,只是站在巷子口回头看着张小鱼笑了笑。 正在炫耀自己的天下第一剑的汉子看见少年走了过去,看起来颇为自豪地把手里的扁鱼剑举到了少年面前。 “怎么样,草为萤,我这剑打得好不好?” 原来他便是汉子口中的草为萤? 张小鱼在巷子里若有所思地想着,看起来这个少年似乎在镇子里很是重要。 草为萤接过汉子的剑,把葫芦挂到腰间,随意地挥了挥,笑着说道:“很好。” 草为萤挥剑的动作很寻常,但是在巷子里的张小鱼却是怔了一怔。 回头看向那片大湖。 湖上有风正在缓缓平息。 像是方才那里曾经起过一场浩大的剑风一般。 再回过头的时候,草为萤已经停了下来,笑吟吟地把剑还给了汉子。 “下次给我也敲一把。” 汉子满口答应,满心欢喜地抱着剑走了。 张小鱼走出了巷子,青裳少年草为萤握着葫芦靠着墙壁,春日阳光从屋檐漏下来,照的那种微笑很是灿烂。 “那柄剑真的打得很好?” 张小鱼有些怀疑地看着草为萤,觉得他是在糊弄那个汉子。 草为萤看着那个远去的汉子的背影,却是很认真地说道:“真的打得很好。” “为什么?” 草为萤转头看着张小鱼许久,说道:“假如你刚开始打牌,尽管打得稀烂,但是还是胡了个屁胡,你觉得这是打得好还是打得不好?” 张小鱼沉默许久,说道:“那应该还是打得好的。” “就是这样。”草为萤笑着说道。 “所以镇上没有别的铁匠?” “没有。” “那那些断剑哪来的?” 草为萤回头看着那处大湖,轻笑着说道:“白捡来的,可能有人喜欢到处乱丢剑,但是丢了之后又找不到在哪里,于是便全留下来了。” 张小鱼看着草为萤的那个动作,一同看向湖中。 “全丢湖里了?” “全丢湖里了。” “.......”张小鱼沉默良久,感叹道,“也确实是一些人才。” 草为萤轻声笑着,握着酒葫芦向着街对面走去。 “总要慢慢来的,说不定以后他便是人间最会打铁的人,那些人也是人间最会丢剑的人呢?” 张小鱼在巷子里静静地看着草为萤离开的背影。 他觉得自己应该去猜一猜一些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过于惊世骇俗。 所以他没有敢去猜。 甚至也没有去问。 只是沉默地看着少年离开。 而后走回大湖边,沉默地看着那个新修建的铁匠台,又看着那一湖剑意之水。 “倒是难得看见师兄修行。”南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张小鱼回过头去,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听风台。 南岛撑着伞一瘸一拐地走上楼来,看着坐在台上的张小鱼说道。 张小鱼站了起来,回头看着楼外细雨人间。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总让他有些恍惚,哪怕看见了细雨,也一直以为在那外面竹林里,正有着春光缓缓流淌一般。 这种感觉让张小鱼有些惶恐,但他隐藏得很好,笑着说道:“毕竟大道也不是睡觉睡出来的。” 南岛想起来城头那个女子剑修说的张小鱼的故事。 “所以师兄除了打牌和睡觉,真的很少修行?” 张小鱼伸着懒腰,笑着转过身来,看着南岛说道:“在修啊,只是我藏得比较好,你想啊,我要是勤恳修行,才有现而今的境界,世人肯定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我要是终日打牌,然后在世人看不见的时候偷偷修行,他们一看你天天打牌都能这样,就会说卧槽!此子非人!” 张小鱼走过来,拍着南岛的肩膀,嘿嘿道:“这样是不是更有冲击力一点?” 南岛默然无语。 “师弟啊,修行的装逼之道,你还差得远呢!” 张小鱼背着剑鞘晃悠着走下楼去。 南岛站在楼梯口,看着张小鱼悠闲地走下去的背影,心里却是默默地想着。 这样确实是很好的。 但自己不是一个应该招摇的人啊。 不是吗? 南岛走到了听风台的边缘,把剑从身后解下,放在了膝头。 神海之中干涸的水洼正在缓缓地积着水。 桃花走到水洼边,低头向水洼中看去,于是水洼变成大海。 桃花站在入海的河道边,看向那棵正在缓缓开花的道树,而后转身向着遥远的某个大湖中看去。 那个小小的少年依旧沉浸在那些梦境之中。 桃花静静地看着那边。 是什么梦这样漫长却也平静? ...... 南岛行走在一片宁静的春日里,没有撑伞,像个普通的少年一样,提着一些吃的,打算去找几个朋友在树下吃吃喝喝一会,然后夜色降临时候回去。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南岛记得自己有次经过镇上的学堂的时候,听见里面的先生在教着一些东西。 大概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现在不正是一片暮春时候吗? 南岛抬头看着春日,想着今日应该是三月二十九? 春天快要过去啦! 不知道某个人的烦恼会不会随着春天的过去,也随之过去。 某个人又是谁呢? 南岛有些古怪地回想着自己方才那个想法。 难道自己曾经认识过一个人,在春日里感叹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南岛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于是把吃的抱在了怀里,走出了街旁树下的林荫,向着不远处的一个院子门口跑去,敲了半天门,才有人走过来开门,是个三十来岁的妇人,怀里抱着个娃娃。 “陈鹤在家吗?” 南岛看着那个妇人,总觉得有些古怪,但是想不起那里古怪了,好像记不得她叫什么名字了,真奇怪,自己在小镇上活了十来年,怎么会记不得了呢? 但是南岛没有多想,只是问了他要找的第一个朋友在不在。 妇人奇怪地看了南岛一眼,问了一句。 “你找谁?” “卖豆腐的陈鹤啊!”南岛说道。 妇人笑了起来,怀里的孩子也在咯咯笑着。 “你找错了,我们不卖豆腐,我家没有叫陈鹤的,也没有姓陈的。” 南岛歪了歪头,又退回去仔细看了好几遍,觉得自己应该没有找错啊。 “这附近应该也没有叫陈鹤的。”妇人又好心地说道。 南岛离开了那里,站在树下歪着头想了很久,难道自己真的找错了? 算了,先去找那个叫张小鱼的吧。 南岛把怀里的吃的打开看了看,很是诱人,最上面的是一只烧鸡。 烧鸡还是等人齐了再吃吧。 南岛边走边往下翻了翻。 嗯? 怎么有副麻将? 难怪这么重! 南岛将那袋麻将掏了过来,正打算丢掉,犹豫了一下,还是留了下来,然后随便找了个冷掉的糖油粑粑,一面啃着一面向着张小鱼家走去。 南岛走了很久,才走到镇西那里。 然后便得到了第二个不好的消息。 这里也没有一个叫张小鱼的。 南岛这一次没有纠结了,抱着东西,继续往南而去。 然而找到了下午的时候,依旧一个朋友都没有找到。 南岛坐在小镇的那条小河边,怅然地看着天边暮色。 原来自己一个朋友也没有? 真是奇怪啊,自己分明记得有的啊。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让他再回去找一遍了。 南岛便在黄昏河边,打开了那包吃的。 有酒,浸了桃花的酒,还有铁板豆腐,用个食盒装着的...... 南岛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搞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吃的,全塞在里面了,又看着一旁的那副麻将,南岛又往包袱里面掏了掏。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会从里面掏出一架轮椅来。 但是并没有发生这个古怪的事。 把东西摆好,南岛便在河边树下,吹着晚风,看着落日,对着一河波光粼粼,开始吃着东西。 不用撑伞的日子正好啊! 南岛突然这样想到。 然后又愣了愣。 撑伞? 抬头看了看天空。 什么傻子平白无故的撑把伞在那里? 南岛笑了起来,昨天下雨他都没有撑伞。 对了,昨天在做什么来着? 南岛想了很久,才想了起来,昨天出门买酒去了,他爹突发奇想,想要打会铁,然后打了没一会就哼唧哼唧地躺着说累了,让南岛去买点酒回来喝。 南岛虽然很想在后院躺着晒太阳,但是还是出门买了一坛酒,还偷偷私藏了一些,想着今日叫几个朋友一起出来喝酒玩。 但是谁也没有找到。 真奇怪啊。 南岛喝着酒想着。 身后却是传来了一些脚步声,踩着河边树下的叶子上,窸窣地响着。 难道是他们谁回心转意,决定不骗自己了? 南岛有些惊喜地回过头去,却发现来的不是陈鹤他们,而是一个穿着一身青色衣裳的少年。 南岛总觉得他有些熟悉,一直到少年在一旁坐定了,开始拿着自己的酒喝了,南岛才想起来他是谁。 他就是镇上学堂的先生。 像南岛这样没有去学堂启蒙的,也是认识他。 因为他太年轻了。 南岛已经记不得这个先生什么时候来的小镇了,总之当初他来的时候,镇上的人很是怀疑。 这么年轻,能教好吗? 但是后来人们便不再怀疑了。 因为他教得确实很好。 南岛先前想到的那句话就是在他口里听说的。 这个先生叫什么名字来着? 好像是叫草为萤? 真古怪的名字,还没有自己的南岛好听。 南岛还在想着,那个叫草为萤的学堂小先生已经把他的酒喝了快一半了。 南岛倒没有心疼的意思,只是觉得这样喝会不会把人喝出事?听说镇上很多人都还是挺喜欢这个先生的,万一真出事了,自家的铁匠铺也别想安宁了。 于是南岛赶紧从草为萤手里把酒壶夺了回来,揭开盖子看了一眼。 “你的朋友们都没来吗?” 草为萤却是擦着嘴角的酒水,看着南岛笑眯眯地说道。 南岛放下了酒壶,低头看着身前的一堆吃的,也没有在意草为萤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叹息着说道:“对啊,也不知道他们跑哪里去了,害得我一个人孤独寂寞的在这里看风景。” 草为萤轻声笑着说道:“那确实让人没办法开心起来了。” 南岛看着草为萤,见他也是一个人来的,好奇地问道:“你的朋友呢?” 草为萤笑着看向小河流水,缓缓说道:“我的朋友们都死了。” “死了?”南岛惊了一惊,“为什么?” 草为萤看着暮色河水,轻声说道:“生老病死而已,或许有些故事,但我记不得了。” 南岛拿着酒壶喝了一口,然后又给草为萤递了回去,说道:“不好意思,问起你的伤心事了。” 草为萤并不伤心,只是看起来有些惆怅,拿起酒壶又开始喝了起来。 “没关系啊。” 草为萤喝了一口酒,轻声说道。 “能够有人问起,也算是件好事,不然可能太久没人问,我都想不起来,原来我曾经也有过一些朋友。” 草为萤说着,却是顿了顿。 南岛看着草为萤,问道:“你在想什么?” 草为萤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我在想他们姓什么。” “......”南岛默然无语,“连姓什么都记不得了,想来应该有很多年了吧,难道他们是你幼年的玩伴?” “是的,有很多年了。”草为萤轻声说道,但是后面那个问题他没有回答。 二人在河边吃着东西,一面闲聊着,天边渐渐向那种橘子一样的色彩里沦陷进去。 南岛开始收拾着残局,把剩下的一些吃的打包好,又把二人推让了许久的一只鸡腿硬塞给了草为萤,把酒壶挂到了腰间,然后便发现一旁不知何时多了一把收起来的黑色的伞。 “这是你的伞吗?” 南岛拿起那把伞来,递向了草为萤,草为萤啃着鸡腿,含糊地说道:“不是我的,我来的时候它就在这里,难道不是你的伞吗?” 南岛挠了挠头,想着自己今天有带伞出来吗? 想了许久也没有想起来,低头看着这柄伞,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于是干脆夹在了腋下,白捡一把伞,也算是一点小收获? 二人离开了河边,向着小镇街道上走去。 学堂与南岛的家在一个方向,所以二人还要同路许久。 暮色里不知为何,却是渐渐有雨水滴落下来,南岛抬头看了看,想着还真是巧了,快要下雨的时候便捡到把伞,把夹着的那把伞拿了出来,正要撑开,然后便看见一旁的草为萤用着一种很古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少年的目光里有着很多的色彩,惋惜,遗憾,怜悯? 南岛怔怔地看着草为萤很久,说道:“怎么了?” 草为萤啃着鸡腿,转回头去,看着长街行人,稀疏穿过长街的路人里并没有几个开始打伞的人。 “你真的要打伞吗?” 草为萤如是问道。 南岛低头看着手中的伞,又抬头看着在那种昏黄的色彩里滴落的雨点。 “打伞有什么问题吗?” 草为萤轻声说道:“可能会有,比如你一打开这把伞,可能便再也放不下来了。” 南岛愣了一愣,而后笑了起来,说道:“先生真会开玩笑。” 撑着这把伞,你便再也不是个凡人,世间的情欲,你便不能再沾上半点。 怎么听都像是话本里的台词。 草为萤只是笑了笑。 于是南岛撑开了那柄伞,抬头看了眼暮色里的天边,向着草为萤靠了过去。 二人一同站在伞下,看着暮色。 “你看,我撑着伞了,什么事也没有啊,嘿嘿。” 草为萤只是笑着,然后从伞下走了出来,啃着鸡腿向着旁边走去。 南岛看着草为萤离开的身影,古怪地问道:“你要去哪里?” 草为萤没有回头的说道:“有些事情。” 南岛耸了耸肩,沿着来时的方向往铁匠铺而去。 草为萤走了一阵,便停了下来,低头看着手里拿个鸡腿,又看向南岛离开的方向。 却是在自言自语着。 “日后这小子会不会说我坏事做尽?” 那把伞确实是他带来的。 草为萤叹息着摇了摇头。 而后身影消失在小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