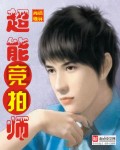姜叶看着卿相说道:“不错在哪里?” 卿相有些愤愤地说道:“这老小子不讲武德,来偷袭我一个一千岁的老人家,还好我会那么一点剑,顺手杀了曲岭,这小子转头就跑了,你既然杀了他,也算是帮我出了一口气,当然不错。” 姜叶沉默了少许,说道:“不是我杀的,我当然杀不了一个灵巫。” “那是谁?你有哪个师兄成大道了?” 卿相颇为好奇地问道。 姜叶低头看着怀里的那柄不眠剑,想了很久,缓缓说道:“是公子无悲。” 卿相愣了一愣,咂咂嘴,似乎有些不知道该如何说了,只是说着:“花无悲啊。” 姜叶看着卿相,想了想,说道:“但我确实不明白,公子无悲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只是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在问忱奴是不是想死的时候,忱奴没有回答?” 卿相歪着头想了想,说道:“你觉得花无悲是什么人?” 姜叶说道:“我不认识他。” 姜叶确实不认识公子无悲,不是所有剑宗弟子都像陈怀风那样被公子无悲拜访过。 卿相看向大泽之中,说道:“花无悲以前入大巫的时候,曾经带着花无喜来槐安到处走过一遍。” “这个我知道,师兄们打牌的时候说起过他。”姜叶看着卿相说道,“这能说明什么?” 卿相笑着说道:“你想一想,一个破了境,便开心地带着自己的弟弟到处去游山玩水的人,会是什么人?” 姜叶沉默了少许,说道:“我不知道。” 卿相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在山石上站了起来,而后走到了姜叶身边,缓缓说道:“不知道便不用再去想了,是怎样的一个人,也只是他自己的事。” 姜叶看着怀里的不眠剑,缓缓说道:“他杀了怀民师兄,也杀了另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剑宗老师兄。” 卿相回头看着姜叶,姜叶的年纪自然也不小了,过了三十岁,对于修行界而言,都算不上如何年轻的剑修。但是卿相作为一个活了一千多年的大妖,自然看谁都像小孩子。 所以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姜叶的头,而后在察觉到不妥之后,又快速地收了回来,背在身后一脸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模样,缓缓说道:“陈怀风也杀了柳三月。” 姜叶沉默了下来。 事实确实是这样。 卿相静静地看着人间,平静地说道:“人间杀人,当然是要承担罪责的。但是当修行界这种自称规则无视律法的存在掺和进来,很多故事便不能只看杀人来定好坏。” 卿相转头看着姜叶:“我们要看真相。” 姜叶沉默了少许,说道:“真相是什么?” 卿相耸耸肩,向着幽黄山脉北面走去,说道:“我不知道,我和他又不熟,只是听过一些他的事情而已。” 姜叶依旧站在那里。 卿相回头看着他,说道:“走吧,别想了,先回南衣城睡一觉再说。” ...... 张小鱼背着剑跳下了城头。 南衣城城防已经被那些北来的军队接手,便驻扎在城外青山之中,张小鱼自然也懒得再停留在城头之上吹风。 张小鱼背着剑,穿过了那些渐渐又有了些行人的街道,一身血衣自然黏糊糊的极其难受。 要不是现在路上有人,当众跳入河里洗澡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雅观,张小鱼都想直接跳进河里洗个澡再说。 好在路人们都是有些兴奋地在议论着城外之事,没有人上来打扰张小鱼,张小鱼便直接背着剑,穿过了街巷,向着悬薜院走去。 回剑宗太远了,一个城南一个城北,张小鱼也懒得踏剑风,人间自然要有人间的样子。 于是一路晃悠着来到了悬薜院门口。 梅先生正在门口扫着地,看见张小鱼倒是有些诧异。 “你不回剑宗跑这里来做什么?” “去湖里洗个澡。” “......” 梅先生虽然猜到了张小鱼肯定会干这种事,但是从他嘴里听到说出来,还是觉得很是无语。 张小鱼背着剑一路穿过玉兰林,走到湖边便愣住了。 草为萤便在那里笑眯眯地看着他。 张小鱼忽然觉得不洗澡,也不是那么难受。 只是来都来了,转身就走也不像话。 张小鱼只好背着剑尬笑着向着草为萤走去。 “前辈怎么在这里?” 草为萤看向那口在下午的阳光下格外平静的静思湖,笑着说道:“来这里坐坐,顺便看看人间。” 张小鱼哦了一声,在草为萤身旁坐了下来,觉得有些无话,想了想问道:“前辈来了多久了?” “大概你还在那座桥上祛除剑意的时候,我便来了。” 张小鱼愣了愣,说道:“原来这么久了吗” 草为萤只是笑着,没有说话。 张小鱼回头看着那些被斩得细碎的白花,猜测着应该便是南岛干的。 于是有些没话找话地说道:“南岛呢?” “哦,他先前跑过来洗了个脸,然后就回藏书馆了。”草为萤随意的说道,“你要不要洗个澡。” 张小鱼想了想,说道:“这样可以吗?” 草为萤笑着说道:“想洗就洗呗,我又不是谁家大闺女。” “......” 张小鱼最终还是洗了个澡。 当然没有脱衣服。 只是带着一身血衣跳入了大湖之中,大概是觉得有些羞耻,还沉入了湖底。 草为萤便在湖边托着腮,看着湖中那些弥散的剑意。 过了许久,张小鱼才从湖底钻了出来。 白衣之上的血色已经褪去,于是又变成了最初在人间晃悠着要打牌的张小鱼。 只是张小鱼似乎真的不准备打牌了。 从城头跳下来到现在,一个打牌的念头都没有出现过。 张小鱼踩着湖水走上了岸,一身湿漉漉地站在湖岸。 过了许久,却是取下了身后的剑,拔了出来,缓缓说道:“这柄剑应该是前辈送给南岛的?” 草为萤抬头看了一眼,说道:“不记得了,我那里剑太多,哪里记得住这么多东西,可能是的吧。” 张小鱼静静地看着剑上鹦鹉洲二字。 其实倘若单论剑。 这柄剑其实并不算得上是多好的剑。 问题便出在剑镡上的那三个字上。 落笔之间,尽是剑意。 才使得这柄剑一副寒光凛然的模样。 张小鱼沉默地看了很久,在湖畔坐了下来,把剑放在了膝头之上,看着那一湖隐隐有些血色的湖水,轻声说道:“其实我一直在猜测,前辈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草为萤微笑着看着张小鱼,说道:“所以你猜出来没有。” 张小鱼低头看着剑,缓缓说道:“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没有去猜了。”张小鱼抬手抚在剑镡的三字之上,轻声说道,“猜到了也是没有意义的,前辈的世界离我们太远了——人间人去猜天上人,哪怕猜得再如何准确,也是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草为萤轻声笑着,说道:“但总要大胆一些,去猜猜去看看,哪怕猜错了,也是没有关系的。” 张小鱼摇了摇头,说道:“不猜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问前辈。” “你说。” 无所事事的少年看着这个一身白衣坐在湖边阳光下的剑宗弟子。 张小鱼转过头来,看着草为萤:“前辈在人间,是要看什么东西?” 草为萤笑着说道:“当然是坐在人间看一些天上的东西。” 言下之意,自然便是人间之事,与他无关。 张小鱼转回头去,缓缓说道:“原来如此。” 草为萤微笑着看着张小鱼说道:“你好像有些怕?” 张小鱼轻声说道:“当然怕,虽然也许前辈曾是晚辈的某个师祖辈的存在,但是终究中间不知道隔了多少岁月,师祖也未必不能成为敌人。” 张小鱼抬头看着天空,依旧在想着那次进入那个小镇,在镇外看见的那个凝练成为湖水的一湖剑意。 “如果真是那样,我不知道人间该怎么去做。” 草为萤只是看着湖水,很是平静地说道:“所以有时候你会很犹豫,因为你不如另一些人大胆。” 张小鱼蓦然回头看着草为萤,而后沉默下来,重新转回头去。 这次的沉默是极为漫长的。 因为草为萤的那句话。 过了许久,张小鱼才轻声叹息着说道:“也许是的。” “你在南衣城待太久了。”草为萤平静地说道,“所以你眼睛里总是会看到更多的人间。” 张小鱼似乎不想再说下去,站了起来,带着一身湿漉漉的水汽,在穿过了玉兰林洒下来的阳光下向着回廊那边走去。 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弯腰将那柄鹦鹉洲递给了草为萤。 “前辈你的剑。” “送你也可以。” “南岛呢?” “我另外给他一柄剑。” 张小鱼似乎有些心动,但是犹豫了少许,还是放下了那柄剑,沿着小道走去。 “还是算了。” 草为萤也没有强留,微微笑着看着张小鱼离去的背影,似乎有些欣赏之意。 直到那个湿漉漉的白衣身影离开了静思湖边,草为萤才看向了那柄剑。 抬手拿了起来。 长剑被握在青裳少年手中,整个大湖却是蓦然起了无数剑风。 而后又缓缓平息了下去。 草为萤静静地看着这柄在城头被张小鱼拿着杀了很多人的剑。 “你怎么这么犹豫呢?” 草为萤轻声说道。 剑上的犹豫自然是极为愚蠢的。 用剑之人本身便是在行险招。 因为剑能伤人,也能伤己。 草为萤看了许久,把剑放了下来,插在了一旁的湖畔泥土之中,等待着某个同样无所事事的少年来取这柄剑。 ...... “师兄打牌吗?” 张小鱼离开了悬薜院,走在阳光灿烂的南衣城街头的时候,突然从一旁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 张小鱼下意识地就想说来。 只是才张开了口,便沉默了下来,转头看着在街边某个牌馆里探出的那个熟悉的牌友的脸,笑了笑,说道:“算了,不打了。” “怎么不打了?正好师兄你也战斗了这么久,正好打几圈休息一下。” 那人笑嘻嘻地招揽着。 张小鱼转回头去,向着长街前方走去,平静地说道:“戒了。” 那人似乎还试图劝说着,张小鱼却是头也不回的走远了。 那人在窗口摸着头,有些不解。 整个南衣城谁不知道张小鱼牌瘾贼大? 真的说不打就不打了? 张小鱼伸手在怀里摸着那一张红中,平静地走在长街之上。 当然不打了。 昨日在街头与鼠鼠说完那番话之后,张小鱼便真的不打牌了。 张小鱼摸了很久,把手从怀里拿了出来,沿着长街很是闲适地走着。 随着南衣城外的那些黄粱之人的暂时退却,南衣城中又开始热闹了起来。 人间热闹,牌馆喧嚣。 一切又都在大风历一千零三年的四月第一日下午吵闹了起来。 张小鱼只是安静地走着。 这虽然只是暂时的。 但是依旧是美好的。 有许多的受了伤的岭南剑修在街头走着,大概这也是他们要从凤栖岭下来的原因。 那个一心想要把南岛拐去岭南的女子剑修陆小小也在街头走着,腹部的伤口大概是找了城里的医馆重新包扎了一下,看起来整洁了许多。 陆小小正在街边抱着剑闲逛着,四处张望着,不知道是在找些什么。 也许是想偶遇一下南岛? 张小鱼这般猜测着,但是没有去问,只是停在那里看了一会,便继续向着前方走去。 一直到城中心。 那片墓山大河的所在。 张小鱼远远地看着墓山之巅的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却是笑了笑,而后穿过了那条大河,在阳光下碑影斜斜的山道上往上而去。 “小鱼师兄你掉河里了吗?” 还没走到山顶,张小鱼便听见胡芦的声音在上面传来。 “......”张小鱼有些无语地看着在山顶像个小和尚一样的胡芦,恶狠狠地说道:“小胡芦你再乱说,小心我把你推河里淹死。” 小少年胡芦娃毫不畏惧的说道:“那我就叫怀风师兄把你也推河里淹死。” 张小鱼默然无语。 推河里淹死自然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打一顿还是有必要的。 张小鱼走了上去,提着胡芦的衣领,就给他胖揍了一顿。 “出息了是吧,昨天还偷偷背着剑想上城头了?” 胡芦挣扎着说道:“我可是比那些很多岭南剑修都厉害的!” “他们是四十岁,你是十四岁,厉害有锤子用。” 张小鱼手下却是没停过。 陈怀风也没有阻止,只是在一旁笑呵呵地看着。 张小鱼比胡芦大了十一岁,动动手还可以接受,陈怀风就大得比较多了,自然不好动手,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会阻止,甚至还有点想加油助威。 一直到揍得差不多了,陈怀风才假惺惺地说道:“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张小鱼停下手来,把胡芦丢到了一旁,看着陈怀风,却是愣了一愣。 “师兄你剑呢?” 陈怀风平静地说道:“公子无悲在城里,我的剑在那边。” 张小鱼沉默了少许,回头看着人间,日头正盛,南衣城人来人往,却是没有看见那个年轻人与枸杞剑的踪影。 “要去看看吗?” 张小鱼缓缓说道。 陈怀风平静地说道:“我已经让胡芦去见过他一面了,有些话让胡芦来说,也许更为合适。” 比如如果他想干坏事,就让丛刃来揍他的话。 无论是张小鱼还是陈怀风,说出来总归是容易让人嗤笑的。 但是小胡芦来说却是幼稚得刚刚好。 “他来做什么?”张小鱼却是有些不解。 陈怀风沉默了少许,说道:“不知道,但是现在既然管不了,那么自然先不管他。” 张小鱼看着陈怀风许久,轻声说道:“看来师兄正在忙着破境。” 陈怀风笑了笑,说道:“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忙着破境。” 忙了七年了。 只是有些东西,倘若天地根不大。 那自然只能靠岁月的累积。 所以活得久的人,自然会更强一些。 只可惜世人活来活去,依旧囿于百年寿数之下。 张小鱼没有说什么,陈怀风却是看着他说道:“你呢?” 张小鱼看向南衣城长街短巷,看着某些重新热闹起来的牌馆——压抑了几日之后的报复性打牌。 “师兄是说我的剑,还是什么?” 陈怀风轻声笑着说道:“二者都有。” 张小鱼靠着一旁的某块墓碑,随手摘了朵小黄花在手里晃着,说道:“如果师兄是问我之前用的剑,我已经还了回去。” “别的呢?” 张小鱼轻声说道:“我也不知道。” 陈怀风没有追问下去,只是摸着自己怀里的东西。 那里除了一帘风雨道术。 还有一样东西。 一张红中。 那是陈怀风时隔多年重新出现在南衣城视野中的时候,顺手从门房的牌桌上拿的。 陈怀风想到这里,突然便觉得有些好奇。 那一副麻将少了一张红中。 师弟他们是怎么继续打下去的? 假如刚刚好要胡红中了,结果听了半天牌,发现这副牌里只有三张红中。 会不会气得掀桌子? 陈怀风看着在墓碑边靠着的张小鱼,却是少有的恶趣味地想着。 张小鱼到时候要是发现少了一张牌,会不会也会气得掀桌子? 陈怀风觉得这大概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所以他没有将自己怀里有一张红中的事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