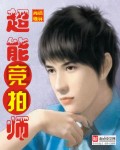人间春光明媚。 哪怕是残破的,被打碎了,不知道有多少世人葬生于其间的东海人间。 那种和煦温暖的阳光洒落在那些青山间,却也隐隐让他们有了一种安宁的色彩。 落叶从枝头坠落着,带着如雾如霜的露水,然后砸落成为了一些灿烂的光点。 而后被一双小小的鞋子踩在了上面,发出一些窸窣的声音。 小小的鞋子上面是一身小小的轻盈的小裙子,然后是一张很是安静的小姑娘的面孔。 小姑娘一路翻过了青山平原,终于在晨曦落向人间的时候,站在了某座最靠近的海的青山之上。 当春风拂面而来,一些躁乱的气息都被掩盖了过去,吹得小姑娘的短发像是朵蓬松的蒲公英一样纷乱地飞着。 丛心脸上终于有了一些笑意,好像便在身后的,便在先前的那些故事,被尽数遗忘了一般。 这个历经了千年,才终于肯从南衣城来到东海的小姑娘并拢着双腿在山上的某棵开满了白色的花的树下坐了下来。 当丛心在树下坐下的时候,那些白色的花便开始带上了许多的色彩,像是素面白净的女子,清晨想着要见心上人,于是便开始梳着状,擦着脂红一般。 于是桃花便开了。 在那些春风里,纷纷扬扬地落向人间。 于是小丛心便长开了。 从一个小小的人间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梳着两条黝黑的辫子,眉眼如画的女子。 春风是向着人间吹的,然而那些桃花却是在不断地向着那片广袤的东海飞去。 像是要飞越那些漫长的,有着四十九万里的辽阔大海,落到当年那样一个白衣剑修死去的地方。 丛心笑吟吟地看着那片大海与那些飞向远方的桃花。 只是眼眸之中,那些笑意之下,却是有着盈眶的泪水。 春风吹了很久,这个像是桃花一样的女子褪去了鞋子,站了起来,白生生的小脚便踩在了那些落满了桃花的山岭之上,而后提着鞋子安安静静地走在这片东海人间,一直向着那片海岸走去。 身后桃花不住地落着。 就像一些泪水一样。 “一千年了,桃花开了也谢了呀。” 桃花谢了也开了呀。 你在丛中笑吗? ...... 清晨的时候。 镇子里的人们看着那些散去的云雾,也看着那些随着星光一同落下的剑光,终于放下了那颗忐忑的心。 只是人们来不及看着那些被某两个剑修大战了一场变得满目疮痍的人间有着什么感叹,便惊诧地看向了那处高崖。 高崖之下,有着一个背着剑的小少年长久地保持着一个姿势,安静地仰头看着那处漫长的剑阶。 而那些云雾涌动的山崖之间,有着无数剑意正在翻涌着。 人们惊讶地看了很久,而后纷纷围了过去,远远地站在了那个小少年的身后。 那只是一个知水境的小剑修。 然而在这样一个令世人仓皇的故事结束之后,一个突然出现在崖下的剑修,自然很容易让世人想到某些很是玄妙的故事。 也许知水不是知水呢? 于是有人看着那个仰头看着高崖的小少年,大声的问道:“你要上崖吗?” 小少年过了很久才回过头来,看着那些不知何时已经在自己身后那条清溪之后拥挤的小镇剑修们,而后很是平静地摇着头。 “我不上,但是我师叔正在上崖。” “师叔?” 镇上的人们的目光落向了那些云雾之间剑意翻涌之处。 那些翻涌的地方确实正在缓缓的上移着。 “那是千丈之下吧,你师叔走到这里就已经这么慢了,大概是上不去了。” 那些小镇里的剑修与世人们纷纷地说着。 “他当然上得去。”小少年认真地看着那些人们,又转回了头去,继续仰头看着那一处高崖。“因为师叔不一定要是年纪很大了,饱经风霜了的中年男人。” 人们惊奇地看着那个小少年。 “那你师叔多大了,和那王八蛋张小鱼一样大?” 小少年轻声说道:“十六岁。” 人群之中一阵哗然。 人们自然不会相信。 “那你们是哪里的剑修?流云剑宗,人间剑宗?” 有人看着小少年仰着头的背影问道。 “都不是的。” 陆小二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便低下了头,转过身来,从身后取下了溪午剑,执剑一礼。 “岭南天涯剑宗,陆小二。” 人们神色古怪地看着那个少年。 所以是岭南的人? 当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岭南的人不能来登崖。 事实上年年都有岭南的人来过来,尤其是在前些年,岭南有着八万剑修的时候。 那时人间安宁,磨剑崖下剑修如流。 只不过往往都是停在了一千丈下,便狼狈地滚落了下来。 所以人们在听见岭南二字之后,便换了一种惊叹的神色。 “岭南的人啊,能够走到这里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诚心诚意的称赞,只是无论如何,大概都有些像是讽刺一样。 但是那些说着这样的话的人眼眸之中的神色,自然是无比认真而诚挚的。 陆小二沉默了少许。 岭南自然是这样的。 除了一些值得被称颂的品质,他们一无所有。 只是小少年还是认真地说了一句。 “岭南会好起来的,师叔也会走到很高的地方的。” 这些东海的剑修们自然不是很相信这样一句话。 只当是少年的梦罢了。 在弄清楚了少年的来历之后,人们便越过了清溪,一同来到了崖下,抬头张望着那些云深不知处的剑阶。 磨剑崖便在人间,只是人间却极少有能够见到这样一座高崖真容的存在。 是以无论何时去看,崖下的人眼中永远有着好奇与憧憬。 “你师叔什么境界了。” 有剑修拍着小少年的肩膀问道。 陆小二轻声笑着,很是自豪很是得意。 少年最得意,大概便是谈及自家师叔。 “踏雪斜桥。” 原本有了些热闹之意的崖下人间,又沉寂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向着这个小少年看了过来。 “岭南的剑修?十六岁,踏雪斜桥?” 有人哂笑着。 “小少年你不要开玩笑。” “人间剑宗的那个叫做胡芦的少年,都没有这种境界吧。” 有人说着,便突然想起了什么,眸中渐渐有了一些很是惊异的色彩,睁大了眼睛看着陆小二。 “听说今年一月的时候,有个岭南少年剑修在南衣城差点将胡芦一剑送走。” 那人怔怔地看着小少年,又抬头看着那处高崖。 陆小二诚恳地说道:“便是我师叔。” 留在东海小镇的剑修都是沉默了下来。 一时之间不知道是夸那个少年好高的天赋,还是夸他好大的狗胆。 那些从一开始听到了岭南之后便觉得希望渺茫的人们,此时倒也是觉得少年登崖之事不是那么荒唐了。 至少,一千丈。 也许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 人们安静了下来,与小少年一样仰着头,长久地看着那些云雾里不断翻涌着的剑意。 “那是八百多丈了吧。” 有人不无惊叹地说道。 自己十六岁在做什么呢? 练着剑?看着山? 还是看着小镇里的那些剑炉,畅想着有着某一日,世人也会记住自己的那柄剑上的名字? 一众剑修的目光都在默默地跟随着那些翻涌的剑意缓缓向上而去。 然而那些剑意却在九百丈的时候,突然停止了下来。 人们心头一紧。 难道人间踏雪斜桥,都不足以踏上千丈? 陆小二亦是沉默了少许,而后看着众人认真的解释着。 “师叔一路走过来很累了,所以他也许需要休息一下。” 人们看着陆小二。 “很累,为什么?” 陆小二轻声说道:“因为他是从白鹿妖族战场走过来的,而且......” 陆小二的话并没有说完。 因为他要说的话,被另一个人接了过去。 “他和我打了一场。” 陆小二听着那个很是熟悉的声音,蓦然转过头去。 一个一身带血,蒙着眼睛裹着耳朵背着一柄带血之剑的白衣剑修安安静静地站在了那条崖下清溪的上游,静静地抬头看着那座高崖。 “张小鱼.....” 陆小二怔怔地喃喃道。 世人一开始还没有认出这样一个无比狼藉的剑修,直到陆小二的话语坠落在了风里。 人们才惊诧地看向了那个搅动了整个大风历一千零四年风雨的剑修。 张小鱼在当下人间,自然是见不得光的,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间的人。 只是这里是磨剑崖。 崖上的女子自然可以一剑将他送去冥河。 然而谁都知道,磨剑崖不问世事,已经千年了。 所以哪怕那个剑修带着一身凄惨的血色,带着那幅狼狈的模样,出现在了这里,亦是没有一剑自高崖而来。 于是只有小镇有愤怒的剑修提剑而出。 “张......” 那个成道境的剑修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名字都没有说出来,便被一道剑意掠过了喉间,捂着喉咙倒了下去。 “你们知道的,我现在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就容易滥杀无辜。” 那个剑修安静地站在那里,转过了头来,那只血色干涸之后像是一朵黑红色的花一样眼眶,毫无情绪地看着众人。 “所以你们最好安静一些。” 一众镇上的剑修都沉默了下来。 那个当初南衣城嘻嘻哈哈的小道境剑修,现如今已经是五叠剑修,哪怕再如何狼狈地站在那里,亦是有如渊渟岳峙一般,拦住了人间的春风。 陆小二亦是沉默了下去。 所有人都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转回了头去,抬头看着那处高崖。 只是那个白衣剑修的那般模样,与他最开始的那句话,无疑给这些剑修们极大的震撼。 所以那个少年,当真在东海与这个五叠剑修打了一架,才会那么疲倦? 张小鱼并没有在意世人们在想着什么,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哪怕他可以听见风声,同样也是看不见那样一个少年在剑阶上做着什么。 人间风声勾勒一切。 然而高崖人间风声不可入。 所以那些云雾对于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白衣剑修只是静静地站着,也在静静地想着。 你既然一定要往前。 师弟。 那就要承得起世人的仰望。 要么被捧到高处摔死。 要么。 就跳出命运。 所以这个白衣剑修出现在这座高崖之下,是要带来什么? 是一个天下三剑的名头。 今日之后,世人便会知道,那个少年与张小鱼打了一架,打烂了张小鱼的眼眶。 ...... 世人自然不知道那个少年为什么在那里停了下来。 张小鱼也不知道。 这样的事,只有某个崖上女子,与那个少年自己才会清楚。 少年停在了那处九百丈的剑阶之上,身周有剑意流转,而手中空空如也。 那柄伞已经被放下来了。 就在脚边。 南岛神色复杂地看着那柄伞,也抬头看着人间天穹。 没有风雪。 人间没有风雪降临。 就在某一刻,这个一路执伞面对着剑意登临而去的少年,心中蓦然有了一个很是古怪的念头。 他知道这样的想法很是危险,也很是疯狂。 只是他还是在漫长的沉默之后,弯下腰来,将那柄伞放在了地上,而后抬头看着那些云崖之外的天穹。 春光烂漫,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像这样一个少年,从来都不需要撑着那样一把伞一样。 只是分明人间没有雪,少年肩头却好像满是风雪一样,压得少年直不起腰来,只能双手撑着膝头不住的喘息着——这是一个人间很是常见的肢体动作,但是南岛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这样,是什么时候了。 他五岁的时候,便开始撑着伞,像是一个黑色的蘑菇,安安静静地蹲在檐下。 南岛一直喘息了许久,才终于缓过气来,重新站直了腰,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抬头像是看着高崖也像是看着天空。 云雾是翻涌的缠绵的,但是眼前终于没有了那样一抹黑色,藏在了眼眸的边缘,遮蔽着许多东西。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少年想要不打伞,便只能留在这样一座崖上枯守一生吗? 南岛不住地问着。 他也不知道要问谁。 分明没有伞了,只是少年的呼吸却越发的艰难起来。 南岛一直用了很久,才终于平息下来,什么也没有说,弯下腰去,重新捡起了那样一柄伞,默默地穿过那些已经足以在身上留下深深浅浅剑痕的剑意,向着崖上而去。 你不是来登崖的,南岛。 你只是,来见先生的。 ...... 秋溪儿沉默地站在剑阶之上。 当少年放下伞的那一刻,这个白裙女子亦是怔了下来。 看着那些满崖的剑意,与少年伞上那些若有若无的剑意,这个白裙女子好像明白了很多东西。 有些人,也许生来便是应该在崖上的。 那个曾经在某个青裳少年的天上人间里数次迷茫的看着一切的少年,也许才是真正的,磨剑崖的传人。 是的,崖上的传承,在红衣之后,便断了。 而有人被某个白衣剑修,带去了青衣的三弟子那里。 所以自己的剑为什么叫做故里呢? 那是秋水吧。 ...... 春光灿烂,春光明媚,春光迷人,春光沉醉。 在小楼饮了一夜酒的卿相,从楼边站了起来,拿起了身旁那些已经空空如也的酒壶。 当我满是痛苦的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也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卿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样一句话。 大概是两手空空这样一个词,出现了太多次吧。 于是卿相站在楼边,看着那些一地零落如血的红梅,拥抱着满楼春光。 这个白衣书生很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而后踢醒了一旁喝了一些烈酒正在沉沉睡着的云胡不知。 年轻的书生揉着眼睛晃着脑袋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抬头看着自家先生。 卿相凭栏微笑着。 “春天真好啊,可惜没有钱,朋友也死了,那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反贼吧。” ...... 胡芦醒过来的时候,在那里发了很久的呆。 剑宗里就像是被雪埋了一般的沉寂,什么声音也没有。 但人间哪有雪呢? 人间春光明媚,人间春风温柔。 但人间并不温柔。 瓜皮头的少年在溪桥上坐了起来,长久地茫然地看着人间天色。 清晨的阳光正在斜斜地穿过那棵开得无比旺盛的桃树落下来,有着许多的桃花落在了少年的肩头。 梦里花落知多少。 人间花落知多少? 那些一切的繁华热闹似乎还在耳边,但是眼前所见的一切却都是寥落的了。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 梦里青草香。 胡芦突然低下了头去,无比悲伤地哭着。 那些悲伤的哭声惊动了留在了剑宗里的江河海,这个七境的师兄匆匆跑了过来,独自站在了一池的小道上,看着那个泣不成声的少年,也抬手抹着眼泪。 “师弟,你终于醒了。” 于是少年的哭声更大了。 谁愿意听见这样一句话呢? 为什么是你终于醒了,而不是你是在做噩梦呢? 那种满是悲伤的哭声响彻了整个园林。 于是成为了这个千年剑宗里,唯一的喧嚣的热闹的繁盛的声音。 ...... 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 第二卷,剑中人。 完。
- 首页
- 最近阅读
- 快速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