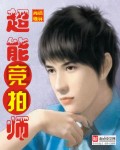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样的事,当然并不少见。 大理寺的人将祝从文带走监押了起来,当然也不是真的要对这样一个书生动手。 只是有人大荒星陨开团,他五级大聪明闪现跟团而已。 兵部尚书之死并没有过去多久,只是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被天狱与巳午妖府的交锋盖过去了而已。 现而今随着天狱一些调查的水落石出,这样一个故事自然重新回到了世人的视线之中。 而大理寺接下来的那些动作,也由不得他们不得不去想着那些东西。 巳午妖府有不少人被带去大理寺。 而相对之下,本应该对天狱进行反击的巳午妖府,在那之后,却是突然沉默了下来。 如同天狱那些含糊其辞的否认极为有理有据一般。 只是随着朝堂之上一些故事的流出,侍中大人早就离开了大风朝决议中心之事,也终于被世人所听闻。 一时之间,人们面对那样一处与兵部尚书之死脱不了干系的巳午妖府,渐渐也大胆了起来。 大理寺卿余庆年听着人间巳午之时,在雨中那些街头的议论声,自然也有些惆怅。 倒不是不想听见那种声音,只是不想在大理寺附近听见这样的声音。 终究那还是当今的侍中大人。 陛下没有回来,哪怕天狱也无权处置那样一个人。 除非哗变。 但倘若槐都想要哗变,在兵部尚书仍在之时,这样的事情便已经发生了。 而不是一直拖到现在。 祝从文被关在了大理寺牢狱之中,不厌其烦地说着过去的许多事情。 他也不知道大理寺的人究竟要听多少遍,才能够相信他说的那些故事确实是真的,他只是一个被无辜卷入的书生而已。 在终于应付完了那些刑部与大理寺的盘问之后,祝从文终于可以安静地待一会了。 只是书生还没有在狱中歇息多久,那些大理寺的吏人便又来了。 不过好在这一次总算不是提审了。 他们还带来了一个人。 用保温的食盒装着一碗书生很爱吃的面的顾小二。 在送走了那个奇怪的吃面的道人之后,顾小二想了想,烤干了衣裳,认真地下了一碗面,装了起来,向着大理寺这边而来。 在巷子里吃面与在牢狱里吃面,总归意味是不一样的。 祝从文看着在牢外坐下,正在那里打开食盒,将分装的面与汤倒在一起的顾小二,有些惆怅地说道:“我都没有想到顾哥你还会来给我送面吃。” 顾小二在那里放着臊子搅着面,而后把面递了进来,认真地说道:“因为我想了想,那样一个傍晚时候,吃的那样一碗面,总让人感觉像是断头饭一样,太不吉利了。” 祝从文接过了那碗面,人间固然大雨,只是终究不是寒冬腊月,这一碗面倒是还没有凉,书生想到没有凉的时候,也被顾小二带得有些胡思乱想起来,没有凉是好事,面没有凉,那自己也没有凉。 面不止没有凉,而且还没有坨,毕竟顾小二考虑到大理寺离面馆很远,所以面汤分离带来的。 书生很是感动地吃着那一碗面,却也颇为不解风情地说道:“难道在狱里吃一碗这样的面,就不像断头饭了?” 顾小二诚恳地说道:“当然不算,因为我后面还会给你送面来吃。” 祝从文吃着面,喝着汤,想了想,说道;“外面怎么样了?” 现而今已经是下午了。 人间的风声也吹了很长的一些时间了。 趋势如何,自然也该有些分晓了。 顾小二听到这里的时候,却是沉默了下来,默默地看着祝从文很久,而后轻声说道:“你先吃面吧。” 于是祝从文便已经猜到了许多东西了。 侍中大人或许确实无力回天了。 这一处牢房里便只剩下了沉闷的吃面的声音。 祝从文沉默地吃完了那一碗面,而后将面碗放在了一旁,盘坐在那里,默默地看着牢房外的顾小二。 顾小二想了很久,而后轻声说道:“其实你也不用过于担心,毕竟你确实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没有罪名,哪怕侍中大人真的倒台了,你也不会受到什么很是严苛的刑罚。” 顾小二想了很久,书生也沉默了很久,而后叹息一声说道:“我当然也知道我死不了。哪怕现在在牢里坐着的是我,而不是他。只是......” 祝从文很是诚恳的看着顾小二。 “很现实的与你讲,我只是担心我以后,是不是会因为这样一件事,导致一生的轨迹都被改变了。你也知道,与一个世人乐见倒下的侍中大人扯上了关系,说到底,不是一件好事——我不想一辈子真的只能在面馆里做一个小二。我只是担心我的前途。” 顾小二沉默了下来。 对于一个干了一辈子小二的人而言,这样的一些话,或许确实有些伤人。 只是对于这样一个自幼苦读,出身于悬薜院的书生而言,倘若只能做个小二,大概同样是伤人的事。 虽然未必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但总归对于书生二字,算得上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就像黄粱的那个书生一样。 在修行界的故事里,那个叫做青悬薜的书生固然是天命之人,只是在人间的故事里,大概也只是一个对功名求之不得的人而已。 顾小二沉默了很久,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长久地叹息着。 这个面馆小二其实还想问一问书生,他第二次去巳午妖府又是为了什么,只是大概到了这里,也没有问的必要了。 他曾经也想过在路上捡到黄金万两,才能有着足够的底气,去大大方方地与某个心中的姑娘说着许多东西。 顾小二收起了那些面碗,提起了食盒,站了起来,看了书生许久,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确实说不出什么能有用的安慰的话来了,于是向着牢外而去,走到一半,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着书生嗫嚅了很久,才轻声说道:“明日我再给你送面来吃。” 这大概就是顾小二的安慰了。 祝从文轻声笑了笑,说道:“好。” ...... “不可否认的是,在你出现之前,我确实想过去天工司一趟。” 水在瓶撑着青伞,站在那处长街里,静静的看着雨里撑着伞的柳青河。 皇宫之下,确实便是那样一处极为浩瀚庞大的司衙所在。 水在瓶出现在这里,自然不止是为了看一眼这座宫城。 那指间白发一剑,轻而易举的破开了水在瓶的一身妖力,然而却连这个天狱之主的一身黑袍,都没有能够吹动。 一切都沉寂在了那些如渊似海的剑意里。 就像风吹进了风里。 柳青河只是微微一笑,说道:“哪怕你去了天工司,也不会有什么办法,相反的,如果你真的在天工司闹出了什么动静,水在瓶。” 这个天狱之主的神色平静,没有称呼侍中大人。 “你便是往后千年,人间最大的罪人。” 水在瓶沉默的看着远处某一条在迷蒙的雨中,向着下方斜去的巷子,穿过了那里,便是向下而去的悬街,走过了那里,便是人间别有洞天。 或许也是另一种命运。 可惜那样一个道人的到来,改变了许多东西。 低估了这样一个天狱之主的,又何止是人间。 水在瓶也是一样的。 这位侍中大人没有再说什么,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而后轻声说道:“到这里,故事确实已经结束了。” 柳青河温声笑着,说道:“或许是的,但是也许还没有,我给了你一个故事,让你去证明自己。” 水在瓶有些诧异的看着柳青河,后者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转身在雨中而去。 走了很远,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回头看着那场雨里迷蒙而模糊的一抹青白色。 “依旧是云在青天水在瓶?” 那位侍中大人只是轻声说道:“是的。” 云在天上。 水依旧在瓶子里。 水在瓶撑着伞静静地在那里看了许久。 人间的故事或许确实很是匆忙,已经下午时分了,这位侍中大人依旧看见了一脸愁容地从宫中殿议回来的诸位大人。 各部尚书与尚书令中书令那些朝中诸臣大概也没有想过,会在这里看见水在瓶。 尽管有些故事所有人心知肚明,只是水在瓶终究依旧是门下侍中。 是以众人还是走了过来,与水在瓶见礼而去。 水在瓶神色平静地与众人回了礼,待到他们快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侍中大人很是平静地在雨里说了一句话。 “黄粱此次退兵,不会再越过大泽而来了,接下来,槐安只需要提防叛乱的悬薜院与人间妖族之事即可。” 暂任兵部尚书的右侍郎回头很是惊诧地看着那个雨中的侍中大人。 一众人自然都是不知道水在瓶为什么突然会在这里说起这样一件事。 他们或许以为这个门下侍中在那里离开了皇宫之后,便已经无心关注这些人间之事。 只是许多故事,自然并非如此。 门下侍中,自然永远是陛下的门下侍中。 巳午妖府,也永远是槐安的巳午妖府。 水在瓶哪怕再如何偏执于那样一个少年之事,只是这个说着月色洒落,说着人间千年的门下侍中,自然不可能不会去关注那些东西。 大约六十多岁的尚书令皱眉看着水在瓶,沉声说道:“侍中大人如何这般笃定?” 水在瓶很是平静的站在那里,也许是想起了先前那样的一个道人所说的一些东西,这个白衣大妖很是认真地说道:“因为人间是天下人的人间。寒蝉没有理由去继续做着一些很是愚蠢的事情。” 一行人沉默了很久,吏部尚书深深的看着水在瓶,缓缓说道:“那么侍中大人呢?” 水在瓶撑着伞平静的离开。 “我当然也没有。” 有些故事,自然适可而止。 ...... 或许天工司也很忙。 少年在院中静坐了一下午,也没有见到那样一位本来有些兴致勃勃的天工司司主说要来看一看自己的伞的事。 就好像那样一件事突然便被遗忘了一般。 少年隐隐觉得或许与那样一个突然出现的道人有关。 只是一切究竟如何,毕竟少年对于许多事情都是毫不知情,自然也猜不到什么。 哪怕细雪剑人间初闻名声,终究少年依旧是淹没在大潮之中的人。 这个人间变化得太快。 哪怕少年开门见山,亦是难以追及那样一些人的足迹。 在数次拒绝了余朝云很是诚恳的枸杞茶之后,少年不得不委婉的表达了自己更爱喝酒的喜好,而后才终于在院子里安定了下来,静坐修行着。 直到某一刻,那柄身后的鹦鹉洲骤然出鞘,在余朝云与南岛一同不解的目光里,裹挟着细雪剑意游行在了院子之中。 二人才很是惊讶抬头看向了那些砥石穹壁。 人间悬火,人间也垂雨。 那些迷蒙的照亮这片地底人间的灯火,在那一刻,却是如同被大风吹着一般,不住地飘摇着。 那是某道白发剑意出现在槐都街头的那一刻。 余朝云很是茫然也很是惶恐地想起了当初在青天道中之时。 在某一刻,她也同样感受过这样一种剑意。 尽管同样只是转瞬即逝,然而那种心悸,这个出关境的道修少女,自然很难忘记。 她并不知道那样一种剑意究竟来自何人。 只是身旁的少年却好像清楚些什么。 人间三剑,少年见过两个。 这其实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哪怕是千年以来,人间剑修都少有同时见过三剑之人。 能够见到丛刃的,很难见到神河。 反之亦然。 当那些剑意出现的那一刹那,少年心中便瞬间意识到了那种便是他们这样的人都能够察觉到的剑意来自于谁。 大概也只有陈云溪了。 少年抬头静静的看了那些渐渐平息下来穹壁灯火很久,而后抬手唤回了鹦鹉洲。 这柄来自草为萤剑湖的剑,确实远比少年自己的桃花剑要好得多。 毕竟那才是真正的磨剑崖之剑。 哪怕是当今崖主,少年的那个女子先生,从某种意义而言,都算不得磨剑崖之剑。 余朝云目光落在了少年的那柄剑上,从那种惊诧里渐渐回过神来,很是惊叹地看着少年的剑。 “师叔这柄剑,应该很厉害。” 这当然不是吹捧。 事实上,这柄剑虽然在那些剑意里忽而出鞘,但是并非惊悸之意。 相反的,在那种剑鸣之中,有着一种兴奋之意。 南岛并没有什么得意之色,只是平静地将剑送回了鞘中。 “这不是我的剑。” 少年静静的看着手里的剑,轻声说道:“或许这是某位前辈,送给我,来告诉世人一些东西的剑。” 南岛其实从没有叫过草为萤前辈。 在当初初见那个春风小镇里,很是悠闲地走着的青裳少年的时候,南岛便一直将他当成了同辈之人,哪怕后来有了诸多猜测与了解,也没有叫过前辈,只是说着草为萤。 那个青裳少年自然也乐得如此。 毕竟伞下的少年是烦人的。 只是在与外人说的时候,南岛却也还是说着前辈二字。 余朝云有些好奇地问道:“前辈?是丛刃前辈吗?” 少年摇了摇头,并没有解释的意思。 “那他要告诉世人什么?” 南岛垂首按剑,平静地说道:“没什么。” 余朝云没有再问下去。 人人理所应当的有着自己的秘密。 这个青天道少女重新抬头看向了那些垂流着灯火的穹壁,轻声说道:“也不知道槐都上面发生了什么。” 南岛当然也不知道。 那只是一个被道人截断了的,另一种命运的走向而已。 少年并不知道,关于槐都的故事,其实已经快要结束了。 ...... 宋应新没有空闲去找少年。 在那个青天道而来的叫做秦初来的道人离开之后,天工司便忙碌了起来。 那些将巷子挤得无比逼仄的司衙之中,四处都是整理着各种记载文书的吏人——宋应新所说的,当然是极为认真的,天工司当然不止于机括,而是包罗万象之司衙。 那些吏人们真的便将二十年来,所有的,从那一日的秋雨里延伸而出的相关联的记录,尽数搬了出来。 石台之上的各处司衙都暂时停止了本有的工作,投入到了鉴别那些浩瀚如海的信息之中。 却是详实到了当初鹿鸣某户人间,在大雪里炒了一道什么菜。 宋应新默默的看着那份记载着某户人家炒的那碗芹菜黄牛肉的记载。 鹿鸣终日风雪之地,黄牛肉这样的东西,自然是珍稀的。 不过这大概确实不会是什么可疑的事。 毕竟不是过年,也可以吃饺子的。 这位天工司司主有些疲倦地放下了手里的文书,取下了叆叇,坐在那里捏着眉心。 院外却是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绕过了那些堆积的记录文书,停在了宋应新桌前。 “大人,这里似乎有些可疑。” 本打算休息一会的宋应新不得不重新戴上了叆叇,而后接过了那名吏人递过来的一本册子。 那是一本关于十一年前,妖帝神河寿诞之时的一份礼单。 记载了当时天下各城与诸多修行之地送过来的贺礼名录。 宋应新沉默了很久,翻开来那本册子,看见了上面某个被吏人们圈出来的名字。 这位天工司司主长久地看着那个名字,渐渐眯起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