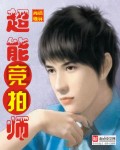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 风雪山脉的边缘,陈鹤正在那里唱着他的不知名的曲子,一面艰难的推着车向着雪山之中而去。 哪怕他在那处西北小镇里,做足了准备,却也是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车轱辘的轴承被冻住了,根本开不了,哪怕是推车,都要时不时的拿着铲子铲着轱辘那里的冰雪。 这使得这个兴致满满的想要去鹿鸣卖铁板豆腐的年轻人,不得不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丢了,只留下了一包驱寒的药材,还有穿在了身上的那些棉衣,外加几本传记拿来垫着坐。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陈鹤一面哼着歌,一面在这处山隘处停了下来,在这样的地方,山隘永远都是好地方,往这里一停,风雪都被遮去了许多。 这个闲云野鹤的唱着奇奇怪怪的曲子的年轻人,在隘口背风面休息了一阵,又拿来了铲子,在那里叮叮当当的敲着车轱辘上的冰锥。 “后面呢?” 就在陈鹤专心致志的弄着自己的小车车的时候,突然便有一个很是醇厚温和的声音从风雪上方传了出来。 给陈鹤吓得一哆嗦,差点一铲子铲在了自己的脚上。 抬头向上看去,隘口上方的山崖上,正坐了一个一身素白僧袍的浓眉大眼的中年和尚,很是诚恳的看着陈鹤。 好在陈鹤好歹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很快便平复了情绪,认真的想了想,说道:“你不问我还能想起来,你一问,我倒是真给忘了。” 那个和尚显然有些惋惜。 不过大概确实很好奇,所以顶着个大光头坐在风雪里,想了想说道:“那我不问,你再重新唱一遍。” 陈鹤倒也觉得还行,只是刚一张嘴,就忘了调和词是啥了。 在那里愣了半天,于是那个和尚很是诚恳的唱道:“我有花一朵.....” “啊对对对,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 陈鹤唱着唱着就觉得不对劲,抬头看向上面的那个和尚。 “不对啊,你一个和尚,为什么好奇女人花后面是啥。” 和尚也愣了一愣,而后笑着说道:“就是突然听见一个这样古怪的调子,有些好奇而已。” 是人当然就会好奇,不止是猫。 “更何况,你唱得,难道和尚就唱不得?” 陈鹤默然无语,说道:“你难道不应该说的都是如是我闻吗?” 和尚笑着说道:“如是我闻,东来谒者曰: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 陈鹤叹息了一声,于是低下头继续铲着雪。 叮叮当当的好一阵,那个和尚却是皱了皱眉头说道:“你别敲了,吵得我脑壳痛。” “我不敲,车就动不了啊,要不你来帮我推车?” 和尚说道:“那不行,我要在这里等一个有缘人。” 陈鹤靠在轮椅上,看着上方问道:“有缘人,什么是有缘人?” 和尚说道:“有缘人就是有缘之人。” 陈鹤没有在意那个和尚的废话,指着自己诚恳的说道:“你看我像不像有缘人?” 和尚低头看了陈鹤许久,说道:“不像。” “为什么不像?” “因为不敢像。” 陈鹤笑着说道:“你是怕像了就要帮我推车吧。” 和尚微微一笑,说道:“只是不敢像而已。” 陈鹤叹息一声说道:“我还以为你们和尚都像千年前的有缘和尚一样,见谁都要说上一句你与我佛有缘呢。” 和尚诚恳的说道:“有缘大师也不会见人就说有缘。” “比如?” “比如他就没敢和槐帝说你与我佛有缘,也不敢和青衣说你与我佛有缘。” 那个白色僧袍如雪一样的和尚坐在崖上,无比真诚的说道:“所以我也不敢和你说有缘。” 陈鹤若有所思的说道:“所以你要等的有缘人,大概就是懵懵懂懂,很好欺负很好诓骗的人?” 和尚诚实的托手笑道:“善哉善哉。” 这句话大概翻译过来,就是对啊对啊妙啊妙啊。 陈鹤这才看见那个和尚手里好像一块白色的石头。 “那是什么?” 陈鹤看着和尚问道。 和尚低头看着掌心的石子,倒是端端正正的唱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只是那究竟是什么,和尚却并没有说。 陈鹤见他不想说,倒也没有继续问,于是低下头继续敲着车轱辘上的冰。 和尚很是愁苦的抬手捂住了耳朵。 陈鹤敲了好一阵,抬头看着那个看起来很是苦恼的和尚,说道:“真的有这么吵?难道你会什么佛门绝学天耳通?” 和尚叹息一声,放下了捂在耳边的手掌。 “阿弥寺都没了,哪还有什么天耳通?我就是在雪里坐久了耳朵痛。” “......” “不信,不信你把你的耳遮摘了,来这隘口上坐几天试试?” 阿弥寺都没了,和尚没有和尚样,大概也能理解了。 陈鹤看着这片终年风雪的人间,自然不会把自己的耳遮摘了,只是看着那个和尚说道:“那你为什么不戴耳遮?” 和尚说道:“你想想,如果你想在这里等一个有缘人,结果别人来了一看,嚯,带耳遮的和尚.....” 陈鹤哈哈哈哈哈的在下面笑着。 不得不承认,和尚说的很有道理。 “那这么说起来,你也不是真的只喜欢穿着这一身单薄的衣裳的。” 那身素白僧袍虽然让这个和尚在崖上坐着很有韵味,只是大概也是能够把人冻得瑟瑟发抖的。 和尚说道:“那倒不是,毕竟贫僧真的武德充沛。” 和尚说着,在崖上并足站了起来,双臂展开,不动如钟的站在那里,而后双手缓缓向着胸前合十并拢,单薄的僧袍在风雪里撕扯着,倒是真的勾勒出了一身极为健壮的肌肉。 “......” 好一个武德充沛。 陈鹤默然无语。 话说你武德这么充沛,怎么把我当个有缘人帮我推个车都不敢? 和尚很是满意于陈鹤的反应,唱了一声佛号,又坐了下来。 “你是不是有个名字叫做大力和尚。” 陈鹤看着重新端坐于风雪里的和尚问道。 和尚惊喜的看着陈鹤说道:“你怎么知道的?难道你会他心通?” 陈鹤诚恳的说道:“当然不会,只是因为一看就很大力。” 和尚倒是显得有些惋惜。 陈鹤也不知道他在惋惜什么,二人在这里胡扯了好一阵,他也休息够了,于是把东西都收拾好,推着车就要出隘口而去。 只是看着前方风雪茫茫的人间山川,又停了下来,仰头看着上方的和尚问道:“你知道离这里最近的鹿鸣城池在哪里吗?” “阿弥陀佛,施主一路向南即可。” “向南,那是哪里?” 和尚想了想,说道:“我也不知道,向南是哪里,取决于你在路上遇见的第一个人给你指路指到哪里。” 陈鹤默然无语。 “所以你就是瞎指呗。” 和尚笑着说道:“这么大的风雪,我给你指了路又怎样,你连路都看不清,还不是要一路看运气走过去?万一我指对了,你自己走错了,反倒还要来怪我,我可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陈鹤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武德充沛,但是很是谨慎的人。 和尚最后又说道:“当然,我觉得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西边正在打仗,可能快要打完了,你如果运气好的话,倒是可以不用遇上那些事。” 本来打算推车过去的陈鹤狐疑的看着这个和尚。 “鹿鸣也要造反?” 和尚诚恳的说道:“不是鹿鸣要造反,而是造反的人来了鹿鸣。” 陈鹤好像想明白了什么,缓缓说道:“三十万青甲?” “大概是的。” 陈鹤想了想,还是向着那边去了。 “说不定我一路迷着路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完了呢?这个时候卖铁板豆腐生意肯定好得很。” 和尚也没有劝他,只是笑眯眯的坐在崖上。 “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似花花似梦.....” 一直到那个推着车的年轻人哼着曲子在风雪里渐渐远去。 这个和尚才转回头来,不远处的隘口对岸风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坐着一个很是凄惨的人,双手很是无力的垂着,大概是被打断了,坐在风雪里不停的咳着血。 也许他一直都在那里,只是被风雪盖住了而已。 “明施主不要急,等我等到了有缘人,再去找那个跑掉的剑修,送你二人一起去冥河。” 和尚微微笑着看着那个一身巫袍染满了鲜血的中年人。 毕竟贫僧武德充沛,并不是在开玩笑。 明蜉蝣咳嗽了许久,才终于将喉咙里郁结的巫血咳了出来,抬起头看着对崖的和尚,声音有些嘶哑的说道:“大师在这里,那么阿弥寺呢?” 和尚微微笑着看着明蜉蝣,说道:“贫僧都找不到阿弥寺的入口,施主为何觉得他能找到?” “他是庄白衣,他师父是丛刃。” “有道理,毕竟因果剑前辈是人间最后一个到过阿弥寺的人。”和尚轻声笑着,说道,“但那与庄白衣有什么关系呢?” 明蜉蝣还想再说什么,那个和尚只是双手合十,轻声说道:“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 这个来自黄粱,离开的时候曾经无比自豪的说着自己是灵巫之上神鬼之下的第一人的南楚灵巫,突然便看见了那个和尚手中的那枚白色石子。 “那是有缘大师的舍利子?” 和尚低头看着掌心的石子,轻声叹道:“当年有缘大师在黄粱以风雪冻杀了一城之人,如何能够有舍利子?” 明蜉蝣沉默的坐在那里,又开始咳着血。 一直咳了许久,明蜉蝣才看向了那个已经消失在风雪之中的那个身影离去的方向。 “那人是谁?” “一个过客而已,明施主很好奇?” “因为觉得大师有些过于拘谨了。” 和尚轻声笑道:“是的,因为确实有些放不开。” 大概确实不如向明蜉蝣展现自己充沛的武德的时候放得开。 明蜉蝣自诩有着鬼术越行,然而依旧无法从这个和尚手中逃脱。 和尚也许确实不会天耳通,只是耳朵痛,但是大概他是会神足通的人。 所以在三次越行之后,明蜉蝣被逮到了。 而庄白衣则是趁着明蜉蝣倒霉的时候,化作剑光窜了出去。 佛门也许没了。 只是和尚还是有的。 ...... 披甲的年轻人脸上的胡子已经很久没有打理过了,看起来乱糟糟的。 高山上有着一条尚未结冰的河流淌下来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 所以河边搭着许多的帐篷,一路绵延而去,像极了一线风雪川原之中无数的草垛。 草垛也许是青黄色的,于是那些整齐有序的穿行在草垛之间的甲兵们也是带着青色的。 那些青色甲胄,有着很强的避水避火御寒的能力,只是总是这样,他们也不得不想办法塞了许多绒草来保暖。 年轻人的青甲并不合身,是捡了某一个被冻死的士兵的盔甲,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之中,自然更加的寒冷。 只是他并没有回营烤火,而是拄着剑,站在那条河流的旁边,低头看着自己脸上的胡须。 并不茂盛。 倒像是一些稀稀拉拉的杂草一样。 年轻人的年纪,大概尚且不足以让他长出令人一眼便觉得豪迈的胡须来,所以纵使留得再长,也生不出那种威严来。 年轻人在那里看了许久,身后有个很是别扭的脚步声踏着雪咯吱咯吱的走了过来。 这样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个瘸子。 于是年轻人也走了两步,原来也是个瘸子。 小瘸子的腿是被老瘸子打断的,老瘸子的腿,是被更老的瘸子打断的。 只不过小瘸子被打断了腿,反倒激起了更为愤怒的情绪,于是就跑去撞南墙了。 在槐都,一头给自己撞得找不着南——虽然世人常说找不着北,但是小瘸子还是找到了北,带着青甲狼狈的跑进了北方大漠里。 更何况,他本就姓北,又怎么可能找不着北呢? 仓皇北顾。 北台一直觉得他家先祖的名字不是很好,如果不是叫做北顾,又怎么会导致他们在南方看了那么久的北方? 当然叫做北岛也不行,不然总让他向着某个叫做南岛的少年的时候,就觉得那是自己祖先辈的人。 叫做北伐最好。 只是自家先祖,一个好好的函谷观道人,为什么要叫做北伐? 两个瘸子在河边站着,各想各的。 “鹿鸣这样的地方,确实不需要驻扎太多兵甲,多了不论对于人间的负担,还是对于我们的前行,都是一件坏事。”老瘸子北园站在河边,向着更西面看了过去。 北台看向了自家父亲,又看向远方。 越过这条河,越过这片风雪平原,是一座屹立在风雪之中的都城,那是整个人间都很少知晓名字的地方。 叫做极都。 为西极之都的意思。 黄粱虽然历来被槐安人所轻视,但是至少他们依旧是活跃在人间的。 而不像鹿鸣。 世人一想到鹿鸣,便只有好大的雪。 雪后面是什么? 大概少有人知道。 北台以前也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 雪后面是一个与世无争,被风雪遮蔽的人间。 千年前的故事,哪怕是黄粱,至少也曾经抵抗了一段时间。 只有鹿鸣,这片雪国,在无人问津之中,默默的成为了大风朝的一部分。 如果李阿三泉下有知,大概也得被气死。 当年他为了防止自己在觊觎黄粱的时候,被鹿鸣人直入槐都,一直都留着数十万大军镇守在雪原边境。 穿越一大片辽广的冰原当然是极为困难的事。 更何况还是要大军穿越。 途中的折损,只会远高于战损。 这也是李阿三在最初的时候,数次出兵,都没能真正拿下鹿鸣的原因。 时代的局限性,使得这个帝王最后一事无成的在剑崖之上跳了下去。 这样一个地方,大概安静的就像不存在一样。 当年还有阿弥寺的和尚行走四方,带来鹿鸣的消息,后来阿弥寺没了之后,这片风雪大地便少有人迹了。 ...... 北台安静的看了很久,而后轻声说道:“倘若李阿三当年能够有着这样一支抵御酷寒的青甲,人间的故事也许便不一样了。” 倘若槐安当初向西面的扩张,不会被风雪阻拦,也许妖主依旧在安静的做着他的礼部尚书。妖族不会南去,神河也只会是一个安静的诞生在秋水的小妖。 只可惜当初道门甲兵与机括之术的发展,虽然已经有了起色,然而也只是在当初跨越幽黄山脉之时,甲胄乘风,从两千多丈的高山一跃而下,惊艳了世人。 纵使如此,不得不提的是。 当初翻越幽黄山脉的过程中,那二十万大军,被冻死了摔死了数万人。 所以大概一如北台所说,如果是青甲,那么一切的结局都是不一样的。 北园轻声说道:“故事当然不一样了,不止是当初,也是现在。” 北台从西门手里抢走兵符的时候,故事就不一样了。 这个当初的南衣城北大少爷,安静地站在那里,远眺着那样一处风雪深处,汇集了整个鹿鸣残兵的极都,风雪之上,有着沾染着幽黄高山与冥河的瑰丽色彩,那是与清冷沉寂人间毫不相符的热烈绮迷的色彩。 “那就从鹿鸣开始,重新讲起。等到槐安摇摇欲坠.....” 北台拄剑立于风雪河畔,平静的说道:“我会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