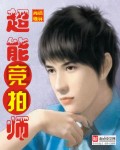大风历一千零三年,三月二十九,细雨。 在一片朦胧的细雨里,有人背着一柄断刀走进了南衣城。 是西门。 是青山里被北台借来的一指山河点成重伤的西门。 在青山里睡了一夜的西门,满脸愁苦。 当他醒来之后,第一时间便拖着身体去了山的那一边。 当他这样去的时候,心里便是抱着一些虚无缥缈的希冀的。 比如北台突然回心转意,就在那里等着自己,然后把兵符交还回来。 比如北台失足滚下去,突然跌死在那些下山的山道里。 总之西门怀揣着极其微渺的希望,去了那边。 然而没有。 山道上有着血迹,似乎有人从这里滚了下去,但是没有死。 那处下山的断崖边,有着许多血迹,但是没有尸体。 血迹在这里便停住了,一直到崖边,像是有人从这里跳了下去。 但是也没有死。 那片藏在青山里的三十万青甲,已经不在这里了,连驻地都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像是有人做了决绝的选择,从此宁愿死在北方,也不愿再回来这里。 西门站在山崖边怅望着那片空空的,余留着残尽余火的山谷,一面咳着血,一面想着。 是在什么样的一场夜色里。 那个满身鲜血的少年,一瘸一拐地跳了下去,然后被谁救下,又一瘸一拐地向着营地走去。 站在高高的土丘之上,慷慨激昂地说过怎样的话语。 而后万千青甲向着北方而去。 是的。 西门的遐想结束的时候,西门便确定了。 北台反了。 当南衣城与槐都还在猜测着黄粱那边何时会反叛的时候。 便在南衣城之外,本应用来应对大泽那边的这些青甲,先一步举起了反旗。 在一个人们从未在意过的,游手好闲热衷于饮酒买醉的冲动少年手里。 所以西门沉默地离开青山,向着南衣城而去的时候,想了一路。 人间对于一切的诸多轻视。 到底是自信,还是盲目的愚蠢? 西门不知道。 他不是来自人间剑宗或是青天道这种地方的修行者。 也不是出身于何等复杂交错的人间势力之中。 西门姓西,名门。 是一个在某个小镇西门口被人遗弃的孤儿。 被五刀派某个在镇子里喝得烂醉的师兄捡了回去。 唯一庆幸的是,西门的天赋很好。 一个小小的极少为人所知的五刀派,自然教不了他。 当他的师父还困守在成道境的时候,西门便已经小道了。 于是便被师门的人赶了出来。 不是清理门户。 只是因为,他们觉得他应该去看看外面更高的世界。 西门那时候觉得师父们想得太多了。 人间只有这么高,无非青山小镇,小河流水三两鱼儿。 能高到哪里去呢? 然后他出了门,在某个青山脚下,遇见了一个忘我失败,疯疯癫癫的十二楼人。 想成仙的自然都是疯子。 西门于是准备拔刀。 但是有人比他更快。 那个人叫程露。 流云剑宗宗主陈云溪的弟子。 西门的刀才始出鞘一寸。 程露的剑已经回到了鞘中。 西门那时才明白,原来人间真的可以很高。 不止青山小镇三两鱼儿。 西门那时颓废了许久,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重新振作回来。 一面走走停停向着南方而去,一面勤加修行。 于是后来在凤栖岭上,西门再度遇见了已经有着四破剑名号的程露。 西门向他请剑。 程露也记得这个当时自己出剑的时候在不远处溪边站着,握着刀发呆的人。 他那时还心想,怎么有人握着刀,却不拔出来呢? 流云剑宗外面的人都这么客气的吗? 程露没有想过是他出剑太快。 西门在走,程露也在走。 一个人见到更高的东西,一个人见到了更低的东西。 程露当时想着,原来外面的人出剑都这么慢的吗?那他们修的剑意之道,想来也不过如此。 虽然西门用的是刀,但是程露还是想着让着他一点,于是在拔剑的时候,故意慢了半拍。 然后程露的头发便被斩下来一寸。 程露当时看着那飘落到地上的头发,什么也没有推脱,只是抬头不可思议地看向西门,而后说道——你赢了。 西门自然知道程露慢了一分,亦是说道——你在让着我。 那一日岭南剑宗诸多剑修便在旁观。 也正是那一日。 人间知道了有个叫西门的人,有个叫五刀派的地方。 西门与程露究竟谁赢了,已经不重要了。 一个人见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人间。 一个人见到了从低处也能向上而去的下层修行者。 西门的那一刀,让程露再也没有留过长发,永远都是一头短发,向着两边分开——或许便代表了程露对于西门的认可。 再后来,西门便来了南衣城。 被同样出身流云剑宗的狄千钧带入了天狱之中。 所以当西门背着断刀,缓慢而痛苦地在南衣城的细雨长街上走着的时候,便想起了那个向来冷漠的天狱南方调度使。 入天狱这种事,说不上好事,也说不上坏事。 人活一世,总不能永远是在漂荡着的。 西门抬头看着细雨。 这场雨给他的感觉并不好。 阴沉沉的。 好像有什么事会发生一般。 所以他背着断刀,在河边捡了根漂着的不知道谁遗弃的拐杖,向着城西而去。 天狱的火已经被扑灭了。 西门走到那条巷子的时候,闻着那种在雨中久久未散的灰烬味道,皱起了眉头。 但天狱的墙本就是黑的。 所以人间大概也不会注意到,这里曾在昨晚又经历了一场大火。 西门推开天狱的大门,穿过那些落满了灰色斑点的梨花,向着更深处走去。 有许多的天狱吏正在内院整理着那些抢救出来的文书案卷。 有人看见西门走了进来,走上前很是惭愧地说道:“昨日有人来了天狱.....” 西门拄着拐杖,背着断刀,沉默地看向监察院所在的方向。 “狄大人他......” 西门叹息了一声,说道:“我知道。” 西门穿过了月亮门,一路走到了已经被烧毁的监察院前。 在那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 西门背着刀,在雨中咳嗽着,而后停在了那具尸体前,沉默地看了很久,而后目光在尸体的心口处停了下来。 那里有着一道极深的剑痕。 没有剑意,只是普通的剑痕。 人间的人各有模样。 人间的剑也是。 而这柄在心口肋骨上留下剑痕的剑。 特征格外明显。 剑形普通,便是南方常有的模样,但是它很厚。 那种厚度一点也不像一柄剑,倒像是一块铁。 就好像是某个才始学习锻造的学徒,惫懒地敲了一个剑形,就放弃了一般。 西门看了很久,低声地咳嗽着,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看向一旁的某个入道境的天狱吏。 “昨晚发生了什么?” 天狱吏低声说道:“我不知道,有人用道术将整个天狱割离了。” 西门没有再问,转身向外走去。 那人在身后犹豫地问道:“狄大人的尸体?” 西门顿了一顿,平静地说道:“烧了吧。” 西门去了天狱前院,停在那些梨花道上,沉默地看向四周,那些落满了火灰的梨花之上,依旧残留着道术痕迹——与前晚所留下的韵味相同,都是古朴的道术。 西门沉默了少许,而后一路向前走去,一直到停在了大门口。 昨日天狱之中有着不少天狱吏。 但是在天狱深处的监察院却是便这样被人走了进去。 而后一剑刺下来。 用了如此玄妙的道术,杀人的时候却是极其简单一剑,那柄剑还是一把工艺拙劣的剑。 是因为什么? 西门咳嗽着,于是明白了什么。 他没有余力。 就像自己被北台的山河一指点中之后,元气大伤,不得不像个世人一样穿梭在人间一样。 那人用了道术之后,神海之中便没有余力再去驱使别的东西,于是只好粗暴地用着世人的方式去杀人。 梨花之上残留的道术虽然韵味古朴,然而并没有什么令西门心惊的味道——或许便是他无法完全施展这一道术。 所以他的境界不会很高。 至少不会是小道境。 用剑的道门之人。 西门再次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张小鱼。 但张小鱼自然不会做这种事。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 倘若说之前他的来意还不清楚,那么昨晚的事便已经很明白地暴露了这个人的动机。 他要藏住一些东西。 所以杀了人,还要放火。 西门抬头看着头顶某朵梨花上落着的灰烬。 这片灰烬很大,因为在梨树的下层,所以没有被雨水打湿冲碎。 西门将那朵梨花摘了下来,上面隐隐有些字迹,西门看了许久,也只认出了一个南字。 轻轻吹了一口气,将那些灰烬尽数吹落,西门将梨花丢在了树下。 南衣城天狱,案卷之中自然满是南字。 这是毫无意义的信息。 西门回头看了一眼天狱深处,而后转身出了门。 向着城北而去。 虽然西门现在有一些线索,但是目前这些事相比于另一件事而言,并不重要。 三十万青甲北上,要去谋反也好,要去泄愤也好,这都是与人间剑宗无关的事。 但是他们不在南衣城了,这是与人间剑宗有关的事。 西门拄着拐走了一路,用了很久才走到了剑宗大门。 少年胡芦抱着剑,在门口发着呆。 看见西门的身影走来,目光又落到了西门手中的那根拐杖上,有些犹疑地问道:“西门师兄昨晚又来过这里?” 西门低头看着手中的拐杖,心道昨晚我被人打个半死,在山道睡了一夜,怎么会来你们剑宗? “没有。” 西门摇了摇头。 胡芦哦了一声,看着西门问道:“那师兄今日又来做什么?” “我想找下陈师兄。” 胡芦指了指门内,正想说陈怀风应该便在里面喝茶,只是突然想起早上听见里面的师兄们好像就是在说着陈怀风去了同归碑下的事。于是又把手缩了回来,往南一指。 “师兄在同归碑那里。” 西门沉默少许,轻声咳嗽着,叹息了一声说道:“那张师兄呢?” “张师兄打牌去了,不知道现在回来了没有,他一般都是走后门的,回来了就睡觉,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里面看看。” “多谢。” 西门向着剑宗内缓缓而去。 胡芦看着西门的那柄断刀,再想起西门的那种虚弱模样,倒是有些好奇,是谁给西门打成了这样的。 想着两位师兄时不时的哀叹——看来人间的事确实很多。 胡芦突然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 这么一想,自己抱着剑在门口坐着也不错。 至少没有那么多烦心事。 幸福果然是需要比对的。 胡芦如是想到。 ...... 张小鱼确实在剑宗里睡觉,侧着脸趴在三池亭子的护栏上,睡得口水拉丝。 西门在问了几个剑宗的弟子之后,终于找到了张小鱼的所在。 只是看着这一幕,却也沉默下来。 张小鱼怎么看都没有陈怀风靠谱。 什么正经人夜不归宿打牌到清晨,然后睡得像头猪一样? 但是西门还是拄着拐杖,走到了亭子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推着张小鱼的肩膀。 “张师兄,张师兄,醒醒!” 西门的呼唤毫无卵用。 要不是已经来了剑宗,再加上受了伤,不想来来回回的走,西门早就扭头去同归碑找陈怀风了。 张小鱼砸吧了两下嘴,翻了一面继续睡着。 不远处有个三十来岁的剑宗师兄从小道过,看见这副画面,笑着远远地喊了一声。 “张小鱼,打牌了!” 张小鱼蹭地一下跳了起来。 “打什么牌?谁在打牌?哪个王八蛋偷偷打牌不叫我?” 师兄早就哈哈笑着走远了,只剩下背着断刀的西门一脸无奈地站在亭子里。 他突然怀疑,是不是丛刃不想管人间事了,才让张小鱼来看着人间的。 相比之下,陈怀风便显得尽职尽责多了。 西门叹息着想到,而后向张小鱼行了一礼,说道:“张师兄。” 张小鱼打着哈欠说道:“原来是西门师弟想打牌?” “......”西门默然无语,过了许久才看着打算重新睡下去的张小鱼,说道:“南衣城要出事了师兄。” 张小鱼懒懒地趴在栏杆上,像只丢了尾鱼的大懒猫一样。 “出什么事啊。” “北台夺了兵符,带着三十万青甲北上了。” “哦,那挺好的,能凑八万多桌麻将呢。” “.....”西门叹息了一声,“我还是去找陈师兄吧。” “哈哈。”张小鱼努力撑着栏杆坐正了起来,打着哈哈说道,“我开玩笑的。” 西门松了一口气,然后差点被张小鱼下一句话气死。 “除了南衣城,哪里找得到八万张牌桌。” “师兄不要开玩笑。”西门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张小鱼严肃地说道。 张小鱼也正色起来,看着西门认真地说道:“是你先和我开玩笑的。” “?” “你西门一个堂堂小道第七境的修行者,能让一个游手好闲的北大少爷把兵符夺了去,难道不是在开玩笑?”张小鱼平静地说道。 西门想要说什么,张小鱼却是打断了他的话头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受了伤,看样子还挨了一顿打,如果没猜错,是山河一指。” 西门沉默地看着这个来自山河观的剑宗师兄。 “但是你动脑筋想想,他一个从未踏入修行之道的北大少爷,凭什么敢去劫你的道?凭一腔正气还是满腔孤勇?” 张小鱼冷笑着说道:“我知道你西门在人间名气很大,但是这么大的名气,北大少爷都敢干这样的事,你觉得是他蠢还是你蠢?” 西门被张小鱼劈头盖脸地一顿骂,叹息一声,说道:“此事,确实是我的问题。” 张小鱼倒也没有继续骂下去,同样叹息一声,说道:“不是你的问题。” 低头看着白衣下面那偶尔露出的一角道袍。 “是那个借山河一指的人的问题。” 张小鱼说着便咳嗽了起来,往池中吐了一口,然后低头看着里面星星点点的血迹——那是残留的一些伤势。 “他娘的,真的好烦。”张小鱼愁眉苦脸地看着池水说道。“你们的柳大人呢?他什么时候回来,这种事情应该是他这个兵部侍郎的责任。” “柳大人仍在大泽中没有回来。” “ε=(´ο`*)))唉。”张小鱼叹息一声,想了很久,缓缓说道,“岭南的剑修下来多少了。” 西门摇了摇头,说道:“不知道,南衣城有许多生面孔,按照以往他们的惯例,应该是倾巢而出。” 张小鱼的心情这才好了一些。 岭南剑宗虽然常年被修行界诟病,但是诸多剑修的到来,自然让世人的心更安定一些,只是那原本应当作为南衣城防守主力的三十万青甲的离去,无论对于哪一方,都是不好的消息。 人间剑宗虽然诸多师兄。 但是修行界高层非必要,不可能下场出手。 更何况大泽那边什么情况,依旧一无所知,那场大雾封锁了一切。 如同千年一般,再度将这两片土地隔绝开来。 张小鱼沉默地想了很久,看向西门,轻声说道:“修书北上,告诉槐都,南衣城允许北面来人。” 西门沉默少许,说道:“槐都未必肯相信,毕竟按照柳大人的说法,陛下不知去向,整个槐都都拿不准主意。” 张小鱼平静地说道:“就说柳三月死在大泽里了。” 西门轻声说道:“这样日后会是欺君之罪。” 张小鱼站了起来,向着细雨中走去。 “你只管写,如果柳三月没死,我去杀了他,那便不算欺君了。” 西门沉默地站在亭中,那根拐杖便在身旁,上面或许还有些未曾烧尽的血迹,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