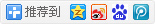当晚,李丹果然将宋小牛叫来这边,做了主菜椒盐烤鳟鱼、上汤三素、蒜蓉青蒿和五花肉炒双菇,还有个五彩汤。 吃得李著连声喝彩,又问这五彩汤是什么做的? 李丹告诉他这是用豆腐、鸡蛋、木耳、青笋(莴笋)和红萝卜(胡萝卜)五样切丝、烫熟后做出来的。 李著赞叹不已,道:“就这刀工便不得了。 罢、罢,三郎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不考科举,凭这份做事的精巧、细密心思将来也绝非池中之物,至少饿不死呀!哈哈!” 那时候的人大多数家庭都是上午日头在顶时吃朝食或叫午餐,傍晚太阳西斜时再吃夕食或叫晚餐。 穷困人家是只有午餐,傍晚最多喝些野菜、块根煮的菜粥(没有粟米那种)。富裕人家就不同了,早起有早茶,甚至夜里还有夜宵。 所以从人的精神状态、肤色和胖瘦上,完全可以一眼区分对方的身份和地位。 点灯之后李严坐着一顶小轿去了县衙,他如今面颐园额颇具富相,一看便知是位不为米麦升斗操心的大老爷。 李三爷是个享福惜身之人。像他的祖父那样为大义捐躯,或者如英年早逝的父亲那样劳碌都不是李严期待的。 他更希望子孙绕膝,做个长长久久的富家翁。 今天下午三生堂的老周来给朱氏把过脉,确定了儿媳妇有喜,这个消息让他像喝了蜜水般浑身上下都透着舒坦。 不过现在他要办的却不是庆祝的宴席大事,是趁着自己的兄长——李府大老爷还没回家,赶紧和范县尊把那分家的事宜定下来才是正经。 正想着,轿子停住了,他估摸长随林子夫拿了自己的名片正往县尊府上投刺。 果然不一会儿,林子夫的声音在轿外低声道:“老爷,县尊请您到花厅叙话。” 李严“嗯”了声,双抬轿子又走起来,不一会儿停下、落轿,帘子掀起。 李严从里面走出来,整理着道袍,手扶平定巾抬头看了看,然后转身跟着名提着灯笼的范府家人步入宝瓶门。 方才轿子走县衙的后门进来,停在了花园夹道。 去花厅的话需绕过花园和眷属居住的区域才可。李严来过多次,对这里很熟悉了。 一般县令每日卯时(5-7点)到前衙开始办公,酉时(17-19点)散衙后回到后衙与家人同处。 不过李严知道只要没什么大事情,本县都会在酉时初刻(17:30)便散衙。 范太尊回到后面用过夕食,正好是现在的时间——戊时初刻(19:00-19:30)左右。 这会儿是一天最放松,且最适合谈些隐秘事的辰光。 刚迈进花厅所在院落的月亮门,就已经看到范县令一身居家深衣大氅,在台阶下背着手相迎了。 “哎呀呀,县尊老大人在上,学生怎敢劳您大驾,罪过、罪过!” 李严是举人身份随时可以出任县吏员或代理县令的,所以他对范县令自称“学生”。 “选之(李严的字)老弟和我还这样客气?哈哈,今夜月色正好,老夫正需一友相伴,你我花厅品茶赏月如何?” 范县令小眼睛眯成细缝,心里却猜不出什么缘故让李严这个时候求见自己。 两人寒暄已毕,李严扶着范县令共同步入花厅面窗并坐,清亮的月光铺洒进来,照在屋内盛开的白色牡丹上,花瓣透出蓝莹莹神秘的色彩。 很快有小厮煮好茶水,为二人烫净细瓷小杯,斟满金色的茶水后退了出去。 范县令先是问了问李著的情形,闻听朱氏有喜忙祝贺他双喜临门,然后聊了两句收成和铺面生意上的话,低头呷着茶水, 不紧不慢地问他说:“选之,你家中喜事连连,不好生铺排庆贺却提灯照影来见本县,可是有什么要事呵?” “大人明见千里呀,学生此来确实有桩家事不知该如何处理,特向县尊请教。” “啊?”范县令增么也没想到是“家事”,他楞了下,揣起手皱眉道:“贤弟,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这……好像是要给老夫出难题呵?” “不敢、不敢,学生怎会做那等事呢?只因这桩事涉及人伦与法度,学生举棋不定久矣,如鲠在喉啊,所以才来求教。 大人本县父母,见识广博、法务熟悉,万望大人给与指点一、二,学生必然知恩图报!”说着李严离席,深深下拜。 范县令听他这么说,这才重新露出笑容,伸手扶起李严请他归位,同时说::“好吧,既然选之你如此虚心上门,我也不好一推了之。 你且把前后讲来我听听,究竟是何事令你这样不安呢?” 李严心中大喜,忙把自家父亲去世前后情形和李肃把持家产的事由大致说了一遍。 范县令听了心中已经有数,脸上却没显出来。 他手捋胡须想了想说:“照贤弟的说法,你兄长接管家务后抚养文正公和足下成人,你二人一个做到知府,一个也是举人。 贵府兄友弟恭,可喜可贺,然则这又有什么毛病呢?” “这……,”李严心说:敢情我白讲了?哦,老东西非要我自己揭开这层不可! 只好回答:“大人呐,兄友弟恭这是圣人教诲,原有之义。 但是……,大兄他把持家产多年,即便我兄弟二人成婚后也未主动提及划分家产之事,而我二人因大兄养育之恩,亦不好开口,故而拖延至今。 但现在孩子们也大了,再拖下去不是个办法。一大家子男男女女住在一起也越来越不方便,才起了是否该划分清楚,然后三家各过的心思。” “唔!了解!”范县令点头:“这是你三房的意思,还是三家都有这个想法呢?” “拙荆与二房商量,那边也正有此意,只是大兄在南昌未归,所以长房那边还未去说。” “既如此,等燕若(李肃的字)回来,你们三家一起商议不就好了,何必再来寻我?”范县令拍开两手,似笑非笑。 李严尴尬地咳了声,低眉顺眼回答:“大人说的是,本该我们自家的事自家讲清楚便罢。 不过……这事既涉及律条,又包含人情义理,该先顾哪头,学生实在愚钝,故而求教。” 他绕着弯子说半天,总算来到核心了。 范县令呵呵一笑:“选之的意思,长兄养育乃恩情,分家而居却合乎法理,孰重孰轻你现在难分首尾,可是这话?” “正是、正是!” “那我来问你,何为法、何为情?” “这……,法者天理之道显也,天子奉天理而行世间国法,以秩序江山社稷。 情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所谓‘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故国法上顺天理,下及人情。” “着!”范县令点头:“既如此说,国法高于人情,两者冲突之时,自当以国法为先。选之可同意否?” 李严想想,却不知这话和自家有什么关系,同意说:“自是如此!” “好!”范县令起身走到月光下,背着手缓缓道:“我朝行两税之法,即按户收丁税,按田亩收地税,又以不同户等摊派赋役。 你兄长虽然把持家财,但贵府二房、三房却因此从未如数缴纳赋税。这个你先心里有数,然后咱们再说其它。” “范大人的意思是……?”李严忽然明白了,范县令的意思是自己要分家,就得揭开这么多年李家瞒报户等、丁口的情形,并补缴积欠的赋税。 这个老滑头!他暗骂一句。不过心里迅速地做个算计,还是带着笑说:“学生以为遵纪守法乃是良民天职。 如果大人能够居中调停,令吾等妥善划分而又不失体面,这些积欠的正税我们是愿意补上的。” 正税也就是朝廷规定要缴纳的正役捐代(前所说雇人代行差役)和税粮,不过李严耍个滑头,没提是否要补齐县里摊派的杂泛差役捐代,这个数目两家即便分摊也还是会令人肉疼的! “大人仁厚爱民,万望相助,学生粉身碎骨,无以为报!” 李严说着,为范县令斟满茶杯,然后悄悄从袖中摸出张折好的银票垫在杯底。 捋须望月的县尊用余光看到这一举动,嘴角微微上扬,点头道:“这个好说、好说。 尊府诗书世家,燕若又曾侍奉今上,我相信定能知错就改的。 大道奉行,这点小小不然的失误算不得什么。孰能无过?”说完两人相对而笑。 “不过,假使分家,又该如何析产呢?贤弟可有腹案了?”范县令回到椅子上坐下。 “这个……,”李严心思一转,问:“难道不该是各房均分吗?” “诶,如此则差矣!” 范县令摇着头说:“你大兄虽然把持家产,有过违法隐瞒举止,但他存心忠厚,抚养你兄弟出人头地、成婚嫁娶,而今你家中也是有秀才和举人,这一切难道不该感念他的恩德么? 若是硬行均分,恐怕你族中有人以为不平,倒让事情不好看了。你说是这个道理不?” “呃,”李严皱皱眉,但也知道范县令说的实话,只是比较委婉,没有说李肃可能会直接与他冲突。 二房女流,大哥还会投鼠忌器,最可能是直接将怒火撒在自己头上。 李严心中暗惊,小心看看范县令,问:“县尊大人有何妙计?” “妙计谈不上。”范县令摆摆手:“你虽占理,但事情不可以这样做,做了别人闲话会说你三老爷恩将仇报的。 话到这里,具体怎样做还要你回去同二房仔细商议,总之要燕若那边可以接受,族里又无话可说才好。 比如承诺析产之后你们两房另置居所,将祖宅交予长房经管等等。 似这样的条件,我估计燕若应该可以接受。当然,必要时我会居中协调的。” 他当然乐意协调,以便吃完二、三房回头再吃长房,反正他不会亏本。 李严听他这说,渐渐明白他的意思,心里打个旋有了些主张,想着回去后和舒氏交代清楚,着她再去说服二奶奶高氏。 想到这里又记起二房还有要分家的事来,忙向范县令提了。 县尊大老爷听完抚掌呵呵笑道:“只要你三家先析分清楚,她家的事情也就不难。 不过,那二奶奶若是惦记着妾室的嫁妆,我劝她不要想。 一来据我所知人家家中是庐江巨贾,产业都在江北,我小小余干县令无权过问;二来虽然文成公不在,可也不是她这个大娘子想如何便能如何的。 那屋里不是还有你家三郎么?她这个名义上的母亲可以做主同意本房析产,但具体做起来却是三郎和五郎兄弟之间的事。 他两个一个是有功名的秀才,一个已经年满十五岁,岂容她女人家插手?最多我到现场说和顺便做个见证就是了。” “大人若能到场,再好不过!”李严心想二房这边自己占不到大便宜,能帮到这地步也就是了,不再多说。 少不得回去让那小钱氏再备份礼给范太尊,自己何必在两个寡妇中间乱跳,难道不怕招闲话? 送李严到门口,看着他背影消失在月亮门的另一侧,范县令这才转身进去,急急地拿起茶杯,取出银票来看,却是张二十两的银票。 嘿嘿,分家?那你们就分好了。范县令得意地笑笑。那李家二房还要接着和妾室分,真是好笑! 范县令晃着八字步往寝室走,想着今晚陪侍的应该是哪个来的? 不管谁,估计李家这次能给自己带来一、二百两银子的收入,今晚身边的这人儿定是个有福气的,值得老爷我好好疼爱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