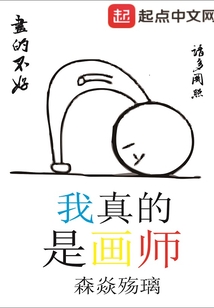“聚元式?”银尘听到了一个新的名词,不禁出声问道,新名词成功地将他的注意力从大眼睛那里转移了出来。 “所谓【聚元式】,就是一种【阵法】,银尘你应该能理解,阵法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包括行军打仗时候使用的军阵,风水师们刻意营造出来的‘小须弥福地’或者‘风水林’之类的都属于【阵法】。而【聚元式】却是特殊的,可以和修士们的元气产生共鸣的阵法,这种阵法,必须是用特殊方法将罡风固定在空间之中才能形成的。你也可以认为是我们修士专门使用的阵法吧。”张萌萌一边耐心地给银尘解释着,一边不着痕迹地将他拉离悬崖。 “那么【聚元式】有什么作用呢?听起来像是提高修士吸收元气的速度的?提高元气浓度的?”银尘接着问道,不知为何,他总觉得有什么宿命一样的东西要降临到自己头上。 “聚元式聚集元气,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用法,厉害一些的聚元式,可是能够不依赖让人而凭空产生罡风,从而化形成各种东西,起到各种各样的作用呢!银尘你学过《残魂经》甚至连残魂绝响都掌握了,不会不知道那些刻印在暗器之中的,用灵魂扭曲成的图案,就是最高明的几种聚元式之一吧?”张萌萌有些奇怪地看了一眼银尘,心想你连最强大的聚元式都掌握了,怎么连聚元式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银尘听到这里,脸色猛然一变,然后就支支吾吾地开始转移话题,一会儿问张萌萌这次行动的计划是什么,一会儿问那些正道可怎么对付,一会儿又问晚上吃什么,问题都是颠三倒四的,显然心不在焉。 银尘和张萌萌随便支吾了几句,就接口想静一静,钻到了属于他一个人的大帐篷里面去了,张萌萌看着银尘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禁更加奇怪起来,这个男孩子怎么了,谈论起聚元式就紧张成这个样子?难道他的《残魂经》修炼出了问题?可是那种功法能出什么问题呢?那已经是最邪恶的法门了呀?不出问题才应该是问题呀?除了问题就很正常了呀? 张萌萌在帐篷前呆呆地乱想了一气,什么都想不通透,只能摇摇头,钻进了旁边的帐篷中去了――她的帐篷和银尘的紧紧挨在一起。 银尘钻进帐篷里,随手拿出他几天前的那个晚上,用剩下的所有梅花镖炼制出来的东西。 那是一块标准的立方体,棱角平直,四四方方,每一条棱的长度都称得上分毫不差。立方体的每一个面上都刻着一条条细细的金色凹痕,这些凹痕彼此相连,仿佛一只不规则的笼子一样将立方体包围起来,那是封印,光属性的封印,就如同他的仙曲一样,光明的封印死死压制住了魔器本身散发出来的死灵气息,使其粗看起来像是一件很普通的物品。 银尘手里的这个有着金色纹路的黑漆漆的铁块,就是他耗费了整整一夜时间,注入一万残魂炼制的“骇客终端”。 银尘自己也不知道这件终端到底是个什么品级,因为这个黑漆漆的铁立方本身没有什么太强的攻击力,也不能生成一个强大的防御阵法,没法用《残魂经》里讲述的鉴定方法来判断,银尘不在乎这些,他现在在乎的就是,这件辛苦炼制的诡异东西,究竟能有多大的能耐呢? 他决定试一试。 同一时间,魔威阁,或者所应该说整个魔道所处的望天峰周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身影,这些人显然来者不善,当然他们也没有任何想要隐瞒身份和目的的意思。他们就是正道百门之中,实力处于中间的一些门派的人,这些人,都是被正道的大门派的弟子,或者其他什么管事的仆从,命令来这李试探魔道中人的深浅的。 “告诉他们,我们魔道现在要用饭了,等我们吃饱了再和他们计较,不行?不行就拿土炮轰他们,反正我们是魔道,江湖规矩么……想起来了我们讲,想不起来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梁云广的声音从魔道阵营的最中间向着四面八方传出去,惹来魔道弟子们的一阵大笑与喝彩。许许多多的魔道人士都跟着发出各种怪声,说着各种上不了台面的难听话,让“包围”他们的正道弟子们面红耳赤却又无可奈何。 虽然在明面的实力上,正道此次明显压过魔道一头,前来的正道侠士们普遍修为高上一两个小境界,可是魔道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一些,在声势上,狠狠地碾压了一下正道修士们。 300位正道修士加上26位和魔道的某些门派有大仇的散修,组成了一支小小的“访问团”,跑到魔道上万人的大营盘边上,扬言要除魔卫道,且不说这些个家伙是不是真的具备斯巴达三百勇士的胆气,就算有,这人数上也太少了吧? 300对一万,除非这些正道修士个个开着高达,否则一定会被魔道们吃得连渣都不剩――这不是什么修辞手法,魔道之中吃人的宗派可不在少数。 “万师兄,你这是为何?为何要亲自过来呢?万一……”300正道“斯巴达”之中,一位身材高挑的十五六岁少女正一脸担忧又崇拜地看着傲立于队伍最前面的男子。那位男子也不过十**岁的年纪,生得高大俊朗,六尺多点的身高虽然不过中等,可是挺拔的身姿和英俊如同天王般的容貌很能在瞬间抓住一些深闺少女的心。这位十**岁的少年,虽然贵为社一群正道修士的首领,可是他的衣着一点也不正道。 月白色的长袍,敞开着衣襟,露出里面深蓝色的,雕刻着盘蛇(除非皇帝的铠甲否则不准雕龙,蛟龙也不行,那是皇族其他人员的专享)的珍品灵器铠甲,铠甲的肩部刚好就是两颗惟妙惟肖的虎头,将敞开衣襟的长袍死死扣在肩上免得滑落,长袍的袖口被收得紧窄,一点也不像南方人的款式,倒有点像北方骑兵将领的样式,可是长袍上如同水墨一样的黑色丝线刺绣出的图案分明又是江南风格的春晖流云纹,这让整件袍子看起来很是怪异,敞开的袍子下摆也短了些,露出了这位仁兄的一双高帮靴子,那又是不知道哪个偏远地区的游牧部落的风格,反正穿惯了布鞋的南方人才不会穿这种东西。那一双靴子也是深蓝色的,上好的东海异兽小蓝龙皮革被弄出许多镂空的网眼儿,露出里面穿着的丝绸袜子,而那高高竖起的鞋帮子的顶端,却又硬生生西北苍天原上雪狼的毛皮,一根根白色的仿佛水晶丝线一样毛发翻在外面,看起来更加不伦不类。除了这些,这个年轻人还在长袍(或者叫短袍子)最外面挂上一件大红的披风,而为了在左腰上拴上一把剑,他居然用三圈细细的铁莲子充作腰带。 他不仅仅穿着诡异,就连他的剑也很诡异,从剑鞘上看,那是一柄很细很长的剑,似乎能有将近五尺的长度,宽度却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三个指头。此时那把剑正安安静静地呆在剑鞘之中,而它的剑鞘,居然是一剑“酸枝红”漆器,那大红的色泽,仿佛一道夺命的血泉,在夕阳下氤氲出近似血雾般的光晕,一看就知道被反复刷了很多遍漆,红亮得过分。大红的剑鞘上用亮白的纹银勾勒出一张圆圆的笑脸,和一张三角形的哭脸,看上去滑稽又诡谲,而那把剑的手柄,却是一一条黄金雕铸的鲤鱼,那细密的鳞片纤毫毕现,那一双白银镶嵌出来的眼睛居然闪着灵动的光彩,鲤鱼大张着嘴,两条细细的鱼鳍被做成了护手,鱼身子和尾巴便是剑柄,而藏在酸枝红剑鞘中的五尺青锋,应该就从鱼口中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