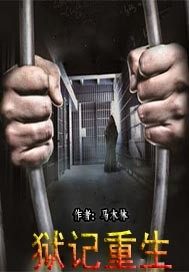转眼就到了春夏交替的季节,气温明显高了起来。紧挨着教学楼马路对面的柳树的叶子由开始的浅绿已经变成了深绿,叶子也完全伸展开了。就像一个蹲着的一个人站起来的样子。还有那棵桃树,现在已经褪去了粉红色的厚厚的花裙,赤裸着绿色昂扬的身段向着暖暖的阳光抬头致意,只是头顶上还有一个尖尖的小刺,证明着他还没有接受过风雨的洗礼。春夏交替的季节最好,风和日丽,花草树木都进入了少年时期,挺拔,青翠,斗志昂扬……太阳毫不吝啬地把热度传递给人们。于是每个人便开始精简自己的衣服,原来的厚重慢慢变得轻松起来。在这个季节人的心情也焕发得奋发向上。 我的心情也渐渐从过去的自危与自卫中解脱出来。两篇写好的新闻稿放在床下,只等着家人接见的时候投寄出去。只是现在农村的麦子需要浇水、施肥、拔草等的劳作,也不知道妻子会来看我吗?我焦急甚至焦躁不安地等待着。 要是家里没人来,我的两则新闻稿就因为时间上的拖延而丧失了自身的生命力。新闻比起文学稿来,时间性更强。 好不容易等到接见日,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写好的两篇新闻上,所以没有出工。石宝、扈驰、吉**,还有白浪也都没有出工。都在期盼着亲人的到来。 白浪给石宝递了支烟,然后两人分别点着。虽然大家的脸看上去都很平静,但是心里都焦灼不安,那种心情,在外面的人很难体会得到,其实打个比方你就能有所感触。就像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约会,即便相约的对方按时到达,你也会觉得时间就像凝固一般,在对方没来之前总是如饥似渴的样子。在这里,每到接见日,等候的犯人都是这样的心情。石宝抽着烟,焦躁地说道:“妈的,下了队就给家里写信了,到现在都三个月了,也不见这个婆娘露个面,是不是跟着相好的跑了。要是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放那小子一码。免得老子在这里忍受十几年甚至20年的寂寞。” 白浪给石宝宽心:“看你想哪了?不会的。你想想你有两个儿子给他左右当着护卫,谁敢和她好啊。再说了,谁也没有吃错药,娶个那么老的婆娘,还要给你两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人家有那钱势,早娶如花似玉分黄花闺女去了。”说完,把头一歪,装作不想搭理石宝的样子。石宝将白浪这一点拨,心里亮堂多了:“我也是这么想,一个又老又丑的婆娘谁稀罕啊。”他两眼又瞪的透圆,咬牙切齿到:“再说了,要是再有人勾引她,我回去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活剥了他!”白浪翻了石宝一眼:“得了,得了,你省省心吧,现在先想想这二十年咋度过吧,其余的都别糊思乱想了。就是婆娘来了咋?还能解决你的实际问题?”说的时候又自怜道:“我都憋了十几年了,派不上用场了。”石宝又是把头一低,垂头丧气的样子。白浪又宽慰道:“我就一个小子、一个闺女,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要结婚了,那老婆娘还不是老等着?别多想了,说不定第一波人进来就有你的婆娘。”石宝脸色又舒缓下来。正在这时,窗户的外面。传出了女人的声音。我能听出来,那是接见室检查物品的那两个女警察。尤其是那个年龄大点的女的,声音特别大,总是爽朗的样子。紧接着便是交交杂杂的脚步声,和那些来接见的犯人家属,还有传进来的男男女女说话声,但这些家属里的的声音没有过多的欢快,听到的只有他们的急促和哀叹。就像是到医院探望病人的家属,面对病人只有伤感和哀叹。可况病人大都很短时间就能痊愈,在这里的犯人却要更久更长的时间才能走出这四壁高墙。所以来这里的家属,除过对荷枪实弹的武警本能地产生的一种畏惧感外,就是对亲人困倦在高墙里的压抑感。即便接见时能听见传出来的笑声,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夹杂着哭声的笑。 听到家属进来,大家都就像驴子一样竖起耳朵,都想听到自己熟悉的那种惹人心跳的声音。如果因为自己的耳朵的分辨率低,那只有再等待着接见楼上值勤员的传唤声了。反正此刻等待接见的犯人心里都十分迫切,又高度紧张。 “赵冬伟、李明宇、王大红……”那个执勤的大个子站在监院门口召唤要接见的人。 第一批来的家属没有我们这个监号的犯人。那个石宝真的有点忍不住了,有些哭腔:“那妈的,这个狠心的老婆娘,因为她,我差点到阎王爷那里去领赏。现在她倒好,都没个怜悯之心。三个月了就像死人一般,连个音信都没有。” 其实都着急着呢。家里人带来的不仅是犯人对家里的草草木木的牵挂,更是一种回归到希望,有家就有改造的尽头。但这对许多犯人来说简直就是奢望,因为好多人不会再有机会了。 那个扈驰就只有一个老妈牵挂他,虽然现在走路都歪歪闪闪的,还是不定期来看他。 第一波,我们监号没有一个人来,空气更加深深的死寂。吉**不是发出几声哀叹。 “我看了,女人就是祸水。没有女人我们好多人也不会犯下这么大的罪孽!”或许这时扈驰又想到了他犯罪的那一时冲动。 我心里也憋得慌,除过惦记家人,还有两篇要寄出去的新闻稿件。听扈驰这么一说,我也为了发泄一下紧张的就像气球要爆的心理,便接过话头,大声说道:“没有女人,世界上就没有男人。因为男人都是女人生的;没有女人,世界就没有男人,因为只有女人的河水才能浇灭男人的欲火。男人都会唱一首歌,叫作妹妹我要渡过你呀你的河。”其实,我现在也是心急火燎。这时,那个扈驰在下头眼睛往我这边直翻,恼怒道:“你瘪犊子无非这回就是沾了女人胡乱给你打分的便宜,有啥高兴的?下一次我还要和你比试,别以为你能胡编乱造文章,就是天下老子第一。” 我见扈驰真的上了火,心里的紧张反倒放松了下来。 我也不理他,自顾自的发泄着心中的烦闷。 “石宝、扈驰、柴兴明……”随着值勤员的喊声第二批接见的人来了。石宝终于等到了家人接见。他走的时候,或许有些紧张,也或许是过于惊喜,反正走路的时候腿有点打闪,像不听使唤似得。扈驰嘴里不情愿地说道:“也不知道老来咋的?这么远的路,在路上摔上一跤可咋弄里。”说着,他和石宝就出去了。现在监号里还有吉**、白浪和我三个人、白浪不会紧张的,老婆自从他进监,已经有一个风韵犹在的中年妇女已经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太太,不用再怕别人勾引了。再说接见他的接力棒已有老婆传给了孩子。每次都是两个已经能挣钱的孩子来给他带些纸烟和零食,另外再给他账上打点钱。再说他年龄大了,也已经没了男人生理上的妄想。只有这个吉**一到接见日的时候就盼望老婆来看他。哪怕老婆来时是两手空空,也能给他心里带来很大的慰藉,毕竟他的家就在这高墙之外的城市里。虽然老婆每次接见后的晚上,他都是想着另一个“俐”女人去发泄,但毕竟有老婆才有那个人的替身。 “哎呀,跟着别人跑了,把老子给忘了。”吉**急躁地背着手在监号里晕晕沉沉的来回走动。 到了快收工的时候,石宝回来了。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进门能看见就像是打了强心剂一样的兴奋:“林峰,来,给你这个老伙计吃个苹果。”说的时候,他已经放在我的床头:“谢谢,见嫂夫人了?”石宝一边把带回的象征幸福的东西分享给别人,一边乐呵呵地说:“是那老婆姨来的。我见她先收拾了她一顿。”石宝绘声绘色地说:“我眼睛一瞪,骂她:你别给我有啥想法,和孩子好好地过,要是给老子带啥绿帽子,我回去就来个‘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他说的是时候,提起左脚,左手做个提拉动作,右手做个刀砍动作,逗得大家都在笑。扈驰没有笑,只是每次接见都是满脸愁容,毕竟母亲老了,步履蹒跚,他看着母亲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 石宝高兴了,满心的喜悦溢于脸上。 下午又是焦躁不安的等待。白浪去接见了,拿回了儿女们给他带来的东西,也是喜滋滋的。第一天接见,我和吉**“扑了个空”。晚上,吉**没有了想那个“俐”的心情,虽然床还在动,但不是过去左右的摆动,只是辗转反侧带来的“咯呦,咯呦”一样叹息。 我的心情也一样,因为我床下还积压着两个小稿。我稍一动床也在响! 明天太阳还是新的,我依然有着太阳升腾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