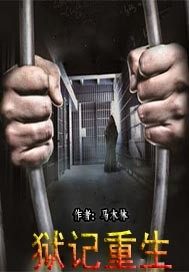我很早就看过《教父》这本小说,说的是“教父”维托·唐·柯里昂在和毒枭索洛索谈判毒品交易时,索洛索从教父的大儿子逊尼的眼睛里看出了对交易的渴望,正是这个渴望的眼神,决定了索洛索要除掉教父,让其儿子以桃代李的决心,最终引发了一系列额杀戮与复仇…… 难道郑维文就是像鳄鱼一样先下手为强找我的薄弱点,作最为前期的试探?但无论怎样我不能使魏志强的故事在我身上重演! 我站起来,没端饭盆,而是不显山露水地把菜盆挡在了身后,我也脸上怀着十分感激的伪装神色:“太谢谢郑老师了,只是在看守所的时候我的胃饿小了,原来饭量可大呢,现在不行了。政府给的正好,以后胃撑大了,人又得受症,还不如这样好,”我还是出来的笑容:“谢谢郑老师!”郑维文一看我真的是心怀感激的去拒绝,也没有继续坚持,又问石宝:“石宝,够不?”石宝有些急切地转过脸,拿起了菜盆,也学着我的话:“谢谢,谢谢郑老师!”同时他还得到了一个馒头的“奖赏”。齐子敬的那盆菜则分给了肚子就像锅凸出来永远永远没有饥饱的刘猛。正如我的所料,吃完饭石宝主动拿上下铺那个老犯人的盆出去洗去了。因为有了第一次,怕这种洗碗的勾当就永远是他的了。我吃饭较快,这在单位和村里,以及所有熟悉我的人都是知道的。那会学校刚毕业,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我在一家钢厂找了份烧锅炉的临时工。每当开饭后,我在橱窗打到饭往回走,离橱窗口大概20米的距离,有个洗饭盆的水龙头,还没走到龙头跟,我的饭就吃完了,正好走到龙头边冲洗饭盆,这样,老是别人还没打上饭我就已经洗了饭盆。在村里谁家过红白喜事,吃席的时候也是,仅上了不到一半的菜,我就已经吃饱下桌子了。后来两个同学抬杠。一个说:“林峰之所以吃饭快,是因为他的嘴大!”另一个同学不以为然,瞪着这个同学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个同学反问:“一半?那你说还有哪一半?”那个同学有板有眼地说:“林峰嘴大,喉咙眼子也粗。”这个同学想了想:“对,你说的太对了,要是只嘴大,喉咙眼子不粗也是咽不下去的。”我吃饭狼吞虎咽我心里明白,最为关键的是小时吃不饱,所以每当吃饭时就有一种迫不及待。吃饭快是日子苦、生活穷留下的坏习惯。但也改不了了。 在号里,我是第一个吃完的,也是第一个洗了饭盆的。要是真趴在那个戴近视镜的床板上从此不仅要改掉吃饭快的习惯,同时还得给他洗碗,这个头一开就没有穷尽。因为在监狱不偏在看守所人来去频繁,调号频繁。在监狱是来服刑的。可能一直就是这几个人,就像一个小家一直是这几副面孔。直到有人减刑回家。即便调号也是小调动,调动来的也是你早熟悉的那相邻监号几个老面孔,只能等到有人回,再有人来,才可能偶尔换个新面孔。就像每年的贴上门的对联,粘上去的时候是新的,但要再换新的,就得等到来年。在重刑监狱里换副新面孔要比新年换对联时间要长久的多。 吃完饭,大家都习惯了午休,都躺在自己的床铺上休息,我才换到个地方,心里总有点紧张,再加上对号里一些习惯成自然的规矩不懂,就像新媳妇嫁到婆婆家,有很多的不习惯,但也得忍耐,慢慢习惯或者改变。我也上了我的上铺,但面对崭新的被罩我怕弄脏了,就看老犯人咋睡。这一看不打紧,真的发现了很多意外,睡在我前上铺的那个戴深度眼镜的犯人的被子不见了。刚才还好好的被子,咋就不见了?只见他睡在床帮的圆钢管上,脸朝上,呈“大”字形躺下。这是玩的哪门子招?再看我的后铺是个瘦瘦的犯人,他的被子也不见了。他是脸朝外侧躺着,与我头对头,把左胳膊当枕头枕着,我就纳闷了,这些老犯人的被子咋转眼间都不见了。再往西边上铺看也是一样,反正被子都不翼而飞,真日怪了。上铺只有我和石宝的被子在,那个齐子敬的也在,不过他在被子上面铺了一张报纸,这样靠一张报纸避免了和被罩的亲密接触,怪不得他上床时手里拿着报纸,原来睡觉都有用啊。我再往下铺看时,终于找到了老犯人的睡觉的绝妙之处,原来老犯人为了不把被子弄脏,不把棱角分明的被子破坏,把被子都放到了下面的自己的马扎上。“研发”了这样既能睡觉,又能保护被子“安全”的“绝招”,真是煞费苦心啊。 看到老犯人这样,我也不敢枕被子了,就把被子往外移了一个空,将就着侧躺着。我的被子厚,虽然也有棱有角,但比起老犯人的豆腐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刚迷糊,就听见老犯人出工,我也下队了,也不知是跟着出还是不出。我和石宝谁也不敢问,石宝看看我我看看石宝,大眼瞪小眼,也找不到答案。 老犯人都站队了。咋办?我推推石宝,看要不要出去。石宝屁股往后挪,不愿往前走。没下队以前,人家戚中和崔小四就一直跟着老犯人出工。现在我们名正言顺下到教员队,就成教员了,可老犯人没有让我们出工的意图。也不能这样老等着,我看石宝没指望了,只好自己谈探个究竟:在教员队里我也不知道谁的“官”大,反正修善林是号长,只有问他了。我赶紧出来:“修号长,修老师:我们出不出工?”我这一说,修善林皱起眉头。他赶紧问那个带班的。带班的是个40多岁的人,个子不高,颧骨较为突出,嘴唇较薄,他看我的时候有些不耐烦,或者还有几分不满或嘲笑:“出哪门子工呢。就会写两篇文章,住在教员号就猪鼻子插葱装象里?” 他尤其是看着我,更是有十足的不满,眼睛里含满了嘲笑:“别以为自己是谁,老师也是谁想当就当的?也说不定以后要扫大院或者拉垃圾呢!”立时教员队里传出一阵嘲笑。嘲笑最大的,笑得都流出眼泪的就是那个看我文章特别不顺眼的扈驰,眼睛笑成了两个扁月亮,嘴里的两个大牙也呲出来,这使我想起我在家喂得两条狗,在争抢吃食时那那种牙露出来的狰狞面目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不满,就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发泄他们的“愤慨”,想通过这一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自高自大和自认为是的才高八斗,嘲笑我能使他们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和在监狱恐慌不可终日的一种放纵。也有不动声色的,那就是郑维文、齐子敬、还有睡在我后铺的那个瘦高个子,还有就是修善林,或许他们本身认为这就是一种接纳,或许他们会一种伪装,或许他们这是达到了一种境界。 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就是我,一个将要在这个看似平静但险象纵生的江湖里学会生存的我。 我站在门口,任凭寒风向一把把小刀在我脸上肆虐,在寒风中能使我思考的更多…… “林峰,林峰!”谁在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