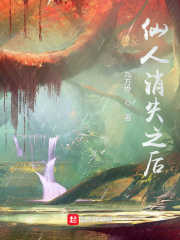底下,吕秋纬忍不住提问: 「主公,闪金平原这般辽阔,连牟国都束手无策,仰善如何将它……?」 他比了个收入囊中的手势。 闪金平原的面积,是仰善的多少倍?连丁作栋都算不过来。想征服闪金平原、想完成两大强国都办不到的梦想?换一个人来说这话,他们得笑他痴人说梦。 贺灵川望向窗外天空,见浓云流滚,忽然心生感应:「仰善在闪金平原,应如潜龙在渊,蓄势待发。」 王福宝兴冲冲道:「那何时方能随云上天?」 贺灵川微微一笑:「等一声惊雷。」 话音刚落,外头电光一闪,随后就是轰隆几声,雷霆滚滚。 今日惊蛰。 众人脸色,都被天雷映得又青又白。 透窗望去,天地为幕,一片浑浊。 只有雷光电蛇划破长空,狰狞傲啸。 众人被震至失语,只能默默感受天地之威,听取雷声一片。 贺灵川运起真力,他的话就伴随雷声,一字一句传入众人耳中:「仰善排云上天之时,必拥雷霆万钧之势。」 远方,最后两道闪电交叉打下来,像天地间长出一棵庞硕无伦的大树,足足持续了两息才消失不见。 漫天雷霆收震怒,化作春雨滂沱。 贺灵川这才继续布置,指了指裘虎和万俟丰:「你们两人,牵头成立仰善军,要有别于护卫队,只取精兵悍将。年底之前,要给我两千五百精兵;两年之内,至少六千。」 两人齐声应是,面色凝重。 这可是巨大的挑战。莫看仰善护卫队现在已近六千人,但主公只说「精兵」,那就是尖锋部队,就是要优中选优,不包括其他杂兵。 这六千人里能挑出五百个锋兵就不错了——包括佰隆人在内。 然而兵无选锋,败之道也。 他们也明白贺灵川的用意,是时候将护卫队与军队分开了,仰善护卫队守卫群岛足矣,而仰善军必须成长为贺灵川手下征战四方的骁骑! 时间紧,任务重,难怪主公要提前布置。 裘虎沉声道:「嵘山传讯,希望往仰善再送来四十位弟子,修行都超过十载;此外,我还联系从前战友,他们也想投奔主公。」 仰善在这一带慢慢有了名气,旧友见裘虎混得不错,才肯来投。 这就叫作呼朋唤友。 对此,贺灵川只有两个字: 「都来。」 而后,他对松阳府的李明扬、李明容兄弟道:「你们这几天带人赶工,给我再造六十套战甲。」 这两位是松阳府仰善分舵的负责人、李伏波的亲传弟子,这两年带领门下颇多建树,把分舵开得红红火火,也挤进了仰善的核心圈子。 「是。」两人先答应再询问,「您要什么样的战甲?」 「轻便的纯黑战甲,并附面具,与仰善的军服迥异;外形狰狞,要能给人一眼留下深刻印象。」贺灵川又想了想,「对了,要穿卸方便。」 两人互视一眼:「我们正好新造一套制甲样版,您来提提意见?」 颜色样式都可以改嘛。 而后贺灵川又给其他人安排任务。 直至雨停,会议结束,各人领命而去。 …… 次日,贺灵川先替换了所有地煞裂口的刑龙柱,再去关怀阴虺之王和伏山越。 伏山越说到做到,果真安心修行不惹麻烦。所以这俩现在相安无事,关系还挺融洽。 几个月时间,伏山越也履行自己的职责,往灵虚城送了两次信 ,向霜叶国师汇报仰善群岛的情报。 这原本是件很尴尬的事,吃兄弟的、喝兄弟的,蹭兄弟的煞气修炼,还要挖兄弟的情报递给上级,脸皮厚如伏山越都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写信都留了副本,这时就拿给贺灵川看。 贺灵川一把推开,一眼不看:「不必,你照实报写就好。」 「这怎么好意思?」伏山越一边大啖又香又甜的龙虾,惭愧呀。 「如实上报,否则你就会被换掉。」贺灵川正色道,「你以为,霜叶国师只派你一个人收集仰善的情报么?」 「呃!」被他这么一点,伏山越恍然,「你说得对。他必定还派别人过来,暗中采集!」 伏山越与贺灵川在贝迦时就关系匪浅,霜叶怎么会对他全心信赖? 「关于仰善的情报,他至少能收到好几份。如果你写了假情报给他,只要他交叉对比,你就很可能露馅。」贺灵川拍拍他的肩膀,「你想跟霜叶那种积年的老妖怪玩心眼子,难啊。」 伏山越很清楚,所以很苦恼:「霜叶对仰善的收入、军力、战略最感兴趣,给我写信时都会问起。」 他又不能不答。 「所谓的战略计划,你是问不到的,霜叶也清楚;至于其他的,你但说无妨。」贺灵川笑道,「仰善群岛正大光明发展,哪有不可对人言语的秘密?」 「霜叶上次来信,问起了你的去向。」 「你怎么说?」 「实话实说,牟国给你派了几个任务,让你去闪金平原完成。任务内容,我并不清楚。」 「对极。」 这时,桃子骑着焦玉过来找伏山越了。 小姑娘笑眯眯,越发开朗,但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跟人牵手。 焦玉看到贺灵川,也打着噗噜上来蹭头了。他跟猛虎顶了顶脑袋,用力抱它两下,把位置让了出来。 去往盘丝岛的海上,摄魂镜道: 「你对伏山越够意思啊,都不让他为难。就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让你为难。」 「伏山越是我和霜叶博弈的重要一环。要是霜叶把他换掉,对我才更不利。」 「博弈?」镜子奇道,「什么时候又开始了,我怎不知道?」 「从他派伏山越过来开始。」贺灵川仍坐在船头,享受扑面的海风。闪金平原的风,没有这么湿、这么暖,「这个举动,既是向我示威,也是向我施压。」 上回玉则成事件之后,霜叶国师不得不替贺灵川打掩护,甚至还取消了朱二娘的通缉令。但贺灵川绝不会天真地以为自己后患尽去,从此可以高枕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