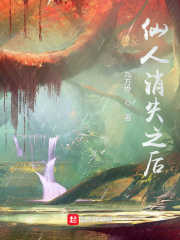是什么原因令她背离了天神的常识和规律?大方壶?这是贺灵川能想到的唯一理由。 贺灵川指了指自己脑袋:“我识海当中有一枚神印标记,但我根本不知何时被种下。” “不奇怪。这么好的皮囊怎会是无主之物?”连它都垂涎不已。董锐则是看向贺灵川,上下打量不已。 这么重要的事,他怎么今天才头一次听说?释难把贺灵川看作东西,后者也不生气,只继续追问:“这种神印标记,能在我不知情的前提下种进识海么?” “想种下标记,需要征得皮囊主人的同意!这才是前提。”释难问他, “你的标记,何时被种下的?”贺灵川皱眉:“记不住了,大概是很早以前。”他在自己和原身的记忆里翻寻过无数遍了,都没找到关于神印标记的蛛丝马迹。 目前基本能确定的是,这印记应该是原身被种下的。他这个倒霉的穿越客,只是继承而已。 释难又道:“嘿,这种事是可以诱导的,尤其皮囊年纪小,懵懂无知。”他的语气中不无羡慕:“你属于哪一位神明?” “奈落天。听过么?”释难长长哦了一声,然后道:“没听过。” “……”贺灵川一阵失望。弥天认不出来就罢了,毕竟它说自己闭关太久;结果释难也认不出来。 这位虽然自称野神,但从它扎根神庙众多的汛阳沙洲来看,它应该挺注重交际的。 “你不认得所有天神吧?” “有地位有声名的天神,我都认得。”释难随口道, “你给我一个没听过的名号,要么它一向名不见经传,要么是还未得名的新神,要么——” “要么?” “要么就是它改名了。”释难道, “天神的主名号也是神格,改名不像你们人类那么容易。” “你从哪里听说这个名号?”释难天又问他, “印记上可不会标注出处。”两人谈话期间,董锐默默给龛前又续了七支香。 没等他插香,贺灵川就把香炉里的灰倒出一小半,而后伸手在桌上比划起来。 这回轮到释难沉默了。这小子,对它是真不尊重啊!但看在刑龙柱的面子上,它不跟他一般计较。 贺灵川用香灰画出了神印标记的图桉。释难看了几眼,没吭声。贺灵川看出了眉目:“你认出来了,对吧?” “这是神明毕碌的印记。”释难沉吟, “它前不久才升格为正神,我还不知道它改名号了。你知道的,每位神明只有一个主名号,但可以有很多称呼。”贺灵川嗯了一声。 弥天的称呼也有很多种,月神正是其中之一。 “这位毕碌神,很强么?” “哪一位正神都很强大。”释难吃吃笑道, “恭喜你,被正神看上了!但我跟毕碌不熟!”贺灵川毫无喜色:“既然我已经被种下标记,那么标记的主人是不是可以随时降临?” “你只付出来了一根刑龙柱和一点点魔气,我就回答你这么多问题,每个都是核心机密,每个都跟你性命攸关。”释难悠悠道, “但我的大方并非无止境,若你想要更多答桉——”他向贺灵川伸手:“就要献上更多祭品!”这家伙是懂谈判的,就卡在贺灵川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上。 “你要哪种祭品?刑龙柱和魔气已没了。” “给我寻几副好皮囊,或者在繁华之地上帮我建起新的神庙。”贺灵川摇头:“目前都做不到。” “那就等你能做到时,再来找我吧。”释难老神哉哉向他伸手,反正着急的人又不是它。 这厮的确回答了好些问题,该给的还是要给它。贺灵川把刑龙柱递给庙侍,又从怀里掏出几样东西,摆在贡桌上:“这几样,有没有你看中的?”他拿出了寒冰符、辟雷牌,还有几样零碎之物。 “喔,你还有不少好东西呢。”释难看了几眼,点中两样, “这两个给我,你就可以继续提问了。”它选中的,居然是琉璃金和浆珠! 贺灵川打破聚灵大阵阵眼时,偷拿了一根琉璃金柱,事后自己砸成了十几大块。 这是珍贵的炼器原料,有钱都未必买得着。千辛万苦去一次墟山,怎么也要把路费攒回来。 浆珠就不用说了,杀妖取珠所得,青阳国师的罪证。贺灵川不知道释难要这两样东西作什么用,或许也是炼器? 毕竟天神也需要笼络人心。 “还是方才的问题。” “神印标记既是定位,也是许可。但是第一次请神需要神降仪式,也就是仪式的主持者和皮囊都必须到场,然后走完整个流程。否则,天神就必须压制皮囊原主的魂魄才行,这样特别、特别费劲。”老庙侍抬头,有几缕烟雾从他鼻子里飘出来, “头一次降临以后么,就不用了。”贺灵川回想当初孙孚平请神时,的确也做了个仪式,才请来神明分身,降临年松玉身上。 他自己这副原身虽然有神印标记,但应该没被降临过。想到这里,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奈落天想吧唧一下强行降临到他身上,也没那么简单。这真是近期听到的最好消息。 “如果天神看中一副皮囊,不经同意可以强行夺取么?”释难的回答很直接:“不可以。”贺灵川摇头:“曾有两个天神分身入侵我的识海,想要鸠占鹊巢。仿佛它们不觉得很难。” “你还挺吃香的。”释难选择性忽略自己方才也进行了这种试探, “他们有没有恐吓你?” “何止?他们直接对我出手。”孙孚平请来的天神分身,进入识海后就变成了与他一同坠崖的沙豹;妙湛天结束对他的神魂审判之前,有一位天神也冲了过来,想将他拽入阴影。 “那就是恐吓,也只能是恐吓。用压倒性的力量威胁你,只要你害怕和软弱——通常都会的——它们就逼迫你同意让它们附身,再烙上它们的印记。”释难笑道, “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往往也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