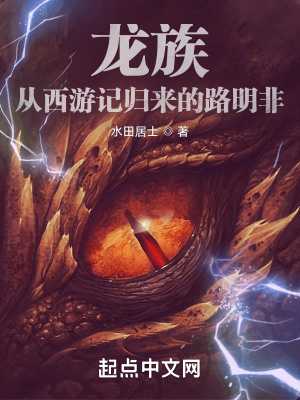正文卷 第六十九章 苏恩曦死里逃生,路鸣泽万事俱备
黄粱一梦终为虚,周而复始只须臾。 深入东海高天原,龙王埋骨歿残躯。 酒德麻衣得造化,千里迢迢救恩曦。 鸣泽施法弄神通,高塔宫闱平地起。 且说绘梨衣怀抱源稚生头颅,正自哭泣。 却听有人唤道:“绘梨衣!醒醒!” 她猛然惊醒,即见康斯坦丁当面,悚然一惊,却被捂住了口。 康斯坦丁道:“莫哭,方才是梦。” 绘梨衣闻言一怔,左右顾盼,即见二人身处下水道,哗哗水声不绝于耳。 她低头看,已不见怀中之头。 康斯坦丁见她面色缓和,即放开手道:“你我被幻梦所惑,将那源氏重工毁了。我自梦中挣脱,携着你来到地下,麻衣多半被擒了。” 康斯坦丁顿了顿,又道:“必是那路鸣泽施法,教你我自相残杀。此地不宜久留,随我来。” 绘梨衣尚自懵懂,见康斯坦丁拽步就走,即紧随其后。 二人寻路前行,见水道幽暗,臭气熏天,纷纷蹙眉。 行不过百步,豁然开朗,现出一口,迈步而出,竟见身处一座城池之中。 康斯坦丁心道:“这东瀛风俗甚是古怪,怎在下水道口建城?” 又走出不远,却见壁厚墙固,乃黑岩、金铁、白银混杂所铸,甬道支差,通往四面八方,竟与那夔门青铜城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斯坦丁心中更疑,转头问道:“伱可知此处?” 那绘梨衣摇了摇头。 康斯坦丁左右打量,寻一通路,即携绘梨衣前行。 这一走早过一个时辰,却望不到尽头。 康斯坦丁正欲回转,却听绘梨衣“啊”了一声,伸手指向一侧。 这龙王瞧去,即见墙破,涌进水来。 那破处乃一段船头撞入,康斯但丁凑近观看,即见其上镌有“Ленин”字样。 康斯坦丁毕竟千岁年纪,对古今中外文字皆有涉猎,蹙眉道:“列宁?那不是个罗刹讼师,布尔什维克党党魁?这船以他为名,必有计较。” 那绘梨衣不明就里,只呆呆望来。 康斯坦丁道:“去船上瞧瞧。” 这二人攀上船头,入得内舱。 只见那船壁上血管密布,爬满全船。枝杈横生,若红树茂密。蜿蜒折扭,若虬龙盘结。 康斯坦丁惊道:“血融金铁,以船为肉,该是个初代王洞府!” 惊讶多时,沿血索骥,即见阶梯走下,入得一舱。 这舱内空无一物,烟雾缭绕,透出红影,耳轮中只听得心跳声起,若战鼓冬冬。 二人撞入血雾之中,即见一颗心脏置于地上,足有一人大小,血脉连通壁墙,不住跳动。 绘梨衣忽道:“这是龙王的心脏?” 康斯坦丁点头道:“该是位初代王埋骨之地,正伺机复苏。” 话落处,忽心头一凛,转头望向绘梨衣,疑道:“你如何说得话来?” 绘梨衣也一怔,忙捂了嘴,顿觉后怕。但见无事发生,复又开口道:“绘梨衣也不知道。” 康斯坦丁默然片刻,忽抬手在绘梨衣头上敲了一下,问道:“痛么?” 那绘梨衣下意识捂头,却怔怔道:“不痛。” 康斯坦丁面色陡变,呆了半晌,叹息道:“你我仍陷梦中。” 绘梨衣一惊,旋即蹙眉问道:“为什么打绘梨衣?” 康斯坦丁头也不回,答曰:“我怕痛。” 绘梨衣暗自气鼓,又听康斯坦丁道:“所以是梦中套梦?我们从那自相残杀之梦挣脱,即陷入了另一处梦么?” 此言一出,二人忽眼前一黑,双双昏死过去。 不多时,那绘梨衣又自醒转,闻得有人唤道:“绘梨衣!醒醒!”又见那康斯坦丁捂住嘴道:“莫哭,方才是梦。” 前番之情,又复上演。 却说康斯坦丁所料果然不差。二人深陷幻梦,来来往往,周而复始。 原来他二人早被路鸣泽所擒,自源氏重工携来东海。路鸣泽将二人坠入水中,以幻梦所惑,引至海底一城,名唤“高天原”。 内有一船,即是“列宁号”,隶属罗刹国前苏联,于十八年前自黑天鹅港驶出,辗转坠于此处。 这龙王之心,便来自当年港口,路鸣泽也曾于那边困顿。 如今他欲以“龙卵”引出白王,却因那初代种死而不僵,寻常人近身不得。路鸣泽又身躯孱弱,入不得水,这才借康斯坦丁二人之手。 此时海面正泊一渔船,路鸣泽端坐船上,暗使言灵,操纵梦境数次循环,终引导二人将那心脏破开,自其中取出一枚龙眼。 那“眼”金光熠熠,才为龙王之卵。他见事已成,喘了口气,即引二人回转。 这一人一龙真如提线木偶,被他所惑,徒劳梦中挣扎。须臾出水,睁睖睖双眼好似痴呆,将龙眼交予路鸣泽。 这贼子咳嗽一声,面露微笑,将龙眼以液氮储之,以待后用。又取出手机,拨通樱井小暮,吩咐道:“送恩曦走罢,将卵取来,带往红井。” 说罢,挂断电话,驾船径奔红井不提。 却说樱井小暮收起手机,即敲门道:“动手吧。” 只听源稚女起身,铮一声掣出刀来。又闻那苏恩曦惊道:“你想干什么……” 话未了,惨叫骤起,甚是凄厉。须臾即止,源稚女开门而出,以袖拭血,收刀还鞘,手中提一长尾肉球,说道:“走吧。” 樱井小暮往屋中看去,即见那苏恩曦小腹剖开,双眸垂泪,嘴巴不住开合,血淋淋的,躺倒床榻之上。 她叹了一声,即与源稚女出门驾车,往那东京去了。 话说酒德麻衣自医院幽幽醒转,睁开眼来,即见矢吹樱当面,问道:“我在哪儿?” 那樱道:“这是家族的医院。你已经脱离危险了。” 酒德麻衣将欲起身,却见全身被缚,束在床榻之上。她沉下脸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樱说:“对于我们来说,你是个危险分子。刚发现时,你手脚全部折断,有严重的烧伤和一条几乎将你切开的伤口。但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间,已经完全愈合了。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服用了进化药。你是猛鬼众的人么?” 酒德麻衣听罢,却松了口气道:“这么说我没破相?” 那樱一怔,点头道:“没有。” 酒德麻衣嘻嘻笑道:“那我有权保持沉默,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荷塘月色。” 那樱纠正道:“是呈堂证供吧?” 酒德麻衣笑道:“不好意思,我日语不好。” 那樱听了,沉下脸来,即道:“你最好与我们合作,为了找回绘梨衣小姐,家族将不惜一切代价!” 酒德麻衣却不听邪,微微笑道:“那请便。” 正说处,忽听源稚生于门外道:“樱,她醒了么?” 那樱即开门,将源稚生迎入道:“她刚刚醒来,态度很强硬,拒不配……” 话未已,却见那床榻上空无一人! 这二人俱是一惊。那樱扑至榻边,但见榻上拘束衣无半点损坏,皮带齐整,只人不知所踪。 源稚生默然至前,自地上拾起一套衣裤,问道:“这是她的病服?” 樱即点头道:“就是她的衣服,怎么在地上?” 源稚生突喝道:“看好门窗!是言灵·冥照。” 却见那樱忽吟唱歌声,唤起“言灵·阴流”,笼住此处。待了片刻,即摇头道:“我的‘阴流’没有碰到人,她的确已不在这里了。” 源稚生听罢,十分恼怒,即命封锁医院,全员寻找。 却说楼下病房,那酒德麻衣惊魂未定,抬头看向屋顶,却见天花板完好无损,并无裂痕。 她喃喃道:“我是怎么下来的?” 正然发懵,忽觉微凉,低头看,即见全身赤裸,一丝不挂。 她登时一惊,忙左右乱瞧,见此房中空无一人,方长出口气。跳下床来,自柜中寻一件病服穿好,暗自思忖道:“我难道是穿墙下来的?刚才我正想如何脱身……” 思至此,忽心中一动,伸手扶墙,回忆方才所感。果见那手穿墙而过,犹入无物。 她又惊又喜,即收了手,心道:“莫非是因为那枚丹药?身上的伤也多亏了它?” 想罢,摸了摸身子,果无半点伤痛,遂喜道:“如此倒方便逃走。” 她忆起前番,心道:“我闻那歌声耳熟,现在想来正是路鸣泽的声音。殿下与绘梨衣必被他所擒……他未去红井,反来源氏重工,不会是巧合……薯片暴露了么……” 想到此情,她按捺不住,立时夺门而出,唤起“言灵·冥照”,避过来往之人,寻一间诊室而入,将医生敲晕,借电脑登录邮箱,点开一则邮件。 原来那苏恩曦凡事料敌从先,自打起了反叛之心,便早定计,将一封邮件发于酒德麻衣,名唤“锦囊妙计”,吩咐她若事不可解,即打开“锦囊”,万事迎刃而解。 当时打开,只见上写“当你打开这个邮件的时候,即代表计划失败,陷入危险。酒德麻衣危险:请按1,零危险:请按2,苏恩曦危险:直接打120。” 酒德麻衣一阵无语,即按“120”。只见那屏幕变作一幅地图,于热海黑石官邸,有一红光以“三短,三长,三短”的频率不住闪烁。 那地图上浮现一串文字:这是我提前设置的程序——我在左边的牙齿里安装了定位器和发信器,可以定位我的位置,以摩斯电码的方式传递信息。在右边牙齿里安装了微型注射器,里面的古龙血清会保我四个小时不死——如果你看到了SOS求救信号,即代表我快死了!别发呆了!快来救我! 酒德麻衣暗骂一声,急奔出门,却见众兵把守,探测器蜂鸣。她慌不择路,撞入东圊之内,即见头上气窗狭小,过不去人。 她急中生智,将病服除下,自气窗扔出,自身则穿墙而过。到了墙外,即唤起“冥照”,穿好衣服,疾奔而出。 辗转奔至长街,正见一人上车,两步赶上,扯了出来道:“借你车用用!” 不顾那人谩骂,上车飞驰而去,径奔热海。 这一路风驰电掣,不过一个时辰,即至黑石官邸。她跃出车来,奔入内室,即见苏恩曦仰躺榻上,只口不住张合,敲击牙齿。 她大惊失色,扑至近前,将手腕塞入口中,喝道:“快咬!” 那苏恩曦立时咬住,鲜血涓涓而入。 这酒德麻衣先得蛟魔王精血,后食金丹,其血堪比大补之药。不多时,即见苏恩曦双眸湛光,被剖开处缓缓愈合,伤疤皆无。 只见她面色潮红,含糊道:“你的血……怎么是甜的?” 酒德麻衣长出口气,将手抽出,埋怨道:“再吸下去,我就要死了!” 那苏恩曦翻身坐起,全无伤痛之相,不住叹道:“唉,兮乎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好险,好险!” 叹罢多时,忽又话锋一转,得意道:“多亏老娘机智勇敢,聪明果断!” 酒德麻衣斜眼望来道:“那您老告诉我,殿下和绘梨衣被抓了,我们两个应该怎么办?” 苏恩曦默然片刻,即道:“作为蛇岐八家的债主,我想有必要将此事告之。” 酒德麻衣问道:“蛇岐八家一帮饭桶,除了源稚生外,其他人有什么用?” 苏恩曦道:“俗话说放屁添风,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也能壮壮声势。最主要还是靠你!” 酒德麻衣一怔,问道:“怎么说?” 苏恩曦道:“那还用问么?快使用美人计,请陛下出山啊!他人家再不来,又是黑王,又是白王,这岛都快没了!” 酒德麻衣哼了一声,说道:“我叫酒德麻衣,又不叫酒德墨瞳,美人计能好使么?” 苏恩曦揶揄道:“你还能输给那小丫头?” 酒德麻衣耸肩道:“男人都喜欢年轻的。” 说罢,她望向苏恩曦道:“扯了这么多,你好点了没?” 苏恩曦拭去泪花,哭腔道:“靠,你这么问我。我又想哭了。” 酒德麻衣起身道:“要哭路上哭,我先去联系陛下,然后就走,去红井!” 她二人如何联络路明非暂且不提。 却说东京城以西,多摩川山中,有一口红井。此井连通两川,正于交汇之所。 天上阴云,不期雨落,几将红井注满。只见一条钢梁横贯井口,潮水漫起,不差三丈。 那路鸣泽负手立于梁上,将一根铁锁左一端束着绘梨衣,右一端缚着康斯坦丁,倒垂而下,去水不过一尺。 他两个七窍流血,滴答答,落在水面,泛起泡来。 路鸣泽言灵念动,缓声而歌,传遍山峦。所到之处,骤起一座巨城。这城以红井为中,往四方铺出皇道,搭起万千楼阁,山为顶,石为瓦,铁锁勾连,悬无数风铃,哗楞楞迸出脆响,将歌声复往远方传去。 这红井中陡现一塔,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约约将井口罩住。 那樱井小暮与源稚女驾车而来,忽迷失城中,难寻出路。所幸源稚女手中肉卵睁眼,迸出金光,引二人直入井来。 二人惊诧不已,及至梁上,那源稚女即将肉卵献上。却听路鸣泽道:“扔下去。” 源稚女一怔,旋即抛下。那肉卵甫一入水,即泛起潮来,将康斯坦丁与绘梨衣淹没。血水相融,化作红浪翻腾。 路鸣泽又取出那枚龙眼,也抛入水中。 浪潮又起,隐隐闻得龙吟之声自水下而来。 他掐指算道:“祭品还差两个。” 只见他喘息一声,口中念念有词,那无数风铃和而为歌,沿山而行,传遍东京。 那东京城中,源稚生与越师傅皆有感应。 单说越师傅,正自院中闷坐,观看“路麟城”烧烤马腿。那八足天马只余七足,闷闷不乐,缩在角落。 只听那“路麟城”道:“想当年,我将这烧火烹调之法,尽数传于长子。不期他青出于蓝,烧的一手好菜,调的一手好汁水,厨艺早在我之上。若他在此,何需我来动手?” 正说处,忽见越师傅面色陡变,抬头遥望。 “路麟城”侧耳倾听,便知计较,笑道:“闹出这般动静,生怕我不去么?”即对越师傅道:“你去瞧瞧?” 越师傅蹙眉道:“我并未答应帮您。” “路麟城”将那马腿洒些孜然,笑道:“去不去由你。不过我闻了闻,却有两个,不,三个后生与你乃同源,怕是你后辈子孙。” 话落处,越师傅霍然起身,惊道:“不可能,我根本没有留下子嗣!” “路麟城”闻言笑道:“这世上勾当,岂是你一介凡人,所能全料?狼子野心者,比比皆是。你血脉于他等堪比玉石金银,岂肯轻抛?我何苦诓骗于你?” 越师傅眼眸闪烁,已有意前去。 “路麟城”看在眼里,呼哨一声,将那天马唤来,对他道:“你骑上它,在云上遥观,便知真假。” 越师傅望来道:“您到底想干什么?” “路麟城”道:“搅闹风雨,浑水摸鱼。你自去便是,我如今能奈你何?” 越师傅似信似不信,呆了半晌,终长叹一声,翻身上马,纵上云头,径奔红井而去。 “路麟城”见他离去,笑了笑,自马腿撕下肉来,自言自语道:“这下祭品齐了。” 却说红井那头,源稚女正与樱井小暮梁上护卫,忽闻得铁鸟轰鸣,抬头一看,只见天边乌云破处,一人纵身而下,落在山中,正是那源稚生。 源稚女心神不宁,即听路鸣泽道:“去罢!你兄弟二人命中注定,有此一战。兄终弟及,天经地义。” 那稚女听罢,躬身一礼,跃下红井,径寻兄长而去。这才是: 源氏兄弟终会面,手足相争并刀剑。 言说前情皆垂泪,过往岁月难再现。 同为祭品将身死,蒙在鼓里实可怜。 白王今夜便出世,龙族祭祀归尘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