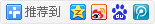安顿好袁青杞休息,出院子时宫一守在门口,看着徐佑的眼神躲躲闪闪。徐佑干咳两声,这都是化身林通时造的孽,不过还好在林屋山待的时间不长,大家点到即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宫一随着林通从正治到祭酒的身份跳跃式变化,心里那点悸动也早就随风而散,今夜再会,偶尔觉得有点羞耻,却并不会生出别的念头。 “祭酒已经歇息了,你快睡去吧,在此山中不必担忧安全问题……若是需要什么,直接吩咐下人们,全当成林屋山就是。” 宫一委身施礼,道:“谢过郎君!” 徐佑驻足片刻,张了张口,却还是没有多说话,微微点头,然后缓步远去。宫一这才起身,望着徐佑的背景,眸子里掠过几许怅然,转瞬恢复了平静,回身警惕的守着门口,并没有如徐佑所言去倒头大睡。 明玉山,终究不是林屋山! 沿着泉井的台阶走到底部,推开石门,詹文君正在处理各种机密情报,螓首几乎要埋在半人高的卷册里,她闻声抬头,笑道:“你怎么来了,宁大祭酒远来是客,主人不陪着成何体统……” 徐佑从后面搂住她的腰身,温声道:“彻夜交战,还死了一位跟随多年的小宗师,又得考虑今后的应对策略,她心力交瘁,早些歇着为好。” 詹文君转过头,玉手抚摸着徐佑的侧脸,爱怜的道:“今夜这样的冒险,以后千万不要再干了!我只恨自己不会武功,没法子在最危险的时刻站在你的身旁!” “术业有专攻,若非你和冬至掌管秘府,我们怎么知道白长绝离开金陵后竟悄然来了钱塘?又怎么知道袁青杞设局到底是为了杀白长绝,还是为了诱我入瓮呢?” 詹文君愣了愣神,道:“夫君信不过袁青杞吗?” 徐佑摇摇头,道:“若是信不过她,就不会有这个局……我只是不愿意把所有人的生死单单寄托在信任这两个字之上,可有了秘府的情报为辅佐,信任才可以真正的发挥作用。” 詹文君明白徐佑心头所系不再是他一己之身,而是明玉山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前程和性命托付,如何谨慎小心都不为过。 可是这样活着,真的太累了! “无论怎样,我和玄机都会陪着你,山巅可去,黄泉也可去!”詹文君紧紧的贴着徐佑的腹部,仿佛要把身子揉进这个男子的体内,血肉相连,不分彼此。 袁青杞率众离开之后,又过了三五日,临川王府第一批人抵达吴县,徐佑带着左丘司锦和清明前往迎接,见到了负责带队的魏不屈。 魏不屈是翩翩佳公子,面如冠玉,目若朗星,手中握着把黑漆银线的折扇,随风轻摇,让人目眩。他先和顾允打过招呼,对顾陆朱张其他人并不搭理,然后冲着徐佑微微下拜,道:“微之!” 徐佑急忙扶起,道:“不敢当郎君大礼,快起!” 魏不屈却摇着头,道:“我此拜,不是拜郎君,而是拜这把徐郎扇。” 徐佑当初在金陵为了装逼发明了折扇,后来被人争相模仿,除过宁、越等偏僻的州郡,其他地方不管冬夏,士族皆以执折扇为美,故又被称为徐郎扇。 “自玄学兴起,名士都执羽扇和麈尾,以为风雅事,我向来不屑一顾。直到徐郎扇问世,见之欣喜若狂,反寒暑於一掌之末,回八风乎六翮之杪,这才是聚江南气韵于开合间的上品雅物。微之诗赋双绝,经艺通达,时人所重,可在下看来,那些东西都是狗屁,比不上这把徐郎扇之万一!” 魏不屈言谈洒脱,气度不凡,然而太过桀骜。今天来迎接的人里还有刺史府的诸多官吏以及顾陆朱张的重要人物,还有部分地方士族的代表,他连正眼都不怎么瞧,面子如何过得去? 徐佑哪里肯陪同着胡闹,笑道:“折扇只是小玩物,郎君喜欢就好。我们先至天平山看看为殿下准备的王府,若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郎君久在殿下身边,可要帮我们拾遗补缺,务求尽善才是。”说完对左丘司锦使个眼色,她心领神会,凑近低语道:“正事要紧!” 魏不屈对这个临川王的义妹相当尊重,闻言收了傲气,对着周边团团作揖,道:“诸君请!” 天平山早已修葺一新,魏不屈做事时和刚才的做派截然不同,里里外外,事无巨细,检查的无比认真,连后院引水所用的暗渠也亲自爬进去查看可否容人通过。之后七八日,不断的有临川王府的人来打前站,数百人在魏不屈的安排下,将天平山打点的井井有条,看似繁琐的事宜也逐渐理出了头绪。 七月初三,天光大好,沿着富川江远处驶来十艘飞云楼船,当先那艘楼船的女墙边甲士林立,刀枪夺目,船头站着两人,正是临川王安休林和王妃徐舜华。 船队抵近钱塘后,徐佑登船拜见,安休林双目含泪,握着徐佑的手,道:“微之,多亏你连月来奔波行走,姊夫才不至于困坐临川,做那盘中待宰的猪羊。此恩此情,没齿难忘。” 徐舜华冷哼一声,道:“知道就好,以后对我七弟好点,别学你那父兄刻薄寡恩。” 徐佑侧目,阿姊你也太彪悍了吧? 安休林丝毫不恼,赔着笑道:“夫人说的是,等大局笃定,我必禀告王兄,对微之重重的赏赐。” 徐佑当然不会像徐舜华那么虎,谦逊的道:“若非有姊夫为依仗,我也不可能在江州、荆州和扬州之间来去自如,江夏王和诸姓门阀给的是临川王的颜面,而不是我徐佑这点微末之光!” 安休林的优点之一,从不贪下属的功劳,处事心公,见事理明,道:“不管怎么说,此次合纵缔交,微之首功,若不重赏,难免让众人寒心,你也别推辞了。” 徐佑笑道:“功劳等打进金陵再叙不迟,当下要紧的是安全送姊夫到吴县天平山。” 安休林略带忐忑的道:“听闻顾刺史不太好相处?” 这就是没权王爷的后遗症,好歹也是天潢贵胄,却担心顾允不好相处,不过从侧面也可看出门阀的可怕与影响力。 徐佑正色道:“传闻不可信,顾刺史为人方正,理政清明,治下严苛,所以被宵小之辈造谣污蔑。依我看来,顾刺史侍君以忠,报国以诚,且敬重姊夫的仁义,此番迎姊夫来扬州,他出力甚多,无须多虑。” 安休林松了口气,还要说什么,被徐舜华拉着袖子往船舱里推,道:“好了好了,你先去歇着,别耽误我们姊弟二人说点体己话。” 安休林苦笑着一边走一边回头,道:“微之,和你阿姊说完体己话,等会来找我,我还有事和你商量……” 徐佑扭过头去,不忍直视。 你这王爷当的…… “哎,哎,阿姊,别……” 所以说做人不能太幸灾乐祸,徐佑还没同情完安休林,就被徐舜华揪着耳朵去了旁边的船舱里,大马横刀的一坐,玉手啪的拍在案几上,道:“你房里那两个女郎呢?知道我路过钱塘,怎么不带来让我瞧瞧?长得太丑没脸见人,还是根本没把我这个家姊放在眼里?” 张玄机去掉脸上胎痕的事仍旧处在保密状态,外人还当她是阴阳鱼脸,徐舜华这么说,显然是对这个弟妇不太满意。詹文君虽是寡妇,然而江东不忌讳这个,只要才貌人品过得去,倒是无所谓。 徐佑走到身后,给她捏着肩膀,道:“阿姊息怒!玄机和文君都是暂住在明玉山,鉴于局势未明,只求安身而已。我尚未明媒正娶,如何能公开带来给阿姊过目?就算我们徐氏是三世不读书的蛮子,可张氏百年书香,高门望族,詹氏门第弱些,但也诗礼传家,别人总得避避嫌……” “哦?”徐舜华乜着眼,道:“食共几,寝同榻,说不得三人齐赴巫山的荒唐事也干过了,这会倒是害臊了?” 徐佑顿时叫起屈来,三人行真的没干过,这个锅不能背,道:“我们清清白白,洁身自好……” “真的?” “真的!” 徐舜华突然伸手抓向徐佑,奇道:“你是不是有隐疾?” 徐佑身为四品小宗师,要是被人掏了铛,那可真的丢尽了武道中人的脸面,轻轻一闪,让徐舜华抓了空。 “阿姊!” 完全无视徐佑的羞愤,徐舜华不屑的耻笑道:“怕什么,小时候又不是没抓过!” 小时候是可爱,现在是雄壮,那能一样吗?徐佑知道跟她掰扯不清,道:“等阿姊到吴县安顿好,我自会找个机会带着玄机和文君前去探访。阿姊你先休息,殿下找我还有事商量……”说完夺门而逃,他真怕再待下去,这个彪悍的前江东第一名媛会做出什么奇葩的举动。 徐舜华追之不及,足履砸了过来,砰的撞上了关闭的舱门,她气鼓鼓的站了一会,噗嗤笑了起来,笑声里是这七年来少有的欢愉。 那个整日里被她揉着脸蛋的七弟,终于长大了,长成了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可以为徐氏遮风避雨,可以为徐氏绵延子孙。 她是早该死的人,可现在还不能死,她要看着徐佑一步步走上朝堂,屹立不倒,然后才能放心的追逐父母叔伯兄弟姊妹于九泉之下。 这个人世间,已经不值得她太多的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