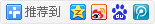詹珽回到后面的雅舍,推开门,房内一灯如豆,在灯光照不到的北上角,李易凤仿佛鬼魂一般,寂静无声的坐在椅子上。 詹珽吓了一跳,这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反手关上房门,压抑的嗓音里透着遮掩不住的怒气,道:“李灵官,刚才在院子里,你为什么不出手?” 李易凤没有搭理他,从怀中掏出一面黑色的令牌扔到了他的脚下。詹珽脸色一变,自杜静之派人跟他暗中联络,共谋大计以来,一直都十分客气尊重,像李易凤这样无礼的举动,还是第一次! 不过,现在的詹珽已经跟詹文君彻底决裂,天师道成了他唯一可抓住的救命稻草,不敢也不能得罪了这个捉鬼灵官。强忍着心中的羞耻感,弯下腰,捡起了那面令牌。 “这是十箓令,既然接受了,今后你就是我道门的十箓将,归本灵官统属。” 李易凤的声音就跟他的长相一样,又干又涩,说好听点叫刺耳,说难听点叫噪音。 詹珽吃了一惊,手中的十箓令差点掉了下来。 他在多年前信奉天师道,就成了入门级别的道民,但这种道民的性质跟其他千万士族子弟类似,仅仅表明了信众的身份,却并不在天师道里担任具体职务。 按照天师道的级别划分,最低级的是道民,然后是箓生,箓生再往上才是十箓,十箓有大箓,小箓之分,大则百十人,小则十数人,以十箓将为首。 也就是说,詹珽被李易凤任命为十箓将,属于越级提拔,破格任命,否则的话,以天师道里正常升迁程序,至少也要五年,且不犯一丁点的错,才能达到这个位置。 詹珽握着冰冷的十箓令,却感觉到一阵的心寒,道:“这是什么意思?” 李易凤沉默不语! 詹珽将十箓令狠狠的砸到地上,道:“李灵官,祭酒亲口跟我说,只要收服了詹氏,拿下了詹文君,就让我做五百箓将,你用这区区十箓令,就想打发我了吗?” 十箓之上,有五十箓,百五十箓,然后才是五百箓,五百箓之上,就是五大灵官,可知杜静之给詹珽画了好大一个饼,怪不得他会动心,不惜出卖自己的家族! “祭酒说过的话,自然作数。只不过你的表现太让我失望,遇到点麻烦,就进退失据,方寸大乱,如何成的了大事?我来问你,既然知道那人名叫徐佑,为什么不提前对我言明?却只报告说是从晋陵过来的普通行商?” “这……不过一个名姓,有什么打紧?” “哈,不打紧?你到现在还以为他是普通的行商?普通的行商能被抓进县衙后毫发无伤的出来,还带了顾允的心腹鲍熙来做说客?普通的行商能让詹文君不顾舟车劳顿,刚至钱塘,立刻马不停蹄的过来拜会?” 李易凤见詹珽还是一脸迷糊,冷冷道:“蠢货,亏得你还是至宾楼的主人!徐佑,是义兴徐氏的七郎,也是这次义兴之变中仅存的徐氏嫡系血脉!” “啊?是他?不可能!”詹珽震惊道:“他不是十几日前在晋陵城外被刺身亡了吗?” “所以你就只当他是行商?”李易凤唇角露出几分讥嘲,道:“詹珽,传言说这几年詹氏之所以能够兴旺,全仰仗詹文君在幕后出谋划策,照你现在的表现,这个传言恐怕不假……” 詹珽最恨就是别人总拿詹文君来压他,顿时怒不可遏,道:“李易凤,你狂妄!今夜的事,到底要算到谁的头上?我费了多少心思,才打探出詹文君的行踪,结果你们呢?总是说天师道里多少高手,怎么连一个女郎都抓不住?要不是詹文君突然回来,赵全,周阳怎么会临阵退缩?有詹氏的部曲在手,管他是不是徐氏七郎,早一并逐出了至宾楼,月黑风高,杀了沉到钱塘湖里,不就了了吗?” “杀徐佑?连太子和沈氏都做不到的事,就凭你?” “我……”詹珽真是要被气的吐血了,道:“咱们不是约定好了?我带人逐他们出店,由你李大灵官带人动手,怎么,知道是徐佑,你就怕了?” 李易凤懒得再跟詹珽废话,屈指弹出一道劲气,烛火立灭,房内陷入绝对的黑暗。 “詹珽,我这就去找祭酒汇报今夜的事情,你自己考虑,要么加入我道门,做一十箓,要么双方的合作,就此作罢。” 詹珽还没来得及说话,房门无声息的大开,又无声息的关闭,他摸索着点起蜡烛,里面已经空无一人! “徐郎君,请!” 徐佑歉然道:“忘了告诉夫人,我还有一侍女感染了风寒,卧榻不起,怕是行走不便,需去雇辆牛车……” “小事!” 詹文君回头招了招手,八名健卒抬起红纱步辇走了过来,对徐佑道:“若是不嫌此辇简陋,可为贵侍代步之用!” “岂敢?”徐佑对詹文君的豪爽大生好感,像此等不做作,不扭捏,落落大方,真性情的女子实不多见,道:“这是夫人的步辇,非侍婢所能乘卧,还是雇牛车的好……” “这个时辰,去哪里雇牛车?百画,去房中请徐郎君的侍婢登辇,不要调皮,莫惊吓了她们。” 百画笑嘻嘻的道:“怎么会,我这么可爱!” 徐佑知道秋分的性子,这会一定一边守着履霜,一边为自己等人在外面的状况担忧,若是百画突然闯进去,说不定会吃上一记凶猛的白虎劲。 “风虎,你也去吧!” 片刻之后,秋分和百画一左一右扶着履霜出了门,得到徐佑首肯后,上了步辇安歇。然后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离开至宾楼,往城东那所幽静的宅院走去。 由于只有一座主楼的缘故,徐佑等人被安排在二楼靠西的厢房。先安顿履霜睡下,吩咐秋分留下照顾,徐佑带着何濡何左彣去了一楼。 还是之前那间屋子,这次换了詹文君坐了主位,在她身后分别站着百画,千琴和万棋,独独宋神妃不见了踪影。千琴犹记恨日间的不满,冲何濡狠狠的瞪了下眼睛。 等徐佑等人落座,詹文君开门见山,道:“听闻几位郎君白日曾登门示警,文君在此先行谢过!” “但凡物不平则鸣,任谁见到此不平之事,都会作仗马之鸣!夫人不必放在心上!” “不平则鸣……徐郎君言语简练,却字字珠玑,文君敬佩!不过,话虽如此,诸位郎君的情义,文君心中谨记,不管有没有良策对付杜静之,总要报答才是!” 这份大气的心性别说在女子当中,就是男子也很少见,徐佑笑道:“不如夫人先听听何郎君的对策如何?” “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何濡也不推脱,道:“在献策之前,我想先问一问夫人,杜静之究竟为了何故,非欲得夫人而甘心?” 徐佑侧目,问的这么直白,会不会被那个冷冰冰的万棋暴打? 詹文君浑不在意,正色道:“不瞒何郎君,此事我也匪夷所思。要说姿色,三吴之地多少美人,怎么也轮不到文君。要说才学,我少读诗书,粗通文理,却仅仅是粗通而已,并不以此见长,更难入杜静之的法眼。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他有何缘故,甚至不惜与家舅为敌……” 魏晋时也称公公为阿舅,詹文君意指郭勉。何濡皱眉道:“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可要是不搞清楚这一点,就摸不透杜静之的底线,应对起来,难免束手束脚。” 徐佑忍不住道:“或许杜静之,那个,那个,别有爱好,恰巧喜欢郭夫人这样的样貌……”就与区区在下一样。 詹文君和何濡同时看了过来,直把徐佑看的心里发毛,何濡才冷哼道:“杜静之在林屋山上的左神、幽虚二观里不知藏了多少美人,无不是修眉小口,妩媚娇柔的绝色。” 言外之意,人家杜祭酒的审美正常的很,别以你那点小见识妄自揣度。 徐佑干咳道:“原来如此!” 詹文君对徐佑笑了笑,似乎对他的尴尬颇觉有趣,转对何濡道:“何郎君为何这般在意此事?” “因为我想知道,杜静之得到你的愿望究竟有多强烈,是不是强烈到可以不管不顾,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都要如愿以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做好孤注一掷的准备!” 詹文君陷入了沉默,显然在思考何濡提到的这个可能性。不过徐佑何等城府,一下子就听出来何濡这是在挖坑给詹文君跳。 任何抛开因果的推理都是耍流氓,杜静之针对钱塘詹氏的行动,要结合这件事的整体来看。刺史府对付的是郭勉,杜静之与刺史府合谋,首要目标自然也是郭勉。 而詹氏,只是杜静之私人的行动,一旦来自詹氏的抵抗威胁到了对付首要目标的大局,他必然要丢卒保帅,任如何不舍,也要放下对詹文君的所有欲望。 所以说,何濡夸大其词,只是为了在詹文君的心目中加重己方的砝码。毕竟,将一个人从刚刚淹没脚踝的水泊中救出,怎么比得上把她从即将溺毙的大湖中拉上岸呢? 智谋,术数,变谲,辞谈! 阴符四相,果然不放过任何一个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事已至此,文君已经做好了你死我亡的准备!何郎君,若你能挽回我詹氏即将面临的命运,今日以后,凡你有命,文君万死不辞!” 何濡摇摇头,道:“这样未免对夫人不公,我不是不讲情理之人。如果能够侥幸破开此局,望夫人答应我三件事!” 詹文君问也不问,道:“可以!我应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