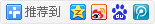至少从表面上看,竺无漏已经彻底跨了,他的眼睛茫然而呆滞,听到声音先是用耳朵去捕捉,然后才是目无焦点的看过来,脸上自然而然的带着点讨好和卑贱的神色,让你毫不怀疑,只要一声令下,这个人可以顺从的做出任何没有尊严没有底线的行径。 曾经那个身穿雪白僧衣,高居莲座之上,如同神仙中人的佛子再也寻不回来,世事总是难以预料,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知道每个人的结局。 “四叔要怎么处置他?” 朱智苦笑道:“我正在为难……” 徐佑明白他的意思,死了的竺无漏并不要紧,可活着的竺无漏却是一个烫手山芋。若把他送还给竺道融,那位黑衣宰相会不会以为这是有意羞辱,从而生怨?毕竟这样的佛子太伤本无宗的颜面,留在金陵一日,就会成为世人的笑柄。 但杀了也不妥,这种事压是压不住的,杀了竺无漏,竺道融可能暗中会松口气,却更要找朱智的麻烦。 “要不找个地方先养起来?”徐佑提议道。 “能养他几时……再被人别有用心的一宣扬,说竺道融薄情寡义,任由佛子流落异乡,不管不问?” “那倒也是!” 徐佑沉吟了片刻,忽然抬起头,眸子里透着笑意,道:“朱四叔,我们其实想得太多了。钱塘现在由中军管理,而中军的统帅是萧将军,而不是你,既然找到了竺无漏,于情于理,都应该交由萧将军处置才是!” 朱智一愣,笑道:“七郎一语惊醒梦中人,不错,这样的大事,自然要萧将军拿主意!来人,送竺法师去见萧将军!” 诸事已了,鉴于钱塘现状,朝廷军队一时还不能离开,等完全恢复到常态,至少还得半年时间,徐佑不想继续待下去,先后和萧玉树、朱智、祖骓等辞行,准备回吴县。朱智怕路上不安全,要派五百部曲护送,被徐佑婉拒了,因为清明、惊蛰已经带着吴善、李木、苍处等数十部曲在离城三十里外的上河津等候,足可保证安全无虞。 “走吧,回吴县!” 和清明他们会合,马不停蹄,直奔吴县。行至西陵县附近,左彣突然纵身而起,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的?” 徐佑勒住马,清明和惊蛰同时出现在他身前,苍处和吴善带着人在四周围拢,摆出防御的阵型。 经历了这么多事,大家都有地啊你草木皆兵。不一会,左彣从道路旁边的深草丛里提着一个人,扔到了徐佑马前,道:“里面还有一个,穿着白贼的戎服,已经死了。这人左腿受了刀伤,没什么威胁!” 刀伤? 徐佑翻身下马,蹲在地上,和蔼的问道:“你是谁,兵凶战危的,为何躲在此地,又怎么受的伤?” 那人穿着破破烂烂的普通衣服,低垂着头,颤抖着道:“我……我是附近农户,因家中断炊,幼儿嗷嗷无食,只好冒死出来打猎。谁想遇到了贼人,搏杀一番,侥幸留得性命,却受了伤,动不得了……” “哦?” 徐佑笑了起来,道:“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听你的谈吐,哪里像是农户?你不要怕,我只是途径此地的行商,去吴县做买卖的,既不属于朝廷,也不属于白贼。你若实话实话,我随身带有刀伤药,说不定可以救你一命。” 那人仍旧没有抬头,小心翼翼的斟酌着词句,道:“我……我真是农户,不过小时候读过几年书,识得几个字。郎君若是好心,也不用赠我伤药,权当没见过小的,放我离去吧!” “哈!” 徐佑蹲下身子,道:“我看你双手皮细肉嫩,不像是长年耕作的老农……这样吧,钱塘离此不远,我派人送你过去,等官府验明身份,再放你离开!” “不要!” 那人惊慌抬头,虽然脸上脏兮兮的,但也可以看出眉清目秀,竟是难得的美男子,苦苦哀求道:“郎君和我无冤无仇,何不放我一条生路?” 徐佑好整以暇的道:“你来历不明,我这人好奇心太重,所以你要么编个故事取信于我,要么就说实话。” 那人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道:“好吧,我说实话。我是西陵县的普通士族,姓李,名易,也是读书人,家中尚有一老母,一妻一妾,两个幼儿。后来白贼造反,西陵招了兵灾,妻妾皆死在乱兵当中,老母重病不起,幼儿孤苦无依,我只好出来找些野菜……” 话未说完,徐佑摇了摇头,惊蛰嘿嘿一笑,长刀的刀鞘重重压在他的大腿伤处,那人惨叫一声,豆大的汗珠滚下脸颊,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 徐佑笑道:“编故事要走心,你这些话骗骗三岁孩童尚可,欺我年少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还是撒谎不眨眼,这里荒郊野岭,杀个人埋了,连野狗都闻不到味!” 那人强忍着腿上的剧痛,知道眼前这些人看似和善,实则跟剪径的贼寇没什么两样,不敢再肆意信口开河,语气变得诚恳了许多,道:“好教郎君得知,非我撒谎,实是身处嫌疑之地,不敢据实以告。我乃宁州胡氏子弟,世代书香,自诩文武全才,却因些许小事被家族所弃。后来听闻五色龙鸾张不疑以寒门出身,被吴国重用为中书令,故而不远千里来投。可恨吴皇不识金玉,仅委以小吏末职羞辱于我,所以数日前城破之后,我便诈死脱身,昼伏夜出,好不容易逃到此地。巧遇另一名逃出来的白贼,约好结伴同行,想着有个照应,不料尚未走出百步,他就伤重而死。我又怕尸体引来追兵,刚欲拖到草丛里掩埋,就逢郎君等骑马经过,我连忙伏在地上,连气都不敢急喘,谁想……”他怯生生的看了眼左彣,道:“谁想竟能被这位郎君发现……” 徐佑转头看着清明,道:“宁州有胡氏吗?” 清明虽然年轻,但从小跟着陈蟾游历天下,论起学问,或许仅次于何濡,可要说到见识,几乎无人可及。 “有,胡氏为宁州第一望族,在当地盘桓百年,枝繁叶茂,家中年轻男子,嫡庶合在一起,至少有百余人,连胡氏的宗主也未必记得清楚。 “也就是说,若要假冒宁州士族,选胡氏子弟再好不过,反正也没人分辨的出来?”徐佑的眼神在那人脸上打了转,笑容像极了老狐狸,道:“是不是?” 清明点点头,道:“是这个道理!” 左彣的目光如同利刃,直指人心,道:“这个人起初回话时呼吸急促如乱鼓,显然是猝不及防,随口胡扯的谎言。可这次回话,一呼一吸,极有章法,平缓连绵,波澜不惊,正常的仿佛两个多年老友在闲话家常……” 唰! 长刀出鞘,惊蛰恶狠狠道:“还在撒谎!” 那人一惊,脖子感受着从刀刃传来的冰冷,忙道:“我说真的,真的!郎君千万要信我……” “好了,我懒得再听你废话。” 徐佑转身上马,吩咐道:“来人,绑了他,塞住口,送到钱塘交给卧虎司。三木之下,我看你还会不会嘴硬?” 苍处取了绳子,蛮牛般的粗腿压住那人的肩背,双手负后,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拖着往马尾走去。 “郎君饶命,郎君饶命!” 那人彻底慌了神,扑通跪地,道:“我说,我说!我姓贺名捷,乃会稽贺氏的子弟。你若放了我,我愿意奉上三百万钱作为回报! 徐佑勒住缰绳,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一字字道:“贺捷?前开国县侯贺倓之孙、前御史中丞贺晟之侄、前大禹书院山长贺纯之子?” 贺捷满脸羞愧,又不敢不回答,道:“是……是我!” 徐佑哈哈大笑,他可以肯定,这次贺捷说的绝对是真话,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贺郎君,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见徐佑大笑,刚才紧张的氛围顿时一扫而空,贺捷忙赔着笑,讪讪道:“不敢当,不敢当!”他还以为徐佑等人真的是行商,存了花钱脱身的念头,道:“这下郎君该知道,我绝没说谎。你若是答应放了我,在钱塘城内某个地方,藏有三百万钱,尽由郎君去取!” “哦?你不怕我取了钱,然后食言么?” 贺捷当然怕,但现在他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赌一把,道:“我擅长观人之法,郎君绝不是言而无信之人。” “哦,你倒是有几分眼光!”徐佑似笑非笑的道:“只是,我对你的钱没有兴趣……” 贺捷突然一阵恶寒,战战兢兢的道:“那,郎君对什么有兴趣?” “六天!或者说,你在六天里的身份,以及你所知道的关于六天的所有内幕!” “啊?”贺捷的脸色顿时煞白,看着徐佑如同鬼魅,道:“你,你到底是谁?” “在下钱塘徐佑,贺郎君可听过我的名字?” 贺捷颓然倒地,几乎生无可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