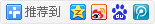在南朝经历新老更替的时候,北朝的权力结构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益州回国之后,元光借口受伤,闭门谢客,三天后登门传旨的人发现空无一物,只找到元光留给魏主元瑜的一封信,他则带着於菟和丑奴不知行踪。 元瑜急命侯官曹追查,皇鸟亲自布置,一晃两个月,没查到任何线索,就像是人间蒸发,渺无踪迹。 这日大雪纷纷,元瑜突然想起幼时和元光戏雪打闹的场景,拿出那封意真情切的信,看着里面的内容,眼眶渐渐的湿润,仿佛那个总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走路都不稳当,却缠着自己教他骑马的元光又出现在了眼前。 随后,内府传出旨意,在西郊青龙池边建造十余丈的高台,台上起五层楼,观宇连阙,飞阁重檐,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取名为忆光台。 魏国的兄弟之争,终究没有像楚国那样血流成河,元光不贪恋权位,全身而退,足可为后来人诫。 留在平城的元沐兰却陷入了莫大的危机之中。 渤海郡公贺旸正式求娶元沐兰,元瑜亲口答应了婚事,并召元沐兰入宫。元沐兰冷冷道:“父皇,你当真要把女儿嫁给贺旸?” 元瑜柔声道:“沐兰,来父皇身边。” 元沐兰倔强的站在殿内,不肯前去。 元瑜叹了口气,离开御座,缓缓走到元沐兰面前,道:“你仔细看看父皇的鬓角,是否已生华发?” 元沐兰娇躯微震,抬头望去,元瑜何止鬓角,就连发丝里也夹杂着根根白发,眼角的皱纹深邃如河沟,曾经笔挺英武的身子也开始有些佝偻。 他老了。 先是皇后的背叛,接着是元光的离开,连番恶战,天灾人祸,国事和家事,还是把那个不可一世的大魏皇帝给压垮了 “父皇……” “沐兰,我近来时觉惊悸,常夜里无梦自醒,辗转难以入睡,用膳也浅尝辄止,食多则胸闷气短,无以名状。太医瞧了,说是无恙,其实我心里有数,怕是天不假年……” “不会的,不会的,父皇是天子,要千岁万岁……” 元沐兰再忍不住,珠泪顺颊而下。 “傻丫头,古往今来,尚无百岁之君王,哪有千岁万岁的皇帝?”元瑜笑道:“”我不奢求百岁,只望再多活三五年,整治好大魏的内外弊政,不愧对祖宗,也就是了。” “然而要整治弊政,只靠杀人是不成的,得恩威并施,让那些大姓听话,又不敢稍有逾矩。” 元瑜的目光逐渐变得无情起来,道:“嫁给贺旸,我知道,你很委屈,但你是元氏的女儿,这是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回去准备准备,等过了年,我发一道明诏,为你赐婚。” “沐兰,我看贺旸真心可嘉,日后对你必然宠爱备至,男人重在权柄,容貌其实无伤大雅。等你们成亲之后,我再封他为王,你辞了军职,好生相夫教子……” 元沐兰心里明白,其实元瑜逼她嫁给贺旸,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大姓,另一方面是为了夺她的兵权。 元瑜自知身体撑不了几年,开始有意为太子元泷的继位铺路。元沐兰的兵权太盛,以前的势力范围还局限在六镇,但经过这几年战南楚、平大乘,已牢牢控制住了中军,比起元泷,实在强大了太多太多。 幸好,她只是女郎! 只要嫁了人,生了子,夺了兵权,对元泷就基本不再具备威胁。 离开皇宫,元沐兰站在拥挤繁忙的街道里,听着周边吵杂的各种声音,突然感觉无比的孤独,如同和这个世界完全隔离开来,他们在过着人生,而自己呢,只是人生里的过客。 “喂!” 一只素手从后面搂住了肩,鸾鸟的脑袋露出来,鄙视道:“还是二品小宗师呢,连被人摸到身子也不知道,我看你的修为越来越退步了。” 元沐兰淡淡的道:“如果不是你,别人早就身首异处了。” “好害怕啊!” 鸾鸟搂着她往前走,低声道:“贺猪猡求亲了,主上怎么和你说的?” “父皇要我以大局为重,受些委屈,帮他稳住诸姓贵族。最好再辞去军职,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我就知道……” 鸾鸟翻了个白眼,道:“你怎么回的?” 元沐兰沉默。 鸾鸟停住脚步,松开了手,走到元沐兰正面,难以置信的道:“你答应了?” 元沐兰惨然笑道:“我能拒绝吗?” “你当然能拒绝!” 鸾鸟气的声音拔高了几度,道:“凭什么?在外面领兵打生打死的是你,回平城联姻取悦大姓的也是你?你是公主,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他的金银玉器,想赐给谁,就赐给谁!” “鸾鸟,慎言!” 元沐兰轻轻抱了抱她,道:“父皇老了,满头白发,我的命从他而来,自然也可给了他去,嫁人而已,没那么可怜。我先走了,想单独静静,别来找我,也别来烦我!” 鸾鸟无法再多说什么,目送元沐兰离去,她的身影,从没像现在这样的凄凉。 “来人!” 鸾鸟突然道。 旁边巷口出来两人,躬身道:“鸾鸟大人。” “将西市冯家牙行的行主带来见我,切记,不要惊动任何人。” “诺!” 两刻钟后,冯行主战战巍巍的垂着头,不敢看鸾鸟,也不敢发声,看上去就是老实本分的商贾。 鸾鸟笑道:“我知道你是秘府的银鱼,别装样子了,今日不会取你的性命,只是让你帮我一个忙。” 冯行主听出来这不是鸾鸟的诈术,而是确实暴露了身份,他倒也坦然,一改方才的胆小,道:“大人请说,能做的,我尽力而为。” “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告诉徐佑,当初他答应的事,到了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冯行主想了想,道:“可以,但我要离开平城!” 银鱼身份暴露后,只有两条路,要么撤回金陵,要么舍身就义,既然鸾鸟只是让他做个信使,那便趁机脱身。 徐佑很快得到秘府的汇报,吩咐鱼道真继续加大对平城的监控,重点是贺旸的行动轨迹,并分批次撤离可能暴露的暗谍。 鸾鸟当真不可小觑,要不是这次因为元沐兰的事,她主动点破,秘府还不知道冯行主已经暴露,虽然潜伏在平城的人都是单线联系,一人的暴露不会影响全局,然而谁知道鸾鸟究竟掌握了多少线索? 又过了一个多月,新年如期而至,徐佑参加完元日的朝中活动,大张旗鼓的回义兴祭祖。 由清明假冒替代,张玄机陪同证明,徐佑带着朱信悄然离开义兴,前往平城。 两人日夜兼程,一位大宗师,一位二品小宗师,几乎不需要休息,只用了六天六夜就到了平城外。 朱信潜入胡记布坊,和霍覆海接上头,知道贺旸今夜会到歌台舞榭云集的沉香坊饮酒作乐。 徐佑换了大乘教的黑色僧衣,头戴幕篱,于子时潜入沉香坊。 这里是平城最大的青楼,占地广阔,放眼望去,无数的亭台楼阁起起伏伏,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廊桥相连,桥下引活水蜿蜒而过,灯光溢彩,美不胜收。 楼阁之间,建有数十座圆柱体的高台,数百名舞姬穿着诱人的衣裳,分别跳着不同类型的舞蹈,有北魏最流行的代面舞,是效仿元沐兰戴着鬼脸面具冲锋陷阵的故事编排的舞蹈,铿锵有力,颇有美感。其他还有拔头舞、踏摇娘等等,让人眼花缭乱,不知今夕何夕。 贺旸正是人生得意之时。 脑满肠肥的他和朋友推杯换盏,怀里抱着身段娇柔的美貌女子,叹道:“再过几日,就要迎娶秀容公主,我这惧内的毛病改不了,可惜以后再来不了沉香坊了。” 有人笑道:“渤海公别气我等了,大鲜卑山的明珠被你采了,还有什么不如意?沉香坊的庸脂俗粉,就是加一起,也比不上秀容公主的一根发丝。” “对啊,我听说成亲之后,渤海公就要封王了,这是一箭双雕,可喜可贺啊!” 贺旸笑的嘴巴都合不拢了,满脸的肉一抖一抖,道:“你们这些啖马粪的家伙,只能看到好处,知道公主的武功吗?二品小宗师!十个我不够她一拳打的!” “哈哈哈!” 众人哄笑,又有人道:“我们鲜卑人还怕这?越烈的马,越是要驯服,几鞭子抽下去,我保你一振夫纲!” 贺旸心里痒痒,手开始上下移动,道:“嘿嘿,我也是这样想的,嫁到了贺府,由不得她使公主的性子……” 正在这时,突然从夜空之中传来黄钟大吕之声: “元沐兰屠戮我大乘教数十万众,今夜杀了她的夫君,为死去的教众报仇雪恨!” 然后,一道璀璨的剑光掠过。 明月黯淡了几分。 贺旸的脖子出现浅浅细细的血痕,骤然断裂,脑袋咕噜噜滚到一边,肥硕的身子歪歪扭扭的倒在了桌子上。 鲜血横流。 一黑衣僧出现在沉香坊最高的旗杆顶端,单足独立,负剑于后,淡淡的道: “弥勒佛坐化之前,传有法谕,凡我大乘教众,定要不择手段,让元沐兰一生孤苦,谁敢娶她,就如贺旸!” 声音消失,人影也随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