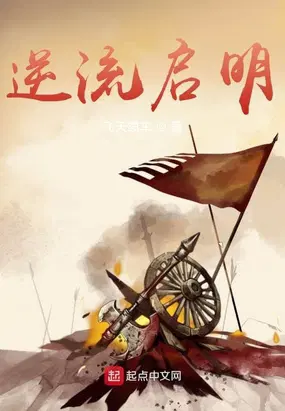总督携带着从京城赐与的金瓶,迫不及待地赶赴拉萨。 掣签前,要将金本巴瓶从大昭寺迎到布达拉宫供有绍武皇帝的僧装画像(圣容)和皇帝万岁牌位的萨松南杰殿。 由大呼图克图率三大寺及布达拉宫南杰扎仓僧众,诵经祈祷七天。 “开始吧!” 三名灵童的名字,生辰八字,纯粹用汉字书写,被放置到金瓶之中。 祈祷七日后,由各呼图克图和西臧巡抚,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 由于是 班婵与达籁念诵停止,然后将目光看向了冯良谟。 后者也不含糊,直接拿起金瓶,双手轻轻地捧着,然后不断地左右摇晃起来。 三个纸团在金瓶中晃荡,仅需片刻的功夫,就见一纸团飞跃而出。 一旁的巡抚张京墨迫不及待地捧着纸团,放置在桌面上。 冯良谟与众人走上前,打开了纸团: 丹增嘉措,绍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 “丹增嘉措为转世灵童!” 冯良谟朗声道。 这下,所有的僧侣们哗啦一下就热闹起来。 “我就说这孩子最聪明……” “平日里他老是去 “终于选出来了,这可比以前好多了!” 相较于之前贵族的明争暗斗,甚至偶尔还能见到刀枪剑影,此次的金瓶掣签格外的简单,也和平。 选人,念经,平和的就出来了。 僧侣们也感受到了仪式感的庄重性与公平。 用抽签法,实在是太公平了! “我会上报给京城,灵童就妥善安置在布达拉宫吧!” 冯良谟轻声说着:“日后也就按照这种方法来,不能有错漏!” “贫僧准备收其为弟子,不知可否?”达籁轻声问道。 “自然!”冯良谟笑道:“由您来教导,竟然又是一位才学出众的活坲。” 他对于达籁施加影响力之事,倒是毫不在意。 因为朝廷本就对其教主的身份很是认可,一个较为整体性的格鲁派,是高原安定的关键。 达籁喇嘛的能力,值得拥有。 张京墨则送这位总督阁下出了寺庙。 “结果是好的。”冯良谟随口道:“转世灵童是良家出身,那么就不会被贵族影响。” “达籁喇嘛年事已高,你可得注意好好操办,越隆重越好!” “是!”张京墨点点头:“最近河谷有些干旱,能从康城调集一些粮食过来,尤其是草料……” “这自然可以!”冯良谟点头应下,他这个总督不就是协调工作吗? “只要你把本子递上去就成。” 忽然,冯良谟认真道:“我听闻格鲁派重视规矩戒律,你平日里也要多加巡查,对于违背戒律国法的僧侣,也不要放纵。” “从严治之,方能肃清僧众内的害群之马!” 张静谟一愣,旋即点点头。 显然,上面已经从种田分田,转化为治理僧侣了。 也对,整个西臧也才一百五十万人,僧侣就有十万人,几乎是三户人家就得供养一僧人。 民间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多与达籁配合!”冯良谟认真道:“他毕竟是教主,要以他的名义行事。” “其余的教派也要筛查。” 一时间,整个高原迸发出肃清毒瘤,挑出僧众中鱼目混珠之人。 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其教派佛经的考核。 道德戒律且不问,对佛经的掌握是必须条件之一。 那些鱼肉百姓,大吃大喝享受生活的僧人,定然是出丑的。 德才兼备的毕竟是少数。 这股风气,不知何时传到了缅甸。 世子孙征灏闻之,大喜过望,忙不迭地准备在东宫中宣扬起来: “我国僧侣众多,固然有许多守戒者,但违背戒律的却有不少,由于佛门松弛,以至于许多漏网之鱼活的痛快,这非出家人之道。” “我意草拟出家人之戒律,严加施行,一旦有违背者,或禁闭,或劳教,或逐出寺庙!” 说白了,孙征灏准备在僧人头上戴上个紧箍咒,把曾经松散且各自为营的僧人们控制起来。 而控制他们的缰绳,自然就是戒律,名正而言顺。 这样一来,遍及整个缅甸的寺庙僧侣们,将会受到限制,从而让王权凌驾于佛门之上。 对于孙家王朝来说,是极其有利的。 饱受儒家学说和汉家文化的熏陶,孙征灏又不像是之前的缅甸诸王,对于佛教无休止地推崇。 正在他津津乐道,宣扬自己的想法时,忽然从急促地脚步响起: “邸下,殿下急令您入宫!” “我知道了!”见到宦官脸色凝重,孙征灏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想法。 他三步并两步,出了东宫。 很快,龙辇就抵达了长寿殿。 浓郁的香料和草药味混合在一起,让孙征灏鼻子一痒。 “父王!”见到床榻上瘦骨嶙峋的孙可望,孙征灏直接跪地,叫出声来。 孙可望则摸了摸这位倍受他期望的儿子,勉强地露出一丝笑容:“缅甸这个江山,我算是完整地交到你手了。” “记住,一定要冷静,平缓,三年不改为父之政,让大家有个适应过程,然后缓缓图之。” 言罢,他就没再多言。 半个时辰内,缅甸文武数十人抵达宫内,跪成一排。 宦官则念起了遗诏,传位于世子孙征灏。 众臣连忙磕头拜下。 孙可望,这位西賊张献忠的养子,终于在异国他乡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四岁。 孙征灏与群臣商议,拟定庙号为太祖武王,谥号则须呈报北京,让其进行赐予。 这是臣子的本分,不能逾越。 其陵墓自然是早就修缮好了,直接入住就成了。 对于其妃嫔,孙征灏起一座尼姑庵,就地安置在其中,免得打扰到他。 至于年号,自然依旧采用绍武二十六年,并无改元的要求。 由此,孙征灏成了孙氏缅甸的 “新京城,怎么看都觉得小了!” 孙征灏站在城墙上,感叹道:“也是时候进行扩充了。” 在武治上,缅甸周边并无强国,暹罗更只是鱼腩,被抢了清迈都只能哭唧唧接受。 这样一来,迎接孙征灏的就是内外的反对派。 地方上是那些旧贵族领主,中央则是那些靠臣。 同时,汉人和土著的隔阂,也是制约缅甸发展的尖刺。 “任重道远啊!” …… 小船一晃,海浪一滚,船只就抵达了栈桥。 船主吆喝道:“到了,到了,该下船的就下船!” 泉州港的码头,已然是极为繁忙。 丁大勇晃了晃脑袋,似乎想让那晕厥从大脑中离开,可惜怎么也无法做到。 在同乡的搀扶下,他踏上了栈桥。 几乎是转眼间,他的脸色好上不少,从惨白变成了正常,眼珠也有了光芒。 “他娘的,终于到岸了!” 丁大勇抑制不住肠胃的翻涌,趴在栈桥上就吐了起来。 像他这样的人有不少,毫无顾忌的呕吐着。 海中的鱼会消化掉一起。 擦了擦嘴,他从怀中掏出了干粮,又嚼了起来。 “你怎么还吃?” “我都吐没了,肚子不就饿了?” 丁大勇啃食着,看向了泉州港。 作为海关驻地,泉州城是对西夷开放的,些许的西式建筑很明显,同时又有许多日式建筑。 泉州是对日本 几乎三成的日本商人首选泉州做买卖,自然而然就聚集了许多的日商。 而之所以如此,不外乎从宋朝开始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然后至明朝,堪合贸易是泉州的主流。 而对日 二人搀扶着登上口岸,买了一些稀罕物,就租赁了一辆牛车,缓缓地回到了家中。 刚至村口,就引得老人的喊叫: “丁大勇,丁岱你们还活着呢!” 一时间,村子沸腾了。 谁不知道,丁大勇与丁岱结伴而行去了南洋,闯荡了两三年后,终于回来了。 不用说,要么衣锦还乡,要么狼狈而归。 而重新看两人这模样,必然是衣锦还乡了。 族亲们纷纷赶过来问东问西,想要知道是否发财了。 而赶来的父母则止不住地叹息,又咧着嘴笑着。 折腾了好一会儿,二人才回到家中。 “老大,怎么样?” 丁老头脸上的褶皱似乎都能夹死蚊子了,他粗糙的双手磋磨着,眼神期待的看着自己的儿子。 老母亲则心疼地打量着他,不住地叹息。 几个弟弟妹妹则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想要知道他包袱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丁大勇则摊开,只有一些衣服,让所有人大失所望。 “儿呀,回来就好!”老母亲笑着。 “能活着就好!”老爹叹了口气,坐在门槛上: “我就说南洋不可能遍地是黄金,要是真的都能发财,谁还待在老家?早就走空了!” “你回来了,就去城里找份事做,码头上的工长是族人,给你安排一个扛包的。” “你别看他累,一天能赚五六十文,攒了一年半载就能娶媳妇了……” 老人似乎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开始琢磨起如何安排了。 家中五子,在福建多子多福的影响下,他并不觉得多,但沉重的压力却让他的腰都弯了。 “爹,我可不去扛包!”丁大勇忙道。 “你这混小子,难道你还想种田不成?村里哪有那么多钱给你种,财主家也没那么多地啊!” 福建山多地少,偏偏又喜欢多子多福,多生儿子,除了像宋朝时因为沉重的丁税不得不弃婴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乐意生子女的。 这就让农村人满为患。 索性福建人并不忌讳经商,脑袋灵活会找出路,各行各业都干过。 见家人误会,丁大勇将门窗关好,然后从袜子中掏出了一叠银票来: “爹,娘,这一路上几千里,公司坐船就得半个多月,人多眼杂,怎么可能放钱在包袱里,别人不就一眼就看穿了吗?” “我都兑换成了银票了!” 望着一叠银票,一家人都惊呆了。 即使是是五块,十块这样的小额银票,也是让人眼睛充血。 “我在齐国开矿,干起了包工头!”丁大勇自豪道: “这两年来一直在攒钱,把黄金都卖了变成银票带回来!” “咱们家,不能再待了,得去南洋!” “你小子,就怕别人眼红?”丁老爹则笑骂道: “咱们族谱连着血,那个敢乱来?” “先给祠堂捐十块,表达你这孝子贤孙的心意!” 丁老爹心情愉悦了不少。 “爹,我还在齐国有几百亩地呢,那里的地便宜,长得也快,咱们一家都过去吧!” 丁大勇鼓起勇气道。 一家人见到钱时,早就千肯万肯了。 “这事得想着族里。”丁老爹沉声道:“你既然在齐国混的那么好,肯定要用一些亲信,还有比族人更信的?” “况且那么多地,不得要人来种?我这把老骨头累得够呛,也该享享福了!” 翌日,丁大勇,丁岱赚大钱的事,立马在村子里宣扬开来,所有人都红了眼。 谁不想发财? 在福建这样的山旮旯,土里刨食没出息,经商又没有人脉和关系,靠族亲就是条出路。 一时间,上百人踊跃而至,让丁大勇吃了一惊。 旋即,他又做出了个决定:“承包荒山开矿!” “老弟,在闽国,这几年来不过七八万人过去了,说一句地广人稀都是抬举,那野兽比人还多!” 丁大勇双目通红:“这些年我在矿上干了,对于什么矿山也清楚一些,到时候费一点钱包山,只要能挖到金银就赚发了?” 婆罗洲三国,文莱已经被湘国代替,那里人口较多,但闽国和岐国人少,政策也更为开放。 只要给得起钱,土地任由承包。 一旦发掘到金矿,银矿,只是要上缴一半所得,余下的就是自己的。 这立马引起了南洋华人的承包开发热潮,吸引了一大波人的前去。 能包山开矿,谁愿意打工啊? “大勇哥,你真的会看山?” “那是,咱们如今有人有钱,肯定会发达!”